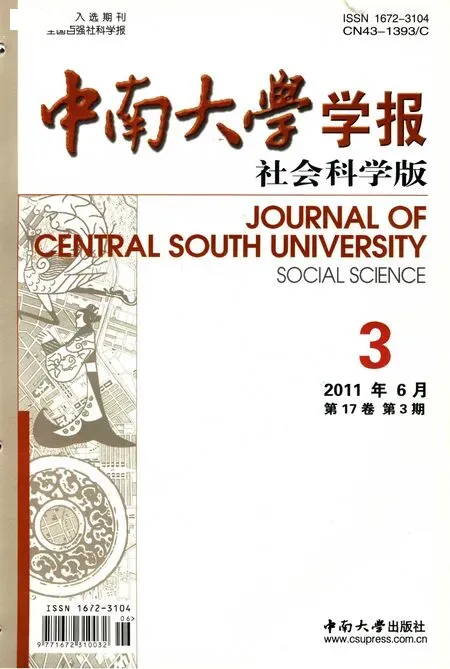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宋前“话”的流变考论
张莉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225009)
研究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尤其是宋元以来的说唱文学,经常会碰到诸如“说话” “平话(评话)” “诗话” “词话” “话本” “话文”等诸多与“话”相关的术语。对于这些术语的探讨,前辈学者已有众多研究成果,如孙楷第先生的《词话考》[1](67−70)、《说话考》[1](71−78),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2],叶德均先生的《宋元明讲唱文学》[3](625−688),吴小如先生的《释“平话”》等,[4](19−31)随着通俗文学研究的升温,还有许多年轻学者加入此阵营,产生不少专著和论文,此不赘述。本文主要从考察被研究者所忽略的“话”的起源出发,结合文献材料,对宋前“话”的流变情况做一梳理,并通过探讨与“话”相关的语词在词义、使用范围及社会功用和地位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揭示宋前“话”的主要义项由“以言载道”向“以事娱人”的转变与其文化地位下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解释为何众多与“话”相关的语词,在宋代之后的俗文学中广泛出现。
一、以言载道:先秦之“话”的雅文化色彩
虽然现存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还未发现“话”的用法,但在先秦文献中,已有多处关于“话”字的记载。例如《诗经》、《尚书》、《左传》中都能找到“话”的使用。同时,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也保存有“话”的古文和籀文写法。
我们先来看看现存先秦典籍中涉及“话”字的内容:
1.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5](548)(《诗·大雅·板》)
2. 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5](556)( 《诗·大雅·抑》九章)
3. 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5](555)(《诗·大雅·抑》五章)
4.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6](1844)(《左传·文公六年》)
5. 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6](1862)(《左传·文公十八年》)
6. 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 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6](1917)(《左传·成公十六年》)
7. 夏,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槚,以自为榇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季孙于是为不哲矣。[6](1929)(《左传·襄公二年》)
8.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7](170)(《尚书·盘庚》)
9. 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7](232)(《尚书·立政》)
10. 王曰:嗟尔众!予言若敢顾天命,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今惟新诰命尔,敬诸,朕话言,自一言至于十话言,其惟明命尔。[8](480−481)(《逸周书·商誓解第四十三》)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先秦之“话”,大都与“言”相关,或作名词,或作动词使用。首先来看其名词用法。如“慎尔出话,敬尔威仪”中的“话”,毛传释曰:“话,善言也。” “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毛传又解释说:“话言,古之善言也。”毛传虽然是汉人所撰,在时间上却是最贴近先秦的,有助于我们对先秦“话”字的理解。毛传将“话”释为“善言”,是较为符合先秦实际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言部”的记录,“话”的古文作“䛡”,籀文作“譮”,有“会合善言”之义。[9](93)由“话”的籀文写法来看,先秦时期“话”的本义最初是来自“会”,指“会合善言”,也即符合道理之言。与毛传的注解相互印证。再如“著之话言”,“不知话言”,“告之话言”,其中的 “话”,杜预均注:“话,善也。”杜预释“话”为“善”,很可能是对经典的误读。对此,清人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纠正说:“经典或‘话言’连文,故《小尔雅》及《左传》杜预注并云‘话,善也’,实则善言为话,非话即为善。”[10](196)其说为确。再看其动词用法。如“乃话民之弗率”中的“话”,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注解释说:“话,告也,言也”。[11](167)“话”与“言”之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尔雅》中寻找证据。如《尔雅·释诂下》:“话、猷、载、行、讹,言也。”[12](2575)关于先秦“言”的使用,《礼记·杂记》:“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庐垩室之中,不与人坐焉。在垩室之中,非时见乎母也,不入门。”郑玄注:“言,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在垩室之中,以时事见乎母,乃后入门,则居庐时不入门。”[13](1561)《诗·大雅·公刘》:“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5](542)根据毛传和郑玄的注解,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先秦之“言”,不同于“语”,主要表示单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指称带有陈述性质的动作或内容,不设问,也不需要对方回答。
通过对先秦典籍中“话”字的考察,再结合后人注疏,我们发现,先秦时期的“话”,主要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词义较为狭窄。主要使用“话”的本义,且经常与“言”连用为“话言”。其次,使用者的身份都比较高,使用范围有限,大多属于官方上层用语,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现存先秦经典来看,“话”在《左传》中出现4处(1处为引用《诗经》),《诗经·大雅》中出现3处,《尚书》中出现2处(1处为引用《诗经》),《逸周书》中出现1处,使用者或为君主或为朝臣,均与政治相关,诸子之书以及其他典籍中未见出现,亦未见于来自下层民众的风歌谣谚中。再次,有典范和教化功用,能引导教育人,是可以著之于书的“载道”之言。再次,表现为一种单方的陈述动作或陈述内容,有接受对象,但不一定需要对方的回答。可见,“以言载道”为核心特征的先秦之“话”,主要出现在主流文化的上层,在一定程度上是贤明政治观点与政治愿望的载体,有着相当高的文化地位。
二、语谈交流:秦汉之“话”的世俗化趋向
由秦至汉,“话”字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没有呈上升趋势,且一部分还是引用先秦典籍中的内容,但与先秦相比,在词义、使用范围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蕴等方面,却已悄然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汉代“话”字,在继续保持“善言”所具有的“载道”特征的同时,又开始向“谈”、“说”引申,向“语”靠近,词义获得丰富,使用范围扩大到交谈双方带有问答性质的谈辩。如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陈恳诚于本朝之上,行话谈于公卿之门。”[14](2247)明确将“话”与“谈”连文。东汉刘珍人等所撰《东观汉纪》,也有一处使用“谈话”的内容:“初,光武学长安时,过朱祜,祜尝留上,须讲竟,乃谈话。”[15](403)此处的“谈话”,有的版本作“谈语”①。“语”与“话”在字形上比较接近,在转写的过程中出现误抄也在情理之中。“谈语”一词的使用,《管子》和《战国策》中有载。如《管子·轻重丁》: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屦穿,寡人欲使帛布丝纩之贾贱,为之有道乎?”管子曰:“请以令沐途旁之树枝,使无尺寸之阴。”桓公曰:“诺。”行令未能一岁,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屦。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对曰:“途旁之树未沐之时,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父兄相睹树下,论议玄语,终日不归。是以田不发,五谷不播,麻桑不种,玺缕不治。内严一家而三不归,则帛布丝纩之贾安得不贵?”桓公曰:“善。”[16](1497)
《战国策·赵策》“冯忌请见赵王”:
冯忌请见赵王,行人见之。冯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问其故,对曰:“客有见人于服子者,已而请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独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谈语而不称师,是倍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称师,是庸说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尧见舜于草茅之中,席陇亩而荫庇桑,阴移而授天下传。伊尹负鼎俎而干汤,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浅者不可以深谈,则天下不传,而三公不得也。’”赵王曰:“甚善。”冯忌曰:“今外臣交浅而欲深谈可乎?”王曰:“请奉教。”於是冯忌乃谈。[17](757)
由“望我而笑,是狎也;谈语而不称师,是倍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与后面“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称师,是庸说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的对应关系来看,“谈语”与“言”具有相同之义。《战国策》为汉人刘向所编,可以说明,至少在汉代,“言”已开始向“语”和“谈”接近。而作为“言”之一种的“话”,其词义向“语”、“谈”引申,也是自然的了。另外,“谈语”的使用场合和阶层,不受限制,男女树下闲聊,主客私下论辩,均可以使用。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汉代“话”的走向产生影响。
再如刘向《说苑·善说》: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问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蘧伯玉曰:“谨受命。”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说。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而吴善用之。釁蚡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盗贼,蚡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以三者言,固可得而托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孰将西归,怀之好音。”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18](282−283)
蘧伯玉与楚王的交谈内容,应该是非常多的。从他们在言及士时所运用的有问有答的交流方式及蘧伯玉的大段舌辩之论,可以确认,这次的“谈语”,是一场带有论难性质的双方的言语交流活动。再从此则被刘向列入“善说”之目来看,“语”具有“谈”与“说”的倾向。汉代文献中的“谈话”,或许为“谈语”讹误所致,或许为“话”之本义的延伸,但不论如何,“话谈”与“谈话”的出现,使得原本属于雅文化范畴之“话”,在汉代以后逐渐落入世俗社会,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日常用语。
三、以情怡人:魏晋南北朝之“话”的世俗化与审美化
魏晋以降,“话”在文献中的出现次数明显增加,与“说”、“谈”、“语”等日常语汇的组合不断变换,词义与使用范围继续扩大,世俗化程度更加显著。同时,魏晋南北朝士人所追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影响到“话”字的使用,使得一些与“话”相关的语词呈现出具有文人雅趣的审美色彩。
首先来看“话言”、“谈话”等前代语词在魏晋南北朝的使用情况。前代地位崇高的“话言”,在魏晋时期已成为常用词汇,除延续善言之本义外,又扩大到谈说、交谈之义,作动词使用。如《世说新语·文学》:“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19](128−129)《世说新语·任诞》:“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19](403)有时又写作“言话”。如《世说新语·方正》: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19](174)
《世说新语·赏誉》: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讶服。[19](270−271)
同时,汉代出现的“谈话”,使用更加普遍,如潘岳《秋兴赋》:“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14](586)《世说新语·赏誉》:“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19](247)另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话”与“说”相连的用法,如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江南人事不获已,须言伐阅,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便尔话说,及相访问。”[20](87)“言话”、“话言”、“谈话”、“话谈”、“话说”等词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频繁出现,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话”有着显著的世俗化特征,这些与“话”相关的语词,已成为当时日常生活中的习语,使用场合和使用者都已没有限制,可以是君臣朝中论政,也可以是士人私下清谈,还可以是百姓街谈巷议、农夫田间闲谈,等等。由意识形态走向世俗生活,“话”的社会及文化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却使得其词义获得了巨大解放,摆脱政治内容的束缚,迈向更加宽阔的空间,为其在隋唐以后呈现出鲜明的叙事及表演特征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另一方面,成为日常用语的“话”,在走向世俗的同时,其中一部分又被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援俗入雅,呈现出别样的雅文学色彩。在魏晋南北朝诗文集中,就保留有许多带有审美意蕴的“情话”、“嘉话”、“良话”、“美话”等众多与“话”相关的语词。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14](2027)张载《七命》:“公子曰:‘大夫不遗,来萃荒外。虽在不敏,敬听嘉话。’”[14](1597)僧佑《弘明集》卷七所载朱昭之《难顾道士夷夏论》:“山川悠远良话未期,聊寄于斯以代暂对情。”[21](44)《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之“徐干”:“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14](1436)这些被文人用“情”、“嘉”、“良”、“美”等典雅美好之词所修饰的“话”,都是作为名词使用的,它们或让人愉悦,或让人期待,或让人崇敬,说明在时人眼中,“话”是具有不同功用与不同审美追求的。这些原本指称日常交谈内容的话语,在文人的审美塑造下,逐渐成为令人愉悦的雅文学用语。
四、以事娱人:隋唐之“话”的叙事与表演色彩
随着“出话”者由政权阶级向普通大众游移,“话”的典范与教化作用也在逐步减弱,统治阶层的“慎尔出话”变成普通大众的随意“出话”,文化地位由雅入俗,特权烙印已不复存在。至隋唐时期,“话”作为“谈”、“说”、“语”之义使用,在文献资料中比比皆是。“话言”虽然还保有一定程度的善言之义,但更多时候,已与“话语”无异。不拘场合和身份的各种“谈话”,在造成“话”的典范作用丧失和雅文化地位沦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话”的叙事特征和娱乐色彩,使得“话”与“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用语“说话”。
隋朝僧人阇那崛多所译《佛本行集经》卷十三,记载释迦牟尼还是太子时在“戏场”与众人同场竞技,“或试音声,或试歌舞,或试相嘲,或试漫话、戏谑、言谈”。[22](405)阇那崛多是以意译方式翻译的佛经,他将“漫话”与“音声”、“歌舞”、“戏谑”等并列为表演伎艺,说明在当时“话”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叙事与娱乐表演色彩。“话”的这种转变趋势,在隋代侯白《启颜录》中也有体现。《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侯白”条引《启颜录》: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蝟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蝟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因乏,不觉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23](248)
“说一个好话”,此处的“话”,已不能简单理解为话语或言谈,而开始具备了另外一层含义,即故事。据《隋书·陆爽传》附“侯白传”记载,侯白“性滑稽,尤辩俊”,“通脱不恃威仪,好为诽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24](1421)由此可见,玄感要求侯白为其所说的“好话”,也必定是其经常所说的“诽谐杂说”。再由“观者如市”来看,这种“好话”无疑又具有很大程度的表演色彩,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俳优小说”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
由隋入唐,“话”的叙事和娱乐特征更加明显,不仅“说话”作为一种专门的伎艺之名出现,还出现了许多以“话”为名的书面和口头文本。如经常被学界所引用的唐代诗人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通行本《元氏长庆集》中该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元稹自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25](55−56)对于“《一枝花》话”的讲说者是白居易本人还是专门的说话艺人,学界尚存有分歧。王古鲁先生在《通俗小说的来源》一文中引元稹自注则作:“白乐天每与余同游,常题名于屋壁。顾复本说《一枝花》自寅至巳。”[26](789)根据王古鲁先生的引证版本,“《一枝花》话”的讲说者当是一个叫顾复本的说话艺人。另外,张政烺所见明抄本《汧国夫人传》下注:“旧名《一枝花》。元稹酬白居易代书一百韵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柱(注)云,乐天从游常题名于桂(壁),复本说《一枝花》,自寅及巳。”[27](244)由此来看,王说为是。与侯白随口编来的故事不同,元稹和白居易所听的“《一枝花》话”,从讲说者到讲说时间、故事内容,无疑都有着很大改观。当“谈话”行为由私下谈说一个个孤立小故事变为有着具体篇名和丰富情节的长篇故事,并出现职业表演者的时候,必然需要一个固定的名称,时人撷取具有叙事和表演色彩的“话”,与“说”相组合,正式作为这种职业说故事表演之名。具有讲说故事意义的“说话”作为专有名词出现,目前,从文献上最早只能追溯到唐代郭湜《高力士外传》。文中载有“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28](120)就是将“说话”与“讲经”、“论议”、“转变”等宗教说唱形式并举。李义山《杂纂》“冷淡”条也有“斋筵听说话”的记载[29](31)。此外,孙棨《北里志序》:“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30](22)这里的“言话”,也就是讲说故事。至于“说话”表演的文本(包括口头和书面),有时也被称为“话”。除上文提到的“《一枝花》话”外,唐代还出现了“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话)本”等以“话”命名的说话底本。在“说话”的影响下,甚至还有一些以“话”命名的文言小说作品,如记载南北朝至唐开元年间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的《隋唐嘉话》、记载刘禹锡所讲故事的《刘公嘉话录》以及记载唐人轶事掌故的《因话录》。
五、余论
可以说,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话”彻底完成了由雅至俗的蜕变,走向民间大众,获得了非凡活力,由僵化的典范教条变成生动形象的故事,并在宋代掀起一股平民文学浪潮,滋生了形态多样的“平话”、“诗话”、“词话”等众多俗文学类别,带来了元明清俗文学的繁荣。关于宋代平民文学与文艺的发展盛况,记载两宋汴京和杭州繁荣景象的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罗烨《醉翁谈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笔记文献,都有不少篇幅的记述。隋唐时期已经成熟起来的“说话”,入宋以后,犹如一粒饱满的种子,恰遇肥沃的土壤,迅速生根发芽,蓬勃成长,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宋“说话”,不仅职业说话人众多,书目丰富,而且有了专门场地,产生了不同家数。有关宋时“说话”的具体情况,前辈学者已论述颇详,不赘。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说话”作为一种诉诸于视觉和听觉的表演艺术,主要由表演和文本两个层面构成。通过前面对“话”字流变的考察,再结合宋代“说话”材料,我们就会发现,“说话”表演中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的是文本(包括口头和书面)层面的内容。对此,笔者还想举出近年来有关中亚东干文学中的一项新材料对其进行说明。
东干人认为“曲子”是包括民歌、戏曲、说唱等所有可以演唱的音乐文学作品的体裁,是“唱”这一动词的唯一宾语。……构成曲子的曲调和唱词分别称作“音”与“话”。[31]
“东干”源于1862年西北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由陕西发起,失败后经甘肃、宁夏、新疆进入中亚。东干文学一直靠口头传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拥有自己的文字。作为中国的一块“飞地”,东干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西北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遗留。由于没有受到现代分类观念的影响,东干口头文学中的“话”,对于我们理解传统“说话”是有所启发的。
东干文学中将说唱的曲调称为“音”,说唱的内容称为“话”,沿着这条思路出发,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说唱文学中会出现“平话”、“诗话”、“词话”这些分类和概念了。说话艺人叙述的内容,可以统称为“话”。而由于表演方式的差异,又被冠以不同的动词或形容词加以区别。如宋代“说话”门下的“讲史”底本,到元代被称为“平话”,就是跟其表演方式相关。“讲史”故事由于篇幅较长,主要采用只说不唱的表演方式,用口语讲故事,所以被冠以“平”,取其平白、平直之义。而一些采用边说边唱进行表演的“话”,又被称为“诗话”、“词话”、“曲话”等等②。后来,当这些运用不同方式进行表演的故事被下层文人整理成书面文字的时候,有的依旧保留了这种命名,如《全相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瓶梅词话》等等。而作为文本内容的“话”,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产生“话文”、“话本”等别名,更是非常自然了。
注释:
① 武英殿聚珍本作“谈话”,清人姚之駰《东观汉记》辑本及《艺文类聚》卷55、《太平御览》卷615的引文作“谈语”。
② 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些关于诗、词理论的书,也称诗话、词话,则与此无涉。
[1]孙楷第. 沧州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叶德均. 戏曲小说从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吴小如. 古典文学漫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5]郑玄笺, 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6]杜预注, 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7]孔安国传, 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8]黄怀信等撰, 李学勤审定. 逸周书汇校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9]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郝懿行. 尔雅义疏(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1]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2]郭璞注, 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3]郑玄注, 孔颖达等正义.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4]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5]刘珍等撰, 吴树民校注. 东观汉纪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08.
[16]黎翔凤撰, 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17]刘向. 战国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8]刘向. 说苑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9]刘义庆撰, 徐震堮著. 世说新语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20]颜之推撰, 王利器集解. 颜氏家训集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1]僧祐. 弘明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2]阇那崛多译. 佛本行集经(乾隆大藏经本)[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7.
[23]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24]魏征、令狐德棻.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25]元稹. 元氏长庆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26]王古鲁. 通俗小说的来源[C]//二刻拍案惊奇附录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27]张政烺. 张政烺文史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8]开元天宝遗事十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9]李义山. 杂纂(说郛本)[M]. 北京: 中国书店1986.
[30]孙棨. 北里志(中国文学资料参考小丛书第一辑)[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31]王小盾. 东干文学和越南古文学的启示[J]. 文学遗产, 2001,(6): 1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