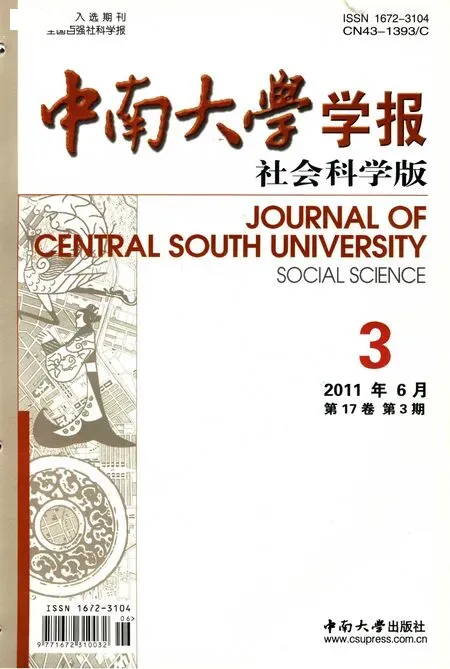我国矿山开采管理“三权分立”模式初探
康纪田
(湖南娄底行政学院,湖南 娄底,417000)
一、国外“三权分立”矿业制度概述
矿业发达国家的矿业立法,取向以社会管制为重心的市场准入制度的构建,一般以矿业环境保护、矿业场所安全与健康保护、矿业市场主体的权利界定和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等为主要内容。而且,其立法重点放在矿产的开采方面。因为开采比勘探更影响社会公众利益,更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笔者重点从矿山开采方面进行分析,至于矿产勘探制度与开采基本相同。国外矿业立法,主要是以矿产物权、特许权与采掘权等三种权利为基本框架而构建整个矿业制度体系的。其中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巴西、波兰、法国和土耳其等。
我国的矿业制度与矿业发达国家的相距甚远,因此,对国外矿业管理制度的认识前提是先辨析国内其他行业相近而又比较成功的 “三权分立”制度,以避免对国外矿业制度理解的先入为主现象。国内相近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房地产开发和机动车行驶。有学者曾提出,国外的矿产权和矿业公司是分开的,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地产公司、汽车所有权与汽车驾驶人也是分开的,唯独矿业制度是合二为一的。[1]国内的土地使用制度以及机动车行驶制度的基本构建都是“三权分立”的。
以城市房地产开发为例,可分为土地使用权、规划许可和建筑许可权、工程承建权,三个权利分别而独立存在。一是民事方面的土地使用权。按照法律,国有土地通过市场出让给私人,出让程序是典型的民事行为,受让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将受让土地入股、合资合作开发或转让。二是房地产公司的开发权。依法成立的房地产公司即使有了归属权明确的土地也不得擅自开发,必须依法获得职能机关批准的用地规划许可、建筑规划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以后才可以开发。三是建筑工程公司的承建权。可以开发不是实际开发,只有经国家许可的、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才能按照建筑施工许可的内容进行实际施工。
再如机动车行驶的基本制度框架也是三种权利分别设立的。一是机动车的归属物权。有了属于自己所有的机动车是一种静态物权。二是机动车的行驶权。机动车买回来以后停在自己的车库里与可以上道路行驶的性质不同,前者是自由的,后者必须经过许可。按照法律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有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行驶许可是法定的要件。三是机动车驾驶权。只有经过考试合格并由国家机关许可的人才有权实际驾驶机动车,没有驾驶证的机动车所有权人没有权利驾驶归属于自己的机动车上道路。因此,只有机动车的归属物权、可以行驶权与实际驾驶权分别而同时存在,才能在道路上实际行驶。
国有土地开发与机动车行驶有区别:一是土地开发属于不动产权而机动车行驶系动产权;二是机动车的行驶许可权对物不对人而可以随车转让,土地开发许可权应由特定的开发主体持有而不得转让。但是,土地开发与机动车行驶有着更多的共性。其一,静态归属物权与动态利用物权分别设立。明确了归属物权的土地或机动车,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排他性支配权,不受他人干涉,也不受公权力的限制,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物权处于平等地位,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的归属物权,一律平等。要开发土地或要行驶机动车是区别于静态物权的动态利用。动态利用是静态归属权的继续状态,但与归属权截然不同。物的动态利用权是不自由的,要受到众多的尤其是公法规定的公权力限制,行政许可就是政府的一种直接限制。其二,动态利用权分为“可以利用”和“实际利用”。可以利用权,是物权利用(区别于流转)的市场准入制,是物权主体支配于物的一种权利能力表现,与准许进入市场的特定物不可分割;实际利用权,是主体本身的市场准入制,是主体进入市场的行为能力和资格,与准予进入市场的特定物没有必然联系,但与准入市场的行为主体不可分离。最后,可以利用权属于行政许可的特别授权。可以利用与实际利用的市场准入都是一种公权限制,但可以利用权受到更特别的限制。所谓特别,就是法律明确规定某类动产和不动产物必须经过许可才能进入市场利用。一般物的市场流转是自由的,多数物的利用也不受政府干涉和限制,但少数物的利用必须受到公权力的严格限制。是否要经过特别限制的许可,是由物在利用时的社会性程度决定的。德国物权法学家沃尔夫总结:“所有权客体满足的社会重要功能越多,就可以对所有权进行越大的限制。”[2](40)自行车的利用不需要行政特别许可,因为自行车的行驶对公众的危害性不大,很少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后果。而机动车不进行特别管制则会对社会危害很大,如果没有明确的号牌,出了交通事故逃逸以后无法找到责任人。因此,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公众利益的物权客体的市场利用必须进行特别的事前管制,才能有利于进入市场后的事中监督和事后处置,才能保护各方的利益。
(一) 矿产的静态归属物权独立并由民法调整
多数国家将矿产资源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物权并初始界定为国家所有,然后又将整体性的矿产资源或矿藏与特定块段的矿产进行区分。矿产,是从整体性矿产资源中通过分割而独立出来的可以用货币计算的矿产资源资产,是通过开采活动能够从土地中分离为矿产品的主要劳动对象,是矿产资源与矿产品的中间物品。矿产在明确归属物权后则成为“矿产权”或“矿产使用权”,与矿产资源所有权以及矿产品所有权不同,矿产权是投入生产的一种基本要素,是投入品,而矿产品是产出品,矿产资源既不是投入品也不是产出品。“矿产权”独立和明晰的目的之一,从国有矿产资源中独立出来的矿产权通过市场让渡给私人,并没有影响国家的专有权地位,反而实现了国家所有权的价值。其目的之二,是为了寻求矿产权在整个物权体系中的平等地位。矿产权是矿产物的静态归属权,可以自由流转和排他性支配,不受他人以及公权力的限制、干涉;与我国的机动车与土地使用权等其他物权一样,受平等、协商一致的民事法律调整。矿产权是普通的民事物权,那么,由于有专门的私法性民法调整而无需在矿业公法中做出更多的规定。所以,多数国家在矿业法中只以简略的条文明确矿产权的民事物权地位。
如《波兰地质与采矿法》关于矿产使用权的规定很简单,该法第7条第2项规定:“国家财政部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使用矿床以及通过设置采矿使用权来处分此项权利的”,财政部是出让“采矿使用权”的唯一主体;第10条规定:“采矿使用权的设置是通过合同来进行的……设立、变更或转让采矿使用权之合同,为防失效,应以书面形式”,自由是合同的重要原则,强调合同形式是为了明确矿产使用权流转的自由性;第13条进一步规定:“民法中与权利使用有关之规定亦适用于采矿使用权”,这就保障了采矿使用权与民事其他权利的平等性。《巴西矿业法典》更简单,唯一规定是第83条:“普通法适用矿产权”,在矿业特别立法中没有对“矿产权”的归属、流转等做出更多的规定。法国的矿产资源做为土地的一部分,多数随土地初始界定为私人所有,只有少数的属于国有矿床,因而在《法国矿业法典》中除了规定“权利人应向地表主人缴纳地下资源租金”这一条以外,很少有关于矿产权的其他规定,当然,私人产权也不必要再由公法去调整。
(二) “可以利用”的特许权设置是各国矿业立法的核心内容
特许权,是某物在普遍禁止利用条件下的特别准许,是行政机关依法对于可能给社会和他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业所进行的直接性社会管制,属于产业的市场进入管制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矿业开发尤其是矿山的开采,在环境、矿业场所安全以及相邻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超过了建筑、化工和爆炸物品制造行业。而且,其影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被影响的人很难通过市场交易来防止影响的发生以及很难以补偿方式填平所承担的成本从而容易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这种不公平现象属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市场总是鼓励矿山企业将环境作为弃置固体废物和排放废气、废水的垃圾场。市场失灵时必须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以弥补市场的不足。矿业特许权就是“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不足的有效方式,是各国矿业制度的核心内容。
任何人非经特许授权不得开发矿产,这是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巴西将特许权写入宪法,《巴西宪法》第168条规定:“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须得到联邦根据法律颁发的批准或特许。”《巴西矿业法典》进一步规定,矿产勘探只需要相应机关批准,而矿产开采要经严格的特许。《波兰地质和采矿法》第15条规定:“以下活动要求取得特许权方能进行:1、矿床的普查与勘探;2、矿产的开采;3、物料在表之非储层储放及废料在地下采坑的储存。”可见,波兰的勘探与开采均要经过特许。《法国矿业法典》第22条规定:“矿山的开采,即使地表主人的开采也只能是依特许权或开采许可证而进行。”这些法律的规定,就像我国的机动车辆行驶一样,即使有了明确归属的物权,也不能擅自进入产业市场,必须经过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才可以利用。所以,排他性支配的“矿产权”与严格限制的“矿产开发权”有着明晰的界限。
特许权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而不是相邻私人的利益,其方向与我国汽车行驶许可相近。《波兰地质与采矿法》以较多的条文规定了特许权授予的要求:明确的矿产归属权;采掘作业的规模和方式;矿床综合利用的程度及其保证实行的具体方式;矿床开发计划;矿区复垦计划;环境预期影响的评价,特别强调的是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开发矿山的申请人符合法定要求的则许可成为特许权人,并就要求的内容与特许机关订立矿业行政合同,作为市场进入者对许可内容的书面承诺。特许权在依法登记后才能实现该矿产“可以开采”的目的。在巴西,特许权授予的地位和要求都很高。对特许的要求,都是以申请人的义务明确规定在矿业法典中的,如必须守法、合理开发、与第三人利益关系、环境与安全、保护水源等,尤其注重“矿床的经济开发计划”,在矿业法典及其规章中对计划的内容、批准和监督都作了详细规定。一旦违反了特许权授予时所明确的义务,则撤回特许权并承担相应责任。《法国矿业法典》第26条规定:“凡不具备开采工作所必须的技术和资金能力的,不能取得特许权。”技术、资金、保证金等,是多数国家授予特许权的法定要求。
(三) “实际利用”的采掘权由有资质的采矿企业行使
有了特许权不等于能够从事采矿活动,必须由专门的、有相应资质的、能独立地承担责任的采矿企业实际开采。《巴西矿业法典》第37条规定:“只有采矿企业方可有资格得到开采权。”多数国家将直接进行采掘的采矿企业与特许权人分开,从而使采掘权独立于特许权而存在。采矿企业与特许权人有着以下根本区别。
一是主体不同。波兰分为“企业主”与“采矿企业”,《波兰地质与采矿法》第6条明确规定:“企业主,指拥有进行本法所管理之活动的特许权的一个当事人;采矿企业,指一个企业主所使用的在技术上及组织上集合在一起的方式,以直接从事矿产的开采,包括在技术上与之有关的矿业工程,建筑及选矿设施和设备。”《土耳其采矿法》将特许权称为“采矿执照”,其主体分为“采矿执照”持有人和“采矿许可证”持有人,后者专门从事开采活动,就相当于我国的建筑工程公司或驾驶员。矿产权人、特许权人与采矿企业的不同主体,是指设立的不同性,分别设立却可以兼任而合并。矿产权人与特许权人一般都可以合并,而特许权与采掘权,有的国家合二为一,如巴西规定采矿企业可以申请特许权,相当于我国的行驶权和驾驶权归一人持有;波兰则不允许,只允许企业主“使用”采矿企业,相当于我们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承建施工一样。
二是主管机关不同。《波兰地质与采矿法》第 16条规定“特许权均由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和森林部授予”;第109条规定“国家采矿监督机构对采矿企业的经营行使监督和控制”,采矿监督机构包括国家最高采矿办公室及地方采矿办公室;两个不同的主管机关又相互配合,第116条规定:“当采矿监督机构认定企业主违反了特许权中规定的条款时,应立即将此通知特许机构。”《巴西矿业法典》第7条规定“共和国总统通过法令颁发开采特许”,在联邦官方日报上公布并在矿产地举行颁发仪式,说明特许权的地位很高;第80条规定“采矿企业,为获得勘查或开采矿床权,或在国内从事采矿活动须有矿业能源部长颁发的批准书”,这个批准书相当于机动车驾驶证。
三是对采矿企业的要求不同。依法设立的采矿企业,根据特许授权时所审批的开发计划,在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矿产资源合理管理、矿区建筑与矿山设备、环境保护、危害预防和改正、矿业用工、矿山技术等方面提交一份采掘经营计划,由管理采矿企业的行政机关以决定的方式审批。审批通过了的开采经营计划作为以后检查监督的依据,如果采矿企业在开采中违反开采经营计划,视其违反程序依法进行处置,直至停止经营。同时,矿业法在采矿企业的进入以及采矿企业的退出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最后是流转程度不同。一般说来,多数国家允许特许权流转,特许权依附于矿产物权转让、抵押和入股,就像我国机动车的号牌和行驶证跟随机动车流转一样。但是采矿企业的资质及其开采经营许可不允许流转。《土耳其采矿法》第27条规定“采矿许可证不得转让,采矿执照可根据规章作为一个整体转让”(采矿执照相当于机动车行驶证)。《巴西矿业法典》第55条规定:“如果特许权所有人按法律手续将特许权转让或抵押,由特许权而产生的权利、义务、限制和效果都将继续有效。转让或抵押只有在开采特许登记簿上登记备案后才有效。”当然,特许权的流转必然是跟随矿产物权流转,特许权单独流转是没有意义的。
二、我国“一权制”矿业立法模式的困境
国外“三权分立”的立法模式,是符合矿业开发特点的应然性体现。相互之间界限分明,为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工、责任、权利等提供了合理的规范,让其在各自的轨道上行为。相比之下,可以发现我国三合一的“一权制”立法及其理论的缺陷。
(一) 我国“一权制”的现行立法及其理论
对于我国,也以采矿权为重点进行分析。我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6条对探矿权与采矿权分别进行了界定,其中“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采矿权的法定含义是整个采矿权制度的基本框架。这里的采矿权、采矿权人和许可证是三合一的:矿产权、可以开采权与实际采掘权,合并成唯一的“采矿权”;主体是唯一的,既是获得矿产品的采矿企业,也是可以“开采矿产资源”的特许权人,还是“许可证规定范围内”矿产物权的归属者,统称为“采矿权人”;一个采矿许可证是“规定范围内”矿产归属的产权证,也是在该范围内可以开采矿产和实际采掘矿产的两个市场准入证,属于三证合一。问题的关键是,“三合一”的“合”,不是分别设立后在行驶中的合并,而是一次性设立的不可分割的“一权制”。因为该规定范围内矿产物权出让、可以开采该矿产资源的特许权授予以及实际采掘该矿产的批准,是唯一的行政职能机关及其一次性的行政决定所完成的。以“一权制”为基本框架构建我国现行矿业制度体系和按照“一权制”实际操作,明显地违反了矿业的一般规律:矿产的静态归属物权属平等的民事范畴,应由市场配置 ,矿产动态利用的限制应由公法规定的政府进行管制。“一权制”则由政府越位取代了市场的配置功能,政府越位而导致公权力管制的缺位。这就是我国现行矿业制度的整体安排。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不但没有质疑探矿权或采矿权“一权制”的弊端,还将不同质的探矿权与采矿权捆绑成“矿业权”。 矿业权理论就像个“玻璃盒”,看得见但又触摸不到。将采矿权(或探矿权)的归属物权、特许权和采掘权(或钻探权)的三个独立权利整合为一体装进“玻璃盒”,则三个独立权利相似于整体中的三个面而表现为一个“三棱形”的“玻璃盒”。当学者站在“三棱形”不同的面去阐释时,“玻璃盒”似乎成了一个“魔盒”。站在“三棱体”的矿产物权这个面看“玻璃盒”时则认为:“矿业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是一种物权。”[3]矿业权归属物权,是由国有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所以《物权法》也在这种无奈的条件下将探矿权与采矿权列入用益物权。而当站在“三棱形”的特许权这个面观察“玻璃盒”时则指出:“矿业权的‘权’仅仅是从事矿业活动的‘特许权’,这种权利并不包括相应的矿产资源物质。”[4]这样否认矿业权还有矿产物权另一个面的存在,并因此得出结论,矿业权是由公法调整的,“矿业权的设立离不开行政许可”。[5]还有学者站在“三棱形”的采掘权(或钻探权)的一面看“玻璃盒”时总结:矿业权是矿业项目投资的经营行为,“矿业权的安全性,是指在矿业投资的不同阶段,如矿业勘查、矿山建设、开采、闭坑等,矿业权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稳定性”。[6]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只总结一面而否定另外两面,也有学者整体地看“玻璃盒”,“矿业权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建立在国家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之上,是国家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通过行政许可方式予以设立的……对申请人的资质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相应资质的申请人,才有可能被行政机关授予矿业权。”[7]从整体上看,矿业权包含了矿产物权、行政特许和资质条件等,因而“学者对矿业权的物权属性主要有准物权说、特许物权说、用益物权说、自然资源使用权说”[8]等众多性质的分析。其实,整体论者从整体上概括这个“玻璃盒”,比其他人从其中一面得出的观察结果更加糟糕,因为整体论者牺牲了普通的法理逻辑而换来了外在的整体联系。比如,整体论者关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立”矿业权的理论,就是为了将矿产物权与行政特许硬扯到一起而不顾所有权人与行政许可主体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也不顾物的所有权人不能行使行政许可的基本逻辑。
(二) “一权制”法律制度在实施中的困境
我国现行“三合一”的采矿权制度,在实施中处置矿产权或行政许可权时总是处于两难选择之中,而矿业开发中的矿难频发、资源流失和浪费、环境破坏以及市场秩序紊乱等,都缘于两难选择。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就可以知道。
首先,矿产权招拍挂的有偿取得方式难以实行。有偿使用才能保障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我国从 2006年起一律实行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按照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的规定:以招拍挂方式确定的中标人、竞得人,按成交协议交纳约定的交易费用则发给采矿许可证而成为采矿权人。这在表面看来是以招拍挂的公平竞争程序出让,实质上是在以有偿出让矿产的名义和民事交易的形式掩盖出让公权力行政许可的事实,最终又回到“整体论者”关于“所有权人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立矿业权”的理论上去了。这就相当于机动车市场交易成功时授予车主行驶证和驾驶证。有偿出让矿产权却最终出让公权力的现象,在权利处置时又是反过来的。按照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规定,未按协议缴纳费用的,由行政许可机关罚款直至吊销许可证,不服行政处罚的可以申请复议或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出让矿产权引起的民事纠纷,以行政强制处罚和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也相当于因为机动车车款纠纷而由行政主管机关吊销其行驶证和驾驶证。这种规定明知是错误的,但在“一权制”条件下只能错误的存在。
其次,矿山企业承担的法律责任难以明晰。《矿产资源法》第42条规定:倒卖采矿权牟利的,则吊销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至今,我国没有相关解释以明晰不许倒卖的是矿产物权还是行政许可权。其实,“一权制”的采矿权因互不独立而无法明晰。《矿产资源法》第44条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处以罚款,可以吊销采矿许可证。”破坏性开采属于采矿企业的行政违法行为,如果给予吊销采矿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必须将矿产物权也没收了。这就是说,吊销驾驶许可证时必然将合法的机动车辆没收。这种法律实施中的尴尬也是因为“一权制”所致。
再次,矿产权有偿取得后的市场流转是个难题。矿产物权是从国有矿产资源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以后依法出让而设立的,与其他物权一样应当在市场上自由流转,依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转的矿产权才能效用最大化。但是现行矿业制度严格限制流转,甚至明确“禁止倒卖牟利”行为。矿产权在市场经济下的必须流转与法律制度严格限制流转的冲突,催生了扩股、承包和变更法人等众多的地下流转现象。因此,许多学者指出法律严格限制流转的不当性。但是,在“一权制”条件下允许自由流转要比严格限制流转的后果更严重。因为“一权制”的主要流转对象不是矿产权而是行政许可权,受到严格管制的特许权和采掘权一旦允许自由流转而摆脱了职能机关的监管视线,将会有破坏环境、矿难频发、资源浪费等现象的不断发生。在这一方面的监管不力都会酿大祸,如果完全失去监管后果会更严重。因此,在 “一权制”条件下宁可让物的价值损失也应保护公众利益,严格限制流转是迫不得已的制度安排。
最后,矿产资源整合运动更不容易。从2005年起进行了全国性的矿产资源整合,尤其煤炭资源整合政策,不顾一切地往前推进,学者则在一边议论颇多。矿产资源开发点多面广,市场进入主体过乱过多,必须进行整合。但是,整合的重点对象是矿产资源,还是可以开采的特许权,或者是实际开采的采矿企业,没有也无法明确。整合的名义和标准是针对矿山企业采掘的年生产能力,比如煤炭生产从单井年产9万吨提到年产30万吨、年产90万吨、年产120万吨,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达到产能的则退出市场。这样,许多由政府许可的采矿企业因政策变化而被赶出市场,过去已明确了归属权的剩余矿产也强制性收归国有,使人们认为排他性支配的物权在政府面前没有了保障。实际上,采矿企业的产能标准只是整合的手段而已,最终却是矿产物权的整合,多数中小采矿企业退出了市场,留下的矿产资源向大型矿山企业甚至集团企业集中,逐步走向资源垄断。资源整合本来是市场的功能,但特许权和采掘权的整合又是政府的功能。因为“一权制”现象而让政府取代了市场的功能,这就导致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加速了资源垄断的形成。
三、建构我国矿业制度“三权分立”立法模式的主要障碍
三权分立的矿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矿产权独立,是将国有矿产资源的某特定区域资源分割出来,单独设立区别于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矿产物权,在市场上出让给私人,私人受让后设立的矿产权能排他性支配。私人受让的矿产权与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之间产权界定清晰。矿产权的设立不与公权力行政许可搭界,是独立的民事行为,有了归属明确的矿产权以后依法定要求申请特许权,申请人与矿产权人并不是同一的。只有获取了特许权的特定矿产才能让采矿企业实际开发。矿业开发的“三权分立”,能各负其责各享其权,假设给予吊销特许权或采矿企业停产停业的处罚,也不会涉及矿产物权。“三权分立”使市场、政府、企业之间有了明确的边界,是构建我国矿产制度的基本方向。
但是,在我国构建“三权分立”的矿业制度体系,还有诸多的障碍。其一,我国矿业制度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矿业立法受原苏联模式影响较深,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基本上转变了原苏联模式,而我国仍然处在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之中。将国有矿产资源奉上神圣地位,用公权力分配民事物权。学者将行政许可方式分配物权称为有“浓厚公法色彩的私权”,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走计划经济的道路而找不到方向时,则给矿产物权贴上一个“准”字,有了“准物权”则可将所有讲不清的理论均归责于“准”,即矿产物权的非典型性。[9]国有矿产资源是典型物权,到私人时成了准物权,前者到后者的变换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秘密。尤其是这种变换,不能给矿产权正常的身份和平等的地位而阻碍了现代矿业制度的建立。其二,我国行政特许制度设置的重大失误。《行政许可法》第12条及第53条规定:以行政许可方式分配稀缺资源。起草《行政许可法》的专家、向全国人大说明《行政许可法草案》的官员以及从事行政法研究的学者,异口同声的结论是:“特许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稀缺资源。”[10](9)凡是有价值的资源都是稀缺的,特许功能是分配稀缺资源的结论实在离谱。在国外,行政特许是对有严重社会影响的行为在进入市场时的事先管制;在国内,一般行政许可都是政府对某一行为的事先准许,也不与“稀缺资源”有关联。唯独我国在行政特许方面严重错位,这是矿产特许制度的一大障碍。最后,现行矿业立法的价值取向不科学。目前立法,主要是以“矿”的物权为中心的财产性《矿产资源法》,主要是围绕矿产资源的分配、保护、税费等做出规定,还不是以“采”的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管制性《矿业管理法》,因而无法将特许权设置、开采的安全、环境保护、矿业相邻关系等重要内容纳入法律之中。因此,现行立法走向是构建现代矿业制度的障碍,必须重构矿业基本制度体系,制定一部以社会管制为核心的《矿业管理法》,甚至应着手制定《矿业管理法典》,才能将“三权分立”作为法律的基本框架。
[1]张文驹. 矿业市场准入资格和矿权主体资格[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06, (10): 4−8.
[2]沃尔夫. 物权法[M]. 吴越, 李大雪,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2.
[3]黄道平. 矿业权抵押贷款刍议[N].中国矿业报,2010−03−20(2).
[4]时红秀. 矿产资源资产权利缺乏体制保障[N]. 中国经济时报,2009−11−17(12).
[5]曹树培. 矿业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与行政许可的关系[N]. 中国矿业报, 2010−01−23(2).
[6]高兵, 贾其海. 浅议矿业权安全的一些问题[J]. 中国矿业,2008, (12): 5−7.
[7]李显冬, 刘志强. 论矿业权的法律属性[J]. 当代法学, 2009,(3): 104−109.
[8]张彬. 我国矿业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J]. 煤炭经济研究, 2007, (12): 58−59.
[9]李显冬. 矿业权的私权法律属性[J]. 北京石油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07, (2): 4−9.
[10]汪永清. 行政许可法教程[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