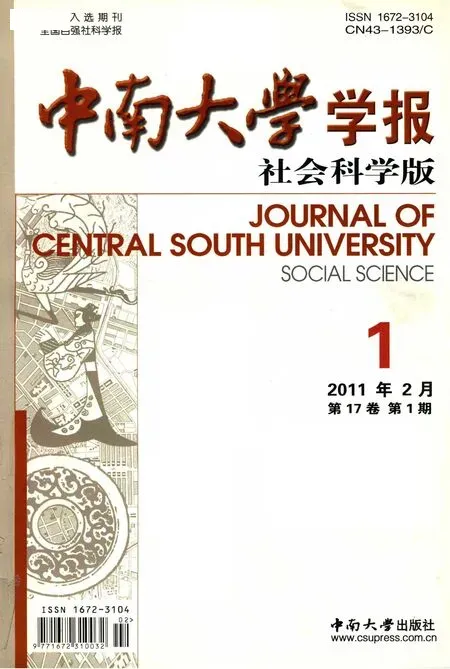政法委与纠纷解决资源的整合
冯之东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政法委与纠纷解决资源的整合
冯之东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因社会纠纷复杂多发,而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单兵作战”效果欠佳,整合既有的纠纷解决资源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内的当务之急。主要依照政治逻辑进行运作的政法委依托于体制优势,基于其职能定位和运作方式,成为执政者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达致“整合资源、维护稳定”这一执政目标的现实选择,而由其组织实施的“会商研判”“联合办案”则成为实现该制度预期的一种有效方式。
转型社会;政法委;纠纷解决;资源整合
一、引言:纠纷解决资源的整合——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需要
现代文明孕育着和谐,但现代化的进程却孳生着动荡。利益最大化和资源相对稀缺之间的固有张力,导致了社会纠纷的无处不在。而在当下中国,因处于体制变革、社会转型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的特定历史阶段,在这固有张力恒常性地发生作用的基础上,源于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所引发的各种新型利益争端也是层出不穷。尽管诉讼、调解、仲裁、和解、复议等当世所有的“解纷”②机制,几乎一应俱全地在中国实现了“制度化”和“典章化”,尽管包括各类机制、制度、机构、主体以及手段、方式在内的“解纷资源”被不同部门和机构为落实“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履行“稳定”这一头等“责任”,而广泛地运用和践行于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之中,尽管难以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纠纷的演变情况作出精确描述和最终结论,但法院审结的诉讼案件数量、信访机关受理的案件类型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行为激烈程度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却真实地映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解纷效果并不尽如人意。③
究竟原因何在?
显然,面对严峻异常且亟待改观的中国社会治理现状,执政者必须尽快找寻到根源所在及其应对措施。社会治理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相对于社会的潜在需求而言,国家可能提供的正式解纷机制永远是不足的”。[1]笔者以为,制度体系内“制度的缺位”,或制度实践中“制度的非正义”,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制度供给上的“不足”。然而,由于制度自身的惯性和制度变迁的渐进性难以逆转和改变,无论是健全既有解纷机制,以弥补“制度的缺位”,还是革新现行解纷制度,以矫正“制度的非正义”,都必将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而对于社会转型、纠纷积聚且亟待解决的当下中国是不现实的。基于这种短期内做不到、长期内又拖不起的现状,执政者为避免各项解纷制度的“单兵作战”,在改良现有制度、倡导构建“多元化解纷机制”的基础上,开始着力强调要积极利用政治优势,“充分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化解矛盾纠纷”。④在执政者看来,既然“短平快”式的更新替代一时难以完成,那就对既有制度资源进行整体性统筹和综合性利用,实现对其的科学整合,以有效应对时艰。
执政者的上述判断,既可以被视为其对现实解纷战略的必要调整,更可以看作是对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现状的及时回应。中国的社会现实表明,既有制度的单打独斗无法满足执政者和广大民众的需求;同时,解纷制度的多元化也必然蕴藉着不同制度之间功能整合的内在需求。各种解纷制度应当有机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而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2]无疑,法律人在关注“国家法律规则如何解决纠纷、国家法律规则不周的情形下如何改善规则”等问题的同时,还须深入探究在国家立法以外“实现善治的其它规范和行动”,[3]还须深入探究能够有效“整合解纷资源”的具体路径与担当这一历史性重任的制度和机构。即在法治的基本框架内,如何借助执政者所独有的政治优势,由特定部门或机构合理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对具体纠纷进行分析研判,对各类解纷资源进行科学重组,相机实施政治、法律、行政、经济等解纷手段,适时采取诉讼、复议、调解、仲裁等解纷制度,或单独行使,或综合运用,或使一种解纷手段从一而终,或将多种解纷制度衔接转换,以最终实现定分止争的社会治理目标。此即本文研究“政法委”的旨趣所在。
因此就本文而言,笔者无意探求如何改良既有的解纷制度,也无意分析政法委的内在制度机理,而是试图基于上述认识,进一步明确“整合解纷资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借助于具体的实证考察,进而分析政法委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制度预期和职能作用,以求证政法委整合解纷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功能。
二、政法委的制度预期和职能定位——整合解纷资源的视角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对既有解纷资源加以整合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最高司法机关就曾提出过“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这一“整合”性质的理念。⑤只不过,要想真正实现对既有各类解纷资源的全面整合,超越而不局限于“司法诉讼”和“法院调解”之间的“调判结合”,仅凭借权威不彰的司法权之一己之力很难达致预期目标。因此,就非常需要由政治性的制度设计统筹协调各类解纷资源。
(一) “综治维稳”职能的强化——整合解纷资源的制度依靠
在“政法实务”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是执政者赋予政法委的核心职能。笔者将之大致概括为:对政法部门进行思想领导;依据执政者的阶段性政策重点,部署政法工作;管理政法干部;领导综治维稳;实施执法监督。⑥需要注意的是,依托于执政地位和体制优势,执政者为有效因应“维护社会稳定”之时势所需,已经在实践中赋予政法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之基本职能以新的内涵,为其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整合解纷资源”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基础。显然,在解纷机制应对失灵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基于制度“理性”对既有职能进行适度调整和加强,这也是执政者重新配置政治资源、改善社会治理效果、进而巩固执政地位的一种努力。
根据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安形势,执政者取法防治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经验,提出了“综治”方略:在各级党政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协调全社会各方力量,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⑦1991年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综治委”)及其常设办事机构“综治办”。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企业改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十分突出,“关注民生、维稳促和谐”成为主流基调。在此背景下,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重要企事业单位都设置了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的“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常设办事机构——“维稳办”。
在当下具体的职能运作和制度实践中,各级“综治委”和“维稳领导小组”分别协助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综治和维稳工作。两机构的“主任”和“组长”通常均由同级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办”和“维稳办”负责人通常均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两办”均与同级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为其内设机构。出于职能要求,“综治”和“维稳”工作必然全方位涉足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而占有各类解纷资源的各类部门和组织几乎都是“综治”或“维稳”机构的成员单位。而作为只存在于文件之中而从未被实体化的机构,“综治委”和“维稳领导小组”二者均须始终通过“综治办”和“维稳办”协调包括党政军群、公检法司、民族宗教、科教文卫、财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成员单位”来行使权力,发挥功能。由于执政者确定了政法委机关同“综治”和“维稳”机构之间的特殊权责关系,政法委才能以特殊方式履行并强化着这一职能。
就具体职能而言,综治与维稳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重在排查化解纠纷、防控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开展平安建设;而后者重在及时发现和准确掌握影响稳定的情报信息和重点问题,制定重大事件处置预案和维稳工作方案,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达10人以上)。在综治办或维稳办的统一协调下,各相关部门既须化解本领域的纠纷,维护本系统的稳定,还要根据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总体形势,依照整体部署进行配合行动。特别是在超出政法职能范围的领域,以“综治”或“维稳”而非“政法”的名义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更加“名正言顺”,力度更大,效果自然也更好。这也正是综治和维稳的优势所在。显然,政法委正是以“综治”和“维稳”的运作模式作为制度依靠,在整合资源、化解纠纷和维护稳定方面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二) 一贯的制度性期待
政法委的职能定位虽然依时势更迭而调整,但它并未脱离“维护稳定”这个自始如一的制度性期待。这既是各权力在政法场域相互博弈的结果,更是转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尽管执政者历来主张,“政法部门系国家安危于一半,政法工作的领导权须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手里”,⑧但据此履行“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职能的政法委,其通过协调个案直接介入微观司法界域的做法,终究因其有“干预司法”之嫌,还是遭到了源自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的强烈抵制和排斥。政法委自身也因应时势之需,于世纪之交开始,日益淡化了其“干预”司法个案的意图和做法。⑨之所以会在中国的政法治理场域出现如此情境,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不排除诸如“司法权的日趋专业化”、“‘司法独立’的强烈呼声”、“社会法治意识的逐步增强”等一系列“政治正确”的原因,但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因素。
从“政法委”的角度出发,它必须正视自始存在于由执政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元素构成的公权力格局中的内在张力。如若无视此种“张力”以及形成于其上的相互博弈,势必会有损于既有公权力结构的宪政地位;触动这一底线,在高呼“依法执政”的当下,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而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日益现实且理性的政法委深知其中的“利害”。基于执政者的制度性期待,它已不愿再直接干预具体个案。因为,对微观领域的过多涉足不但会引发社会对政法委的质疑和诟病,而且介入个案的“小打小闹”,还会导致政法委混淆角色、迷失身份,进而影响其制度性功能在宏观领域的整体发挥。很显然,在宏大且复杂的社会治理进程中,执政者不愿意看到“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负面效应。
笔者以为,廓清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政法委对其职能运作方式的必要调整。在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群体性或政治性事件多发的当下,出于维系和重构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政法委的制度逻辑在弱化“介入个案”的同时,又使其另一内置角色得以强化:通过“统筹”“协调”的体制内手段,逐渐加强整合解纷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功能,并使其自身成为主导该领域工作的当然机构。尽管通常意义上的解纷机制并不包括政法委制度,尽管前文所述的职能定位仅仅是依托于执政者制发的党内文件而非法律文本,尽管执政者也从未正式且明确地主张必须由“政法委”来整合现有解纷资源,但实然中的政法委却依凭执政者的官方定位、“软法”⑩性质的文本依据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义不容辞”地在“解纷、维稳”这一舞台上代表执政者扮演着“主角”。虽然政法委还必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选择,但在制度调整和组织变迁的过程中,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定了发展路径,其必然沿着既定路径继续强势前行,进而实现执政者所期待的自我强化和完善。
三、“会商研判”和“联合办案”模式——对政法委整合解纷资源的具体考察
客观地讲,眼下的政法委在解纷实践中对解纷资源的整合依然处于不断探索、不断求证的初始阶段。虽然在其过往的工作实践中已不乏“整合”的迹象和做法,但均未能达致“制度”或“机制”的程度和境界,依然处于自发而非自觉的层面上。当然,尽管仍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汲取,但不容否认的是,实践中所涌现的个别亮点也的确有必要加以肯定。其中,在前述一般职能定位的基础上,对“会商研判”“联合办案”这一特定模式的运用,就成为了政法委整合解纷资源的有效之举。
(一) 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具体运用
就实际情况而言,“会商研判”和“联合办案”是一组经常被执政者运用于执政实践的工作模式。在解纷领域,即是指政法委在以“排查调处纠纷”为核心目标的社会治理进程中,用于整合解纷资源、有效解决纠纷的相辅相成、首尾相顾的工作机制。在其实际运行中,往往根据纠纷的性质及特点,由综治办或维稳办以“工作组”或“联席会议”的形式来具体操作。“会商研判”着重在纠纷的“排查”环节,即在综治或维稳机构的组织下,由联席会议的各成员单位及其成员发挥自身职业优势,针对带有行业性、区域性、时段性等特点的倾向性纠纷,经共同协商讨论,进而分析其来龙去脉,判断其基本性质,预测其发展趋势,并研究解决策略。“联合办案”着重在纠纷的“调处”环节,即针对涉及多重关系的复杂纠纷,由工作组依托成员多元的优势,共同参与研究对策,并由本级政法委协同相关部门,确定解决纠纷的牵头主办机构和辅助协办机构,提出解决方式和解决时限,适时采取法律、行政、经济乃至于思想教育和心理开导等多种手段,引导民众通过对复议、诉讼、仲裁、和解等救济途径的选择性适用以化解纠纷,合理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方式,及时协调不同主体间的权利(力)义务关系,并使之达致一种稳定的状态。因此,“会商研判”是“联合办案”的基本前提,而“联合办案”是“会商研判”的最终目的。
为充分说明“会商研判”“联合办案”这一特殊模式的特殊作用,笔者在下面将以一省际边界纠纷案件案件为例加以阐释:
H省的V县与A省下辖的两县相邻,边界长达97公里。由晚清至今,在这一发展滞后、以畜牧业为基本经济命脉、几乎全民信教的民族自治区域里,因草山草场划界、盗抢牲畜等问题而引发的两省以及H省内部牧民之间的纠纷乃至械斗常年不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仅群体性械斗致死者就达23名,而每一次械斗中的伤亡人员及其家人亲朋则又成为积极发起或参与下一次械斗的始作俑者或中坚力量。因该类纠纷以及其他大部分争端多发生于省际边界区域,且又涉及民族宗教因素,当地法院以及其他诸如公安派出所、乡镇司法所等政法力量和解纷机构均无力单独介入;司法诉讼、行政裁决、人民调解等解纷制度或方式的单一运用均无济于事;同时,由于当地民众“轻法厌讼”的陈年积习,几十年来,众多纠纷当事人和受害人几乎无一诉诸于上述机构和渠道来解决既有纠纷、实现权利救济。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当地的不少牧民缘于贫困或因械斗致残,为维持生计而逐渐开始从事吸食贩卖毒品、仿造贩卖枪支等犯罪行为。
对于地方当局而言,上述情境无疑是相当严峻的。尽管我们不能说这一切就直接根源于该地牧民的“好勇斗狠”。但无可否认,这里既有长期械斗、伤及人命的严酷历史背景,又有跨省越界、涉及民族宗教等多重敏感因素的现实状况;既有经费短缺、装备落后、警力不足的执法困境,又有物质层面上长期的贫困落后和意识层面上严重的“轻法厌讼”。以上各种因素使得既有的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法制化的“常规性机构”,在单一运用诉讼、调解、裁决等法制化的“常规性途径”的情况下,均无法有效改变上述现状。显然,无论是为了践行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还是为了完成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第一要务”,地方当局面对此情此景,都必须有所作为。
2009年8月,H省V县综治办依照县委政法委制定的总体方案,在动员当地宗教界人士做好辖区牧民思想工作的同时,组织了由政法、财政、宗教管理、民政和农牧等部门人员参加的“专门工作组”,主动前往与之相邻的A省两县,就解决上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与对方进行沟通协商。双方结合区域实际,对相关纠纷的成因、性质、发展趋向和解决方案等环节进行会商讨论和分析研判,在解决纠纷的途径和办法上寻求共识。V县先后与A省两县签订了《边界地区治安联防协作协议书》,借助相互之间的“治安协作”进行联防联治,以实现双方对纠纷的“早发现、早处理、早控制”,共建平安边界。面对当地民众“轻法厌讼”而笃信宗教的实际,双方共同筹建了“边界纠纷协调小组”,由相邻各县综治部门负责人和当地宗教界人士构成,以共同协调处理跨界纠纷。与此类似,H省政法委还同相邻的A省和B省建立了妥善处置跨区域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协作机制,形成了“整体联动共防、信息情报共享”的工作格局,以共同打造“AHB三省边界地区平安走廊”。
同时,V县为实现源头治理,以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稳定,还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政法委书记将“专门工作组”的实际工作向V县党委作了专题汇报,以争取县党政领导班子的体制支持,特别是实现了人员编制和经费拨款的增加,补充和培训警力、添置和更新设备,以进一步加强牧区在解纷领域特别是政法系统的整体建设,干部结构(主要表现于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之间的人数比例和职级配备)将更趋合理化;其次,经专门工作组的统筹协调,县公安、法院、司法、宗教管理、农牧等部门以及“寺管会”(当地寺院内部成立的自治体)等组织,区别实际纠纷的不同类型,分别对之采取了处罚、司法裁判、调解等方式,及时明确了具体纠纷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实现定纷止争;最后,也是最有特色的,即由政法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为本县区域内病残、贫困的牧民家庭解决了牲畜配种改良、子女入学、享受病残社会保障等实际存在的民生问题,从而降低了其因病残、贫困而违法犯罪、引发纠纷、危害社会的几率。现实表明,H省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做法的确化解了一批积淀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矛盾纠纷,实现了预期目标。
(二) 对该模式的评析
显然,这是一个应予积极认可的理想结局,但其过程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讨论。上文已述,面对复杂难解的现实纠纷,“常规性”机构和途径的单一化行使,收效甚微。基于此,地方政法委及时调整策略,借助对各项既有制度资源的整合,取得了前述的良好效果。其中,有两点值得肯定并应推而广之。
第一,对宗教因素的巧妙利用。在因长期械斗而充满了血腥味的那个特定时段,V县的矛盾纠纷之所以复杂难解,尽管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令当地执法部门头疼和棘手的还是其中的民族和宗教因素。其实,在当地行使公权力的执法队伍里,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甚至即便是部分汉族干部,对当地民族语言和民族习俗也颇为熟知。按理说,这本是当地可以充分利用的社会治理资源。但出于对“宗教”这一敏感因素的忌惮和顾虑,他们还是惟恐越雷池一步,难以介入或不敢直接介入具体的矛盾纠纷,担心引火烧身。但地方政法委富有智慧地化不利为有利,不但没有回避宗教因素,而是运用各种策略,充分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全民信教的基本“县情”,在借助国家力量通过正式途径进行普法宣传的同时,积极邀请在当地深孚众望、颇具影响力的“高僧大德”,由他们向广大牧民宣讲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民族宗教政策,并大力宣扬国家的法律政策与宗教教义的兼容性和一致性,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单纯由当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法取得的社会治理效果。
第二,对国家法律政策的一体遵行和制度资源的有机整合。虽然前述的“常规性机构”及其“常规性途径”在当地执政者调整策略之前,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但V县政法委并没有因此在调整策略之后就轻视其既有的制度性功能,而是充分借助党政权威,有效发挥执政者所独有的体制性优势,积极整合了既有的、与解决上述纠纷有关的机构和部门,将“常规性机构”重整为“专门工作组”——特定情势下的“特种部队”。因此,各种解纷资源实现了有机整合,最终一改昔日“单兵作战”的无果而终,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执政者所期待的“制度性收益”。当然,其中最令人称道的还是,在为此“多赢”结局而努力的过程中,就当地施政者所秉持的基本社会治理依据而言,除了“刚性”的法律和政策之外,还包括“善恶有报”的乡民社会的公序良俗,以及更富人情味的、当地牧民更易接受的、以追求和谐正义为宗旨的宗教教义;同时,从策略的调整、方案的实施,直到各类纠纷的化解,各个环节都在国家现行法律和政策框架之内进行。笔者以为,在上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已经初步体现出了治理主体、治理依据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此种情境,完全契合于我们所追求的“公共治理”的基本精神。
当然,上述解纷过程及其结果的正当性还是存在令人质疑之处:政法委借助“综治”机构所主导的解纷活动是否做到了足够的公开和透明? 整个解纷过程是否遵行了基本的正当程序? 是否存在着对公共利益的无原则让渡? 是否存在着强势的公权力通过“合谋”对纠纷当事人,特别是弱势的牧民一方进行压制的情形?等等。对于社会以及广大民众而言,类似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得而知的谜团。显然,如果立足于批判的眼光,从基本法理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上述一案充斥着“党政不分”“政法不分”抑或“党法不分”的现象;更有公益与私益、权利与权力、实体与程序、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等多重范畴之间的“冲突抵触”和“此消彼长”。无可否认,该案几乎就是地方政法委以及综治机构借助于党政权威所上演的一出“独角戏”,法治的痕迹已相当淡薄。因此,上述各类质疑都有其合理性。
但同时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角度对之进行观察,就可以看到,贯穿于这一解纷过程之始终的便是执政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威之间的互助与互动,以及上述公权力主体与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妥协与博弈。必须看到,该案所涉及的系列问题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综合因素,在当下还不是很理想的法治环境中,寄望于一次解纷实践就将其全部“搞掂”是根本不现实的。同时,地方施政者也决不可能因为纠纷的相关法律问题未能得以全盘解决,而在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严重影响和危害社会秩序的复杂纠纷时就无动于衷,更不能将现成的众多执政资源闲置不用而坐等纠纷的进一步恶化、秩序的进一步失范。相反,笔者以为,政法委借助于现行制度赋予相关机构所特有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化解了纠纷,维护了秩序,这才是最为紧要、也最值得肯定的“硬道理”。因为,我们期望中的法治抑或善治的理想境界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无序的社会环境之中。显而易见,我们无法超越当下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在这一基本前提下,上述那种“纷纷扰扰”的解纷过程正是社会治理实践中真实且必然的内容,正是我们迈向理想之治的、充满坎坷的征途中必须加以正视的风景,尽管它并不是那么亮丽。
显然,作为政法委发挥整合解纷资源之功能的具体体现,“会商研判”和“联合办案”的模式使多元权力、机制和机构等各类资源之间形成有机协作,呈现出单一资源无以达致的积极效应。特别是与政法委合署办公的“综治办”和“维稳办”,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其他机构无以替代的作用。前述“省级边界纠纷”充分说明了作为政法委整合解纷资源的制度依靠,综治机构的独特功能。当然,对此工作模式也有质疑的声音:即便是面对复杂纠纷,动辄就“联合办案”“会商研判”,是否有兴师动众、“浪费资源”之嫌? 对此,正如笔者前文所述,现有的解纷资源在面对转型时期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社会纠纷时,与其“单打独斗”无果而终,还不如协调整合,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只有将纠纷及时妥当解决,使社会关系尽早恢复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节约社会治理资源。
(三) 解纷资源整合与法治的关系——政法委及其职能运作的边界
必须承认,任何制度都会导致制度内权力主体之间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进而导致权力关系的失衡。由于单纯在法律框架内无法解决这种失衡,则借助于法律之外的途径就成为必要。[4]无疑,欲实现执政行为与法治之间的平衡,就必须避免类似于因“党政分开”之表述过于简单化而造成的理论模糊和实践混乱。诚然,不论是作为制度,还是作为机构,亟待规范化的“政法委”确有为人诟病之处,但允许我们默认一种瑕疵制度的前提就是因为尚无更好的制度。
现实已经表明,单纯依赖通常意义上的法治无法从根本上有效化解纠纷,在初行法治的中国更是如此。在司法权威严重缺失的同时,“程序正义”的理念和制度又因与生俱来的“机械性”而缺乏社会鉴别力和应变力,因而需要特殊制度装置加以“功能补强”。我们固然无法完全摒弃形式意义的“法制”而另起炉灶,但通过实质意义的“政制”建构以弥补前者,并实现二者的规范性衔接,显然也是制度理性的本质内容。况且,关乎社会稳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种个案化、“切片式”的法律问题,而且还是涉及执政体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无论是作为政治实践中的显性制度,还是作为法治实践中的隐性制度,集双重角色于一身的政法委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已经使其具备了在中国政法实践中担当历史性重任的基本“资质”。政法委正是通过这种对司法权的 “补强”,不但提供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和法治双重性质的动力,更是超越了一般法治的范式束缚。
显然,法治的重点应该是为有利于增进公众福祉的公域之治构架一种基础性机制,而不应只是单纯地局限于“规约公权力和控制自由裁量权”之类的老生常谈;而执政体制下的政法委及其职能必须在特定的权力边界内运作,不能取代、更不能僭越既有的法律制度,即便它的确曾效果显著。我们必须正视政法委在履行职能特别是在实施类似“运动式执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对政法委之职能和权力加以科学配置和有效监督,对需由其介入并解决的纠纷加以明确界定,使之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以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态势,科学推进“法治”这一规则之治。
基于此,笔者以为,必须界定政法委在解纷实践中的权力边界,必须廓清需由其整合解纷资源加以解决的纠纷范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尽管如前文所述,政法委现已不大直接干预司法、介入个案了,但基于对公权力的忌惮,执政者必须把握“现有解纷制度解决在前、政法委协调整合在后”的基本原则,不宜由政法委直接介入具体的纠纷之中,更不宜“率先”直接介入特定纠纷,必须根据纠纷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先行通过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解纷途径,力争纠纷的化解;只有当特定纠纷在国家司法机关或其他解纷途径都无力单独解决之时,政法委才可以介入该纠纷。
而就需由政法委协调解决的纠纷而言,一般只能是那些对于现行单一解纷制度来说,特别难啃的“硬骨头”:或纠纷案情复杂,或涉案人数众多,或牵涉到方方面面,或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交织,或法律和政策规定都不尽明确,甚或相互抵触……,或以上各种因素兼而有之;当然,也不排除下述情形:虽然不是具备上述诸要素的疑难杂症式的复杂纠纷,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动用了现有解纷制度、甚或已穷尽了现有的权利救济渠道之后,纠纷仍然未能得以化解,以至于此种久拖不决的争端严重影响到了当事人的生产生活或严重威胁到了局部的社会秩序。总之,需要政法委整合解纷资源并加以最终解决的纠纷,应大致限定在上述范围之内。
即便如此,政法委在介入特定纠纷之后,也不能对具体解纷程序、解纷手段和解纷人员进行干涉,更不能以“政治大局”的名义而凌驾于法律规则之上,而是只能限于从宏观整体上组织、协调相关的机制和机构,充分利用其优势和功能,尽力避免其缺陷和弊端,以实现最终的定纷止争,实现对原有社会关系的恢复。事实上,对于极度复杂难解的个别纠纷,有时即便是政法委亲自出马,也可能是无计可施。但无论如何,对于政法委既定制度性功能的合理开掘,毕竟是执政者在法治框架下,借助执政权威,对现行体制范围内既有执政资源的一种必要选择和运用。因此,不论是基于纠纷当事人为化解纠纷、救济权利而提出的申请,还是基于执政者为改良社会治理现状而做出的决定,政法委都必须认真对待特定具体的纠纷,认真对待纠纷当事人的主观诉求,而决不能轻举妄动。换言之,在当下中国的具体解纷实践中,在既有的解纷谱系之内,政法委只能担当其他各类解纷制度的“替补”角色(类似于篮球比赛中的“最佳第六人”):在现有解纷制度发挥作用之时,决不可越俎代庖而僭越成为“主力”;只有在“主力状态不佳”或在解纷实践确有需要之时,方可一显身手。
中国社会治理的事实已多次表明,政法委在履行职能之时,也的确曾频频越界。特别是各级施政者为了追求“维稳”之政绩,都在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强化政法委的职能,促使其通过有效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以实现社会的和谐。这种政治使命的赋予,在加强政法委政治责任感的同时,也极易引发其产生功利性的动机和心态,使其更有可能、也更有机会以不正当手段“摆平”纠纷,以追求息事宁人的“刚性和谐”:为实现一时的“稳定”,时而偏袒一方、打压一方,时而违背法律政策、随意承诺、“乱开口子”,时而滥用警力、激化矛盾,此类越权、滥权之行为,都极易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开展各种专项行动的“运动式执政”过程中,与其阶段性、随意性等特点相伴随的就是,在“运动”进行之时,各类权力主体多头并存,看似分工明晰,实则互相推诿、无人负责;而“运动”一旦结束,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至于连当事人在其合法权益受损后的“鸣冤叫屈”都已无人问津。显而易见,如果对上述问题熟视无睹,必将给执政者带来事与愿违的直接后果,而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及权利急需救济的纠纷当事人。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我们不能单纯从域外视角审视中国制度,更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制度,但权力的“相互制衡”和“司法独立”,是可资借鉴的人类法治建设历程中的文明成果。中国执政者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执政党,基于“依法执政”的本质要求,必须对此持客观审慎的态度。无疑,政法委等政治性制度设计在对解纷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之时,须以法治为基础,惟有此才能更加符合社会和法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四、结语:可欲而可求——法治框架下社会治理的政治考量
如上所述,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矛盾纠纷无论是性质与数量,还是内容与形式,都早已今非昔比。在社会主体多元、利益分配不均的社会转型期内,在社会秩序局部失范、执政能力亟需提升的政治情境下,一边是国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求“维稳”——“花钱买平安”,一边却是“民怨”犹存,“社会泄愤事件”不断。同时,当下中国的执政理念和法治实践时而对诉讼制赞誉有加,时而对“ADR”推崇备至;社会思潮时而钟情于法律制度,时而寄望于政治权力,而矛盾纠纷的多发和激变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反复不定。因此,严峻的社会现实根本就不允许执政者慢条斯理、按部就班地对各类解纷制度进行常态化、程式化、制度化的拾遗补缺。可行的途径就是,设法在已有的制度资源上作出“新文章”,找寻并挖掘出新的“制度收益增长点”,以最终避免社会情势的失控。这也是当下中国绝不会改变和消失、更不容忽视和质疑的社会治理前提。是故,基于历史形成的运作方式和执政者所赋予的职能定位,“政法委”就水到渠成地被推到了社会治理实践的前台,责无旁贷地成为新时期代表执政者完成整合解纷资源、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历史性重任的担当者。
显然,任何制度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应把不同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不同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5]因此,我们不可能更无必要与西方亦步亦趋,而应在借鉴域外先进制度与理论的同时,注重对本土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以此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本文从当下中国社会的解纷现状出发,立基于政法委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模式,结合个案就“政法委”整合解纷资源之功能和价值进行了论述。毫无疑问,在进行制度研究时,不能仅仅从制度结构和法律文本出发作肤浅的分析,还应当关注制度和文本得以呈现的源动力。无论是从微观具体的机构层面,还是从宏观抽象的制度层面,对政法委及其制度模式与法治之关系的考量和规范,都必须以对政法委制度实践与法治原理要旨的学理分析和实证调查为原点。转型社会的现实情境,既为其调整职能、转换角色带来了绝佳机遇,更为其整合解纷资源、维护社会稳定赋予了艰巨使命。虽然制度自身的先天不足带来了种种与其设立初衷相左甚至对立于现代法治的惯常性后果,但“机遇”和“使命”所催生的“制度变迁”,既为社会所亟需,也为执政者所倚重。
无疑,政治性的执政行为需要法治加以规范,而追求“程序正当”的经典法治也需要政治力量加以补充。“为构建功能性相互依存的社会,执政者需要发挥整合机制的作用”。[6]由于现代法律试图使复杂社会处于稳定状态,不得不将自身变得日益抽象。但这种抽象性在使法律为各种预期提供更大可能性的同时,也使法律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时呈现出持续退缩的状态。因为法律只能逐步渐次地回应社会需求,而且这种回应必然总是“慢半拍”的。此时,不同于法律制度的政治制度及其工作模式便会应时之需而“闪亮登场”,因为有效回应社会需求既是国家政权有序运行的需要,更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要求。因此,公法学者决不能一味“严格恪守某个既定信念、原理或原则”,更不能“以此信念、原理或原则,削足适履般地去要求气象万千的现实。”[2]否则,我们就可能将经典原理变成恐怖的“普罗克汝斯特斯(Procrustean)之床”。
致谢:
在笔者的写作过程中,北大法学院沈岿教授对于本文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同时,也有幸得到了政法实务界孙治强和田富元的多方面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中不当及谬误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注释:
① 语出自清末重臣李鸿章的《筹建海防折》。
② 为叙述方便,笔者在本文中将“纠纷解决”称为“解纷”,如“解纷资源”“解纷机制”等。
③ 以群体性事件为例,现已从1993年的8709起增加到了2009年的9万余起。其中,因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于建嵘:《2010年社会矛盾预测及建议》,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3期。
④ 文本意义上的标志就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9年年初联名转发了《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中办发(2009)3号)。
⑤ 从2005年到2008年4年间,最高人民法院连续4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均提出过这一说法。朱雨晨:《法院高调解结案率背后的隐忧》,载《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年6月11日,第三版。
⑥ 可参见“中国平安网”有关中央政法委“职责任务”的信息。
⑦ 1978年是“文革”后违法犯罪的第一个高峰期。原有的治安工作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成因极其复杂,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不是某几个部门在短期内就能完全解决的。因此,需要一种长期综合性方略。倪小宇等:《改革开放30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展历程》,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 年第6期。
⑧ “政法部门”是执政者对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等部门的统称;广义上,也包括政法委在内。1990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并适当调整其职能任务。并指出:“政法部门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是党和人民手中的‘枪杆子’,政法部门是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载《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98-1006页。
⑨ 在基层政法委尤其突出。周颖、李文俊:《司法视野下的政法委》,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1期。
⑩ 中国的法治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公共治理绝不能单纯建构于具有程序性、可诉性和强制约束力等特征的“硬法”(hard law)之上,而是还须依托于具有开放性、可选择性、非强制性、不可诉性、形式多样性等特征的“软法”(soft law),即软硬兼施、刚柔并济。这一点在政法领域中有着非常生动的体现。关于“软法”的相关理论,可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 苏力. 关于海瑞定理Ⅰ[C]//法律和社会科学(第四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2] 韩春晖. 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3] 沈岿. 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J]. 宪政手稿,2008, (2): 1−29.
[4] 大卫•席尔斯. 社会心理学[M]. 黄安邦译. 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426.
[5] 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
[6] 马丁·洛克林. 公法与政治理论[M]. 郑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52.
Abstract: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multiple social disputes and the inefficacy resulted from lacking in cooperation among the exist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tegrating existing resources of dispute resolution has become a priori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a realistic choic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tegrating resources of dispute resolution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ruling authorities in its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Committee of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Affairs (CPLA) develops and oper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tical logic,which relies on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is based on its functions and mode of operation. “The Consulting analysis and judgments” and “the joint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ing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CPLA are the effective ways to attain the above ruling goals.
Key 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 Committee of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Affairs; dispute resolution;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he Committee of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affairs and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of dispute resolution
FENG Zhidong
(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D926
A
1672-3104(2011)01−0042−08
2010−08−25
冯之东(1976−),男,甘肃靖远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编辑: 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