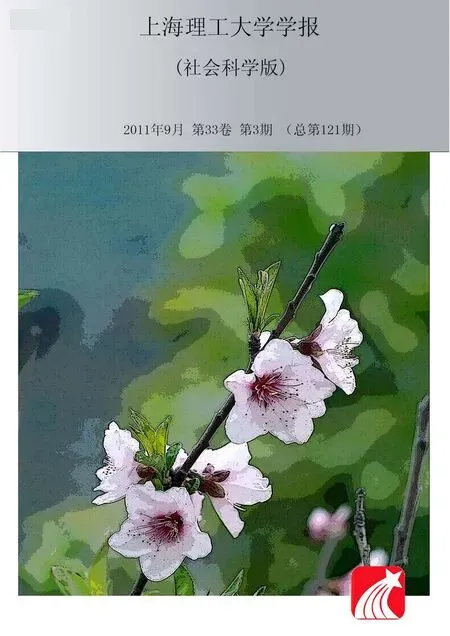我国人权发展话语分析:以“他是同志”为例
左 飚
(上海建桥学院 外语系,上海 201319)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一个跨学科研究课题,或者说是在学科交叉点上的研究课题,被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等交叉学科的学者们用来描述各种言语行为,解释单一学科无法解释清楚的某些现象。学科是人为划分的,而科学及社会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学科交叉研究有利于人们提高认识水平,解决重大的科学和社会问题。布朗和尤尔指出:Sociolinguists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 ith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manifested in conversation,and their descriptions emphasize features of social context which are particularly amenable to sociological classification[1].可见,社会语言学家们特别关注的是话语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及表现在话语中的各种社会要素的互相作用(social interaction)。本文旨在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的粗浅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通过追索话语的语义变化,剖析我国人权发展状况,阐明话语与社会情境互相作用的关系。
一、不同情况及语境下的话语意义
语言学家科克把话语定义为language in use for communication,强调其应用性和交际性[2]。麦卡锡认为,话语分析的重点是the close observ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alk and patterns which recur over a w ide range of natural data,也就是说,应该关注话语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广泛现实生活资料中反复出现的言语模式[3]。社会语言学家福柯认为,“一个正确的句子未必有意义,而一个不正确的句子未必没有意义;一句陈述的意义取决于它出现与存在的情境,取决于它的上下文”[4]。福柯强调话语的情境。以下三段话语中都有一个相同的句子 It’s 6:05 now,但由于说话的情境和语境不同,相同的句子却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含义,隐示了说话者不同的言语行为。
话语一
(In the airport departure lounge)
A:Stephen hasn’t come yet,but the plane w ill take off at 6:40.
B:It’s 6:05 now.(含义:他来不及办理登机手续了。言语行为:抱怨。)
话语二
(At the airport exit)
A:Thank Goodness,we’ll soon see Stephen.The plane is said to arrive at 6:40.
B:It’s 6:05 now.(含义:我们来接机的时间还是够早的。言语行为:宽慰。)
话语三
(In a bookstore inside the airport)
A:Stephen said he would come to join us around 6:40.We’ll have enough time discussing what book to buy.
B:It’s 6:05 now.(含义:是的,买书时间还算充裕。言语行为:同意。)
可以从上述话语中看出话语情境与话语意义及话语参与者行为的关系。同样,根据社会语言学家的观点,静态、孤立地看“他是同志”这句话,它仅是一个包含主语和谓语,语法结构完整、正确的句子;但如果不交代它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也没有上下文,则不能表示任何确切的意义,不能说明说话人的行为,也就不存在任何交际价值,因而就不能称之为通常所说的跨越语言学和社会学的概念“话语”。然而,一旦把这句话放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考察,就不难发现,这句话有着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情境密切相关的丰富含义,成了具有很高交际价值的“话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及政治和社会情境的变化,这个“话语”的含义也发生了相应的窄化、丰化甚至本质的变化,而且这“话语”本身也参与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重建,并沉淀为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有趣的是,“他是同志”这一话语含义的变化,以微观见宏观,有效地见证并参与了我国人权发展的过程,成了人权发展话语分析的一个虽小而有力的论据。
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辞海》和《辞源》、香港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海外版)及台北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同志”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及春秋时代。左丘明所著《国语·晋语四》中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这里“同志”二字实际上意为“志同”,即“志趣相同”或“志向相同”的意思,是主述结构词组。记载周代职官礼法、物名制度的汇编《周礼》中就有“同志”二字的出现。汉朝郑玄在注《周礼》中说,“同志曰友”,“同志”指“朋友”、“志趣相同的人”。“同志”的这两个意义“志趣相同”和“志趣相同的人”,一个抽象,一个具体,前者是概念,后者指人,二者可看作“同志”的源头义,也是它的基本义、核心义,此后其意义的继续沿用或引申发展都源自于此。
本文拟把“他是同志”的话语意义变化与我国人权的发展过程相联系,放在四个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
二、“他是同志”话语意义变化的四个阶段
(一) 谋求人权(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外侮内乱,国运方蹇,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普通百姓别说选举、议政、安全、诉讼、平等、言论自由等权利轮不上,就连生存的基本权利都不能保障,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权利也被剥夺。“他是同志”往往是早期革命党人及后来的共产党人说明某人组织归属的话语,可指“他是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政治团体或政党的成员。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就互称同志,如黄葆桢的“春秋大复仇九世,同志寥落谁商量”(《杨哲商烈士悼歌》)。在孙中山的遗嘱里,有一句著名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引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的日伪统治区及国统区,“他是同志”往往是地下工作者证明某人特殊身份的密语,一旦泄露,必然使此人招致杀身之祸。
这一时期,我国的人权状况极其糟糕。普通百姓在饥寒中艰难度日,只能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革命党人和革命战士浴血奋战,谋求的是生存和信仰的权利;至于其他人权,则既无稳定的政权予以实施,也无可行的法律保障,可谓一片空白。另一方面,“他是同志”这一话语却强化了早期革命党人及共产党人的内部团结及对革命组织的忠诚。“同志”的这一意义很快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内广泛流行,并逐渐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共产党的报刊及大量反映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中频繁地使用这一词语,如高云览《小城春秋》:“新加入的党员和团员,虽然在社里经常跟剑平、四敏一起工作,却不知道他俩是他们的同志。”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内部,同志之间,不分性别年龄,不分职务高低,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情况下,话语“他是同志”带有政党或革命团体归属的含义和一定的保密性质,反映了劳苦民众通过斗争谋求人权的基本状况。
(二) 改善人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这一阶段新政权建立,万众欢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下而上地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在这一时期,尽管“人权”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观念而在国家政策或法律中不直接提及,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实际人权状况大为改善,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安全权、平等权等得到充分保障。
与此相应的是,“同志”的词义丰化,从“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扩展为“与之交往的任何普通人”,作为彼此之间的通称而被空前广泛地使用。在各类报刊、书籍、电影和文艺演出中,“同志”成了最带革命色彩的符号。它既是一般称呼,又在各种场合用作招呼语,人们几乎处处遇见同志,时时呼叫“同志”。“老同志”、“小同志”、“妇女同志”、“警察同志”、“医生同志”等等称呼不绝于耳,“同志”成了中国亿万人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有些北方地区的大姑娘扭秧歌时,爱唱“俺娘不给说婆家,俺就跟着个同志走”的歌词。“他是同志”这一话语失去了原先带有的政党或革命团体归属的含义和保密性质,几乎成了“他是老乡(或朋友、同事、好人、公民)”的代用语,反映了宽松和谐的政治局面及人人享受平等、受到尊重的人权状况。
(三) 践踏人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7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这一阶段极左思潮泛滥,政治民主及法制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处于史无前例的极大动荡之中,人权的底线、作为人的最起码权利——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基本生存——均被肆意践踏。造反派只要凭一纸诬告性“检举”、一份未经证实的材料甚或一种异想天开的“推理”就可以揪斗、关押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老叟妇孺皆难豁免。全国各个层次90%以上的管理者被定为“走资派”而莫名打倒,即使普通人不经意间把一幅头像倒置,也可能瞬间成为“反革命”,人人自危的局面使很多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封建血统论也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并变本加厉为祸人间,不仅侵犯了无数青年的人格尊严,还剥夺了他们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等应有权利。
在这一时期内,由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人们被分成了“人民”和“阶级敌人”非红即黑的两大阵营,“同志”二字常常成了敌我阵营的分界线。历次运动的对象自然不能称呼为“同志”,即使在党内,一旦某人作为敌我矛盾被揪了出来,从此便与“同志”无缘。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绝对化盛行年代,“同志”一朝被列入“非同志”,则如坠深渊,万劫不复;“非同志”被平反后成了“同志”,常激动不已,如重见光明。此时,“同志”一词的功能已远远超出其主要作为招呼语或称呼语的语言意义及社会功能,而承担着不应承担的政治重负。“他是同志”这一话语被赋予了“他是人民的一员(非阶级敌人)”的特殊含义,而“他不是同志”这一话语则成了结束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判决。不少蒙冤受屈的老干部听到“他是同志”这一鉴定时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但绝大部分人在十年浩劫中没有盼到这一相当于为他们平反昭雪的结论。刘少奇、彭德怀等大批建国功臣终究没能重新获得“同志”的称号而含冤离世。在这一时期,凡是涉及“人”的概念,如人性、人道、人情、人权等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观念而讳莫如深。人只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别,而人权则是无人论及也不敢论及的敏感话题。
(四) 促进和保障人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目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致力于改革开放,全国各行各业百废俱兴,蒸蒸日上。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促进和保障人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学术界开始了对人权问题的讨论和再认识。1991年11月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的发表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和认可,标志着中国在人权领域与国际社会交流和对话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相继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意味着我国在人权问题上进入了一个实质性推进阶段,因为一旦加入人权公约,中国就必须履行公约的义务,并切实采取措施保障人权,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2章第33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写入作为最高法的宪法,表明我国的法律体系将面临人权条款的全面审查,标志着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诸如工作权利、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健康权利、受教育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农民权益的保障等,以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包括人身权利、被羁押者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中国人权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发展。
在这一阶段我国人权状况迅速改善的同时,“他是同志”这一话语呈现出多义共存的局面,在很多场合依然保留普通招呼语的意义,在某些场合也还有“他是共产党员或革命军人”的含义,但已失去其在武装斗争时期的保密性质,反映了平等与自由受到尊重和保障的人权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同志”这一话语还悄悄地发生了语义变化,逐渐衍生出新的含义。“同志”作为人们彼此之间称呼语或招呼语的用法逐渐为先生、女士、师傅、小姐、老板等词语所替代,而它的一个新的词义——指同性恋者——则悄然出现,并随着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传播,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在笔者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把“他是同志”的话语含义理解为“他是同性恋者”的人数比例为:25岁以下受访者的86.9%,26岁至50岁受访者的56.8%,51岁以上受访者的15.6%。这一微妙的话语意义变化见证了我国人权状况的大幅度改善。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有关人性的各种权利(包括性取向)受到尊重。2001年4月20日,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不再把同性恋统划为病态。精神病学会为宽容同性恋行为消除了一个关键性障碍。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像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巴西、加拿大及新西兰等国那样承认同性恋的合法化,但这一先前被强制禁止的现象毕竟受到了宽容对待,获得了存在的权利。与此相应,1994年12月,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罪犯人权的体系也日趋完备,促进和保障人权的事业在这一阶段得以全方位的推进。
综上所述,“他是同志”的话语意义变化与我国人权发展过程的关系可归纳如表1(见下页)。

表1 话语“他是同志”与我国人权发展过程Tab.1 The semantic change of the discourse “He is a com 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三、结 论
福柯派话语理论者认为,话语是人们对社会生活进行表述的特定视角。话语不仅反映并受制于社会情境,而且积极建构了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费尔克拉夫(2003)指出,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或限制话语——的建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5]。实际上,“他是同志”这一话语,不仅反映了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境和人权状况,而且也积极参与建构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人权实践领域,成为当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例如,这一话语在第一阶段参与建构了共产党人及革命战士关于谋取生存权(“为人民谋解放”)的观念,并使这一观念深入到百姓之中,为建国后的人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第二阶段该话语使人人平等的权利意识和平等的人际关系沉淀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文革”阶段,“他是同志”这一话语的特殊政治意义,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权被践踏的程度,也强化了人们分清敌我的阶级斗争意识,淡化了人们的人权意识,参与建构了“人民”与“敌人”界限分明的二元社会结构。而当今阶段这一话语的多义共存,增强了人们的人权意识,扩大了人们的自由空间,参与建构了和谐、宽松、稳定的社会结构。
[1]Brown G,Yule G.Discourse Analys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2]Cook G.Discours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3]McCarthy M.Discourse Analysis for Language Teacher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4]Foucault M.The Archaeology of Know ledge[M].U.K.: Routledge,1969.
[5]Fairclough N.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