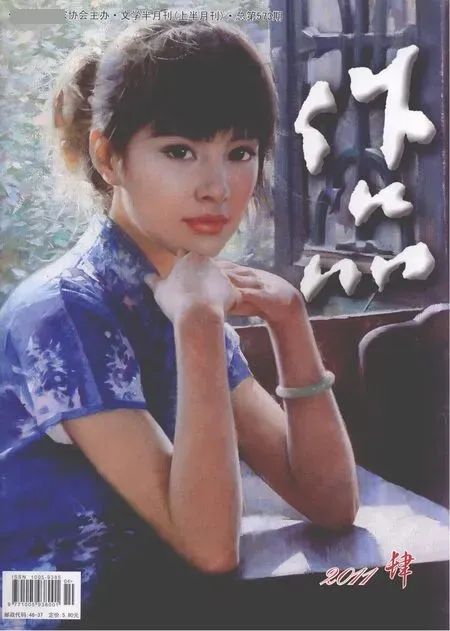天堂再见
◎滕肖澜
关大明出事那一刻,秦悦正在邮局打包一个国际邮件,同事小刘心急火燎地把电话交到她手上,“冷静,千万要冷静——”秦悦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听到电话那头交待完,心反倒不跳了,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完全僵了。
锅炉爆炸是在下午两点。一个新来的临时工违规操作,没将蒸压釜关紧就注入蒸汽,结果一加压,釜盖被蒸汽撞得喷起。临时工当场死亡。关大明和另外两名同事被炸伤。送入医院。
出租车上,秦悦通知了公公婆婆,还有自己的父母。她听到婆婆的尖叫声,忙不迭把电话挂了。她烦得很,又害怕得很,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也像锅炉般,几乎要爆炸了。司机几次回头朝她看,不用她开口,把车开得飞快。二十分钟的车程,十分钟就到了。
刚到手术室门口,便有一具尸体推了出来,蒙着头。秦悦还不及反应,旁边已有几个家属冲上去,哭天抢地。秦悦心里一松。厂里陪同的人迎上来,向她说关大明还在里面动手术。一会儿,厂领导也到了。厂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齐刷刷开会似的主动与秦悦打招呼,手握了又握。工会主席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拉着秦悦安慰了好一阵,劝她别急,厂里一定会尽全力。秦悦把“谢谢”翻来覆去地说,心里是一万个没底。人还在手术室呢。倒见了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秦悦觉得别扭极了。想哭,好像又不是哭的时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两只手都不晓得该怎么放了。
手术中,医生出来过两次,先说要拿掉一条腿,让家属签字。“命要紧——”秦悦听到旁边好几个人撺掇着,眼前一黑,抖抖地签了字。手都不像是自己的了。过了一会儿,医生又出来了,说两条手臂也要拿掉。婆婆撕心裂肺地叫声“儿啊——”昏了过去。秦悦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见医生的嘴巴在动,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也不晓得是谁抓住她的手,签了字。
手术持续到凌晨才完成。秦悦穿上隔离服,全副武装地来到重症病房。关大明躺在那里,鼻孔接着氧气罩,下身插着导尿管。被子盖住了身体——少了两条手臂一条腿的身体,像没有搭完的积木。秦悦紧紧抓住病床的铁杆。后来回想起这刻,她觉得自己还是坚强的。一直挺着,没有痛哭,没有尖叫,没有昏倒。甚至还很到位地向主刀医生道了谢:“辛苦你了。”
当晚她被要求睡在病房里。关大明在重症病房观察,按规定家属不能进去陪夜,但必须留在医院待命,以备突发情况发生。她爸妈给她送来了饭和洗漱用品,还有毛毯。那一刻,旁边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她的爸妈。她仿佛一下子卸掉了重重的壳,完全散架了。
她号啕大哭。
爸妈不停地安慰她。可除了掉眼泪与叹息之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人能帮她。秦悦伏在妈妈怀里,忽然觉得好冷。浑身冰冷。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爸妈怕她寂寞,也怕她胡思乱想,带了好几本书给她。有一本居然是电码书。秦悦忍不住觉得有些滑稽了。她一直喜欢电码,当初考邮电学校也是因为这个,后来到邮局上班才晓得电报早成老古董了。现在通讯那么发达,谁还去发电报?又不是搞特务工作。关大明追她的时候,投其所好,向她学摩斯电码。摩斯电码分“点”和“划”两种字元,“点”的长度决定发报的速度,“划”相当于三个“点”。那阵子关大明学得很认真,整天背电码,还为了这个专门去补习英语,煞费苦心的。秦悦父母初时不同意,因为不想女儿再找化工厂的对象。秦悦父母和关大明的父母在化工厂干了一辈子,住一幢楼,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关大明和秦悦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这种情况下,摩斯电码到底是派上用场了。因为是门挨门,所以秦悦和关大明的卧室只隔了一堵墙。到了晚上,关大明就拿个擀面棍,在墙上发电码。轻轻一撞是“点”,重重的一拨拉是“划”。老式的公房,墙板薄,秦悦在墙那头听得一清二楚——点点;点划点点;划划划;点点点划;点划点划划;划划划;点点划——英文“I love you”,也就是“我爱你”。秦悦脸倏的就红了。
第二天早上,又死了一个。两死两伤。厂里派人送来了慰问金,并且郑重承诺,所有医药费用都由厂里负担,“你们千万放宽心,只要照顾好病人就可以了。”话是如此,可实际上照顾病人也根本不用秦悦操心。厂里特地请了一个看护,二十四小时贴身照顾。还从公安局派了两个同志轮流值班,寸步不离。医院方面则用上了最先进的仪器,最好的医生,最资深的护士。
“一定要全力抢救,不计任何代价。”厂领导说话很有分量。
关大明清醒过来,是两天以后。病房里围了一圈人,像极了给遗体告别的阵势。秦悦站在最靠近他的位置。他睁开眼,看见她。秦悦竭力让表情显得轻松。
“你醒啦?”她挤出一个微笑。
初时他比较平静,但很快便感觉到了异样。他应该是想伸手拿什么东西,但无从着力。失去手臂的肩膀,光秃秃的。停顿了几秒后,他尝试着抬腿。可仅有一条腿动了一下。另一条腿空了。那一瞬,关大明的神情有些迷糊,被点了穴似的。秦悦猜他是在努力回忆,分辨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吼——”忽的,他喉咙里发出像狼一样的嚎叫。响彻整个医院。撕心裂肺。
关大明第一次尝试咬舌,是在当天下午。公安局的同志到底是有经验,一看他的表情,就很果断地掰住了他的下巴,并在他嘴里塞了一团棉花。尽管如此,关大明的舌头还是被咬下了一小块肉。为这事两个公安局的同志还写了深刻检查。厂领导都撂下狠话了:

“两个月!两个月里要是出什么事,大家都没好日子过。他死了,大家为他陪葬!”
当然,这话不是领导亲口说的,而是过来坐镇的党办干事转达的。应该是加油添醋了,虽说是在病房门口说的,但门敞开着,病人多半能听见。关大明手脚是废了,可耳朵好好的。他们竟也不避忌。也许他们觉得,病床上那个缺了两条手臂一条腿的家伙,已算不上人,只是个东西罢了。就连秦悦他们也是不怎么避忌。他们甚至很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死两个人,已经是极限了,只要再多死一个,厂里便要倒大霉。这是市里的硬规定。都到年底了,谁能想到会出这个事。
“就算是厂长的亲妈,也没服侍得这么好。”一个与秦悦有些相熟的护士,这么说。她应该是想安慰秦悦,宽她的心。
另一个伤者依然昏迷不醒。他也被拿掉了一条腿一条手臂。这人还没结婚,他爸妈据说已吓得瘫倒了,还要人服侍才行。他姐姐每天来医院一趟。每次看见秦悦,都要流眼泪,说不晓得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醒。秦悦说,不醒不是蛮好?醒来就糟糕了。那女人眼泪流得更凶了。秦悦本来也不是那种很直爽的个性,现在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加掩饰。她说,你弟弟要是有福气,就一直不要醒,永永远远地睡下去。
关大明的嘴里被塞了个婴儿奶嘴。这还是厂干事想出来的,说这个比棉花好,又美观又安全。秦悦几次要把奶嘴拿掉,都被看护制止,“要是再出什么事,谁负责?”
秦悦忍不住发火:“他又不是小毛头,干嘛要塞奶嘴?”
看护道:“这话你不要跟我们说,找外面负责的人去说。”
秦悦真的去找厂干事。厂干事的口吻跟看护差不多,“我也不想这么做,你要是有想法,可以找领导嘛。”末了又加一句,“你是他妻子,肯定也不希望他出事,是吧?”
没人的时候,秦悦会拿掉关大明嘴里的奶嘴,把头凑近了,跟他说会儿悄悄话。“今天气色好像不错——你妈烧了鸽子汤,一会儿就拿过来——窗帘要不要拉上?光线是不是太亮了——我今天看到我小学同学了,原来他就在这里当医生,都十几年没碰面了,嘿,你说巧不巧——刚才王干事又给了我几张联华超市的卡,有两千多块呢,老公,你们厂可真有钱——”
秦悦不晓得自己原来这么会做戏,真的像闲话家常了。声音语调也控制得刚刚好。很平常很随意。关大明气管严重灼伤,不能说话。她像个单放机,笃笃笃,一句又一句。起初她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现在进步多了,可以大大方方地看他。不会掉眼泪。
替他擦洗身子的时候,比较难熬。好在有看护在旁边,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腔,分散她的注意力。她的功力还是不到家。盖着被子的时候过得去,被子一掀就完全崩溃了。几乎忍不住想要冲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叫几声。她拿毛巾的手,抖得厉害,抽风似的。看护姓刘,是个四十几岁的浙江女人,个子不高,劲道却很大,每次一扳,一翻,再一顶,关大明的身体在她手上像件玩具似的。她应该是见惯了的,所以眼神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动作干净利索。她对秦悦说,以后擦身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吧。秦悦晓得她是为自己好。有时候家里带的饭多了,秦悦就分一些给她。叫她“刘姐”。私下里的时候,刘姐告诉她,医院里给她男人用的这些药和设备,人力物力,加起来一天就要好几万。
“你们有小孩吗?”她问秦悦。
秦悦摇头,“去年刚结的婚。”
她“哦”的一声,很直接地表示:“那还算好。”
关大明的情况一天天好转。生命体征越来越稳定。只是他一直闭着眼。秦悦晓得他其实并没有睡着。病房里人越多,他眼睛就越是闭得紧。只有等到周围安静了,他才会睁开眼。却是什么都不看,仿佛只为了休息——整天闭眼的人,睁眼应该是一种休息。他的眼神,像极了化工厂后门的那条小河浜,太多的东西沉淀着,八级台风也吹不动。他情绪很不稳定,突然之间会厉声大叫,前一分钟还好好的,后一分钟就歇斯底里了。每到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就会一下子冲过来,敏捷得像豹子一般,用力按住他的身体,死死掰住他的下巴。秦悦向他们提过几次——可不可以稍微轻一点,他毕竟是个病人。秦悦尽可能把语气放得和缓,不停地做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她生怕一不小心,那些难听的脏话就会从嘴里蹦出来。她真的很想骂人。好像快要到临界点了,她控制不住了。她甚至还想打人,抽人耳光。
关大明用仅剩的那条腿,敲打着床板。
起初她以为他是在发泄,后来才晓得不是。他的敲打声很有节奏,一敲,再一拨拉——看得出他很用力,额头上的汗珠都出来了。秦悦拿毛巾替他擦汗,嘴里安慰着“没关系没关系——”他看着她,颈里喉结上下滚动着。她觉得那是一种绝望的眼神。有些恶狠狠,又有些无助的。她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大颗大颗地涌出来,止也止不住。她想自己真是个没用的家伙,忍了那么久,到底是没忍住。医院那么多空荡荡的地方,每层楼都有好几个厕所,偏偏要在他的面前哭。
他不停地敲打床板。一敲,一拨拉,熟悉的节奏,让她一下子醒悟过来。
点点;点划划;点划;划点;划;划;划划划;划点点;点点;点。
——I want to die(我想死)。
她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朝他看。他晓得她明白了,可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着床板。他神情很郑重,激动得泛着光。她倒是脸色苍白,好像她才是病人。一会儿刘姐上完厕所回来,他便立刻停下了,闭上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秦悦想,他真是很清醒呢。她晓得,他在给她布置任务呢。秦悦想起白天替他擦身的情景。看到他的身体,他以后只需要买短袖衬衫就可以了,一条裤子裁开,能当两条穿。那一瞬,秦悦脑子里竟闪过这样的黑色幽默。
她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
台历翻过一个星期。
秦悦现在比较喜欢回忆——上星期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好像是出事的前两天,小夫妻俩一起去吃了顿韩国烤肉,都是好好的,手也在脚也在;上月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家里新买了一台液晶电视,屏幕上有点小瑕疵,拿到店里换,反复折腾了好一阵,可人是好好的,手也在脚也在;去年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应该是去三亚度蜜月,当然那时也是好好的,手也在脚也在——秦悦像个机器人,大脑不断重复着一些固定的程序,傻了似的。特别不清醒的时候,她甚至想过寻找那种传说中的时光机,像前不久放的美国大片《波斯王子》,一按匕首,时光之砂漏出来,时间就倒回去了。那样多好,回到事故发生之前。那天她无论如何不会让他上班,拽也要把他硬拽回去。又想,不能只顾自家人,也要事先提醒那个临时工一下,让大家都好好的。
她把想法同公公婆婆说了。做好挨耳光的准备。门窗都关严实了,就算婆婆要哭要闹要尖叫,声音应该也不至于影响邻居。她的语气很平静,好像说的是别人家的事情。连理由都没多说,根本不必解释,情况摆在那里。谁要是不明白,就不是人了。
婆婆哭了。却不是号啕大哭,而是无声的抽泣。也许是秦悦的冷静,镇住了她。公公平常很能说会道的一个人,这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抽烟。
秦悦说,这样是为他好。他还年轻。要是他现在八十岁,倒也没必要了。
公公婆婆最终是点头了。两人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年。婆婆钻心的抽泣声,毒虫般咬噬着她的每个器官,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已不止是悲伤了。公公、婆婆、儿媳,居然在谈论着这样的话题,诡异得都不像在人间了。
她也通知了自己的爸妈。比起公婆,他们更多的是担心,再三提醒女儿,一定要做好准备,要保险,要全身而退,不能把自己也搭进去。秦悦使劲地点头。让他们放心。“我有数的——”
夜晚,她一个人睡在卧室那张六尺的大床上。巨幅的结婚照在头顶,两个人笑得有些没心没肺。披着婚纱的她,粉嘟嘟的像个洋娃娃,不大像她。他的手搭在她的肩上,低头吻她的头发。所以他只露出半张脸。当时婆婆很不喜欢这张,说结婚照就该大大方方,两个人的脸都清清楚楚,不作兴这样糊里糊涂。可摄影师喜欢这张,说光线到位,表情也到位,艺术照就该这样。照片拿回来那天,小两口张罗着布置新房,嘻嘻哈哈,光是摆照片就用了半天功夫,不是左边高了,就是右边歪了。过家家似的。
那时关大明是好好的,手也在脚也在——秦悦“啊”的一声,把头狠狠地朝墙上撞过去。疼得直咝气。她现在不能想事情,否则那些固定的程序会像蜘蛛网一样,兜头兜脸地将她牢牢缠住,透不过气来,很可怕。哪怕是考虑明天做什么菜,脑子里也会浮现关大明在厨房时的情景。他的厨艺比她好,所以通常她负责买和汰,他则是掌勺的大厨。新婚夫妻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洞房,厨房也不例外。他们疯起来的时候,很有些不管不顾。他烧的红烧猪手尤其好吃,色香味俱全,就是胆固醇太高,不能常吃。那时他们还玩笑说吃啥补啥,猪手能补手劲脚劲——那时一切都是好好的,手也在脚也在。
秦悦躺在床上,缓缓地抬起手臂,再抬起大腿。她想像着身上如果没有手臂和大腿,会是什么样子。那应该就不能称为身体了。她记得小时候和同学玩蛐蛐,同学太调皮,把蛐蛐折腾得断了好几条腿,看着像个怪物,却还在动,一时半刻死不了。她不忍心了,一脚把蛐蛐踩死。“——让它早点解脱。”
可人又怎么会一样呢,人虽然也是动物,但到底是不同的。人和蛐蛐能相提并论吗?秦悦整晚翻来覆去,像清醒又像迷糊,似睡非睡,到后来都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现实了。
早上婆婆打来电话,声音听着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好好想想,怎么让他走得舒服点。拔氧气管很痛苦的——”秦悦忙不迭地打断她:“妈,你说什么呢,是不是没睡好——”她“啪”的把电话挂了,叫了辆出租车到公婆家,叮嘱他们别在电话里说这些。
“当面讲没关系,电话里讲就留下证据了。”
秦悦说到这里,猜想婆婆也许会多心,觉得她这时候还能想到这个,过于冷静了。说实话,秦悦也很佩服自己。真是很冷静呢。像在进行一项事业了。所以说人的潜力真是无穷的,秦悦本来是连买青菜还是大白菜都要考虑半天的人,用关大明的话说,就是属于那种没主意的人,“所以才选了你,比较好弄。”关大明半开玩笑地对她下定义。当初商议结婚时,秦悦爸妈还为关家那套新房没加上女儿的名字而耿耿于怀,让秦悦去找关大明说。结果秦悦没开口就脸红了,绕了半天还没说到正题。后来还是关大明主动提出去房产交易中心,加了她的名字。关大明出事的头几天,秦悦爸妈寸步不离女儿,怕她精神崩溃,做傻事。可秦悦却压根没往这上面想。医院家里两头跑,什么都料理得停停当当,比平常能干了一百倍还不止。理智得都有些吓人了。连说起那事来,都是一口气到底,不带咯愣的。
“这大概就是他的命。要是这样算造孽,那让我下辈子变畜生好了。”她说这话时,有些恶狠狠的。
公公婆婆最后一次到医院看关大明。两人在家里排演了无数遍,要自然,要镇定,不能让他看出异样来。关于是否事先告诉他,几人想了又想,决定还是不要,有些太那个了。
婆婆炖了关大明最爱喝的墨鱼排骨汤。给他舀汤时,婆婆的手有些抖。秦悦说,妈,我来。接过汤碗。公公借口抽烟,到外面去抹眼泪。婆婆也跟着出去了,后脚跟还在房里呢,抽泣声就来了。秦悦想,好吧,你们都是逃兵,只剩我一个留守。
她问关大明,味道怎样?
关大明拿脚敲打床板,发了个“delicious(好吃)”。
他脑子真是很清楚呢。秦悦不由得一阵心酸。谈恋爱时,他与她一起报了个英语班,一半是为了学习,另一半则是方便见面。他的记性比她好,背电码快,背英语单词也快。那时她常说,要是放在抗战时期,他可以去当特工。他说现在也有特工啊。她说,现在的特工都是高科技了,谁还用这些老式的电码。他说,那不是白学了?她嗔道,学东西呀,怎么会白学?他便搂住她,笑道,反正骗了个老婆回来,怎么样都不算白学。
喝完一碗,他又拿脚敲打床板,发了个“one more”(再来一碗)”。秦悦又盛了一碗汤,问他,脚敲得疼吗?他摇头。秦悦便在他袜子后跟处垫了团棉花。“敲吧,现在不会疼了。”他随即发了个“thank you(谢谢)”。
两人一个说话,一个发电码,倒也交流无碍。秦悦想,当初学摩斯电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个用处。天底下那么多东西可学,她偏偏要去学电码,而他又偏偏喜欢她,也跟着学了。这是不是就叫命中注定呢?秦悦平常并不迷信,可此时此刻,竟真的有些懊恼了。瞎子的触觉特别灵敏,聋子的嗅觉格外的好。这是一样的道理。老天爷都帮你算好了,少了一样,必然会添上一样。若是多出来,自然给你除了去。反正你不用嘴巴也能交流,发电码只用一条腿便够了,剩下的那些,不要也没什么。秦悦觉得,老天爷才是瞎子,又是聋子,看不见,也听不到。
公公婆婆总算是进来了。婆婆红着眼眶,背对着儿子,问他晚上想吃些啥。关大明摇头。婆婆又问,伤口疼不疼?——这就问得有些傻了。最怕提这个,偏又提这个。婆婆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啊,这个,不疼就好。”说着说着,眼泪又出来了。
“你要不要睡会儿?”秦悦问丈夫,“我们去食堂吃个饭。”
关大明拿脚发了个“OK”。秦悦觉得他现在心情似乎不错,明明点个头就可以的事,偏偏还要发电码。三人临走前,他又发了个“see you(再见)”。
饭自然是吃不下的。只是个幌子,免得婆婆控制不住,被他发现。三人再回到病房时,关大明已睡着了。婆婆在儿子身边坐下,凑近了,端详他的脸。怕他醒来,大气也不敢喘。婆婆都记不清上次这么看他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儿子不像女儿,一过青春期就是人家的人了,一点儿也不贴心。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即便人回来了,心还是在女朋友那儿。怕她烦,还动不动就把手机关了。好在两家住得近,真要急了,就去敲隔壁的门,那小丫头要是也不在,就放一半心,说明两人在一起,出不了事。都说孩子是爹妈前世的债,这小子更是欠的高利贷,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挺聪明的一个人,就是不爱读书,高中没毕业就不想上学了,天天在网上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钱倒是赚了些。人家在开夜车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用赚的钱请女朋友看通宵电影了。问他有什么理想,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准备就这样在网上开小店当老板。公公婆婆都是老派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托关系把他弄到化工厂上班。化工厂也不见得好,但总算是个铁饭碗,正正经经的工作。
公公婆婆每次想到这,便后悔得想一头撞死。要是不进化工厂,也不会出这个事。不该替儿子作这个主。儿孙自有儿孙福,由得他去就好了,哪怕在网上卖军火卖毒品也好啊,就算被公安抓住枪毙,总也是个囫囵的人。这种做一百遍噩梦也未必梦得到的惨剧,竟然会发生在儿子身上。作孽啊!
关大明翻了个身。婆婆忙把头一缩,见他又沉沉睡去。将凳子搬到另一边,继续看他。想,这张胡子拉碴的脸是什么时候变出来的呢,好像昨天,他还是那个脸上光得没有一根毛的小家伙,蜷在妈妈怀里发嗲呢。一眨眼的功夫,喉结就出来了,声音也变粗了,见到她不再是奶声奶气地叫“妈妈”,而是刮啦松脆的一声“妈”!跟女朋友通电话是怎么也讲不够,见到她却是三句两句比发电报还简洁。直到结婚那天,她兀自还有些回不过神来,怎么突然就结婚了呢。儿子在妈的心中永远是个小孩,天天盼他长大,其实又怕他长大,长大了就飞了,当妈的心也跟着飞了。
“乖儿子——”婆婆忍不住轻唤。
公公过来握关大明的手,轻轻摸挲着。秦悦猜刘姐在一旁看得该想笑了。两个男人的手摆在一起,怎么看都有些不搭调。娘娘腔了。秦悦看见公公的眼圈红了,眼泪却是硬忍着没掉下来。到底是男同志,摒得牢。不像婆婆,一遍遍地去卫生间,鼻子都擤得褪皮了。
关大明到底是醒了。公公婆婆齐刷刷地跳起来,转过身,一个说去楼下抽烟,一个说上厕所,逃也似的。关大明怔怔地朝他们看。秦悦猜他应该是有些感觉的,手背上还有眼泪呢。也不晓得是谁的。
她给他削了个苹果,坐下来,一边喂他,一边聊天。有了袜子里那团棉花,发起电码来方便了许多。他起劲得很,把床板敲得咚咚直响。公安局的同志都进来看过几趟了,说怎么回事,是不是有脚癣,要不要搽点“肤轻松”。她说不是,“今天兴致好,就让他敲吧,反正敲也敲不死人。垫着棉花呢,很安全。”
她猜公安局的同志应该听出她话里的刺,都有些讪讪的,挺尴尬。她晓得他们也不容易,天天扳着手指倒计时呢,看距离两个月还剩几天。又不是什么美差,从早到晚待在医院里,也不见得会加奖金。责任倒是要担的。秦悦倒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们了。眼看着就要给他们添麻烦了,弄不好还是大麻烦。大家活着都不容易呢。还有刘姐,早上带了些家乡的黄岩蜜桔来,分给大家,说今年桔子丰收。她还剥了一瓣喂给关大明,嘴里说“很甜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话是有些不伦不类,可秦悦明白她的心意。
关大明的兴致真是很好呢。还给她发了个“beautiful coat(衣服很漂亮)”。床板敲得咚咚响。秦悦想,真是的,病人也会人来疯,上前刮了一下他的鼻子,弄得一手油。她从包里掏出自己的吸油面纸,给他鼻子吸油。他闭着眼睛,一副很享受的模样。
“把这些油加起来,够炒个小菜了。”她开玩笑。
他应该是想说“猪油味道香”,可一时不记得英文该怎么说,只好做口形。她看懂了,却故意说,“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发电码!”他便老老实实发了个“pig oil delicious”。她笑笑,拿吸油面纸给他看,“是不是,我一个月不吸,也没这么多油!”
他也笑了笑。她看见他的笑容,心里一酸,把头转开。
晚上她留下陪夜。送公公婆婆下楼的时候,她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爸、妈,不管怎样,我总归是你们的媳妇。”她说着,自己都觉得别扭——这时候好像说什么都不合适。公公嗯了一声。婆婆用手在她肩上搭了一下,嘴巴动了动,却一个字没说。
她站在医院门口,看两人扶持着,渐渐走远。路灯下,两人的身影泛着微黄,有些飘忽,像落叶浮在水面上的感觉,没着没落的。秦悦怔怔站着。她本想多留他们一会儿,是婆婆自己说要走,“留着反而不好——”婆婆的声音,听着像吃甘蔗吐出的渣,干涩得都发毛了。
“你们放心——”秦悦反复说着这句,都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大约是白天太疯的关系,关大明很早便说困了。“tired(累)”——他说。
秦悦一颗心被扯了起来,拉橡皮筋一样,生疼生疼的。她想让他别睡,再说会儿话。他要是嫌累,就躺着听她说。她还有好多话没对他说呢,就算讲一天一夜也未必讲得完。秦悦觉得,今天晚上,时间是可以握在手里的,真像“时光之砂”了。一小时六十分钟,一分钟六十秒,每一秒都是调皮的砂。手握得紧些,砂便漏得慢些;倘若一个不提防,手一松,倏忽便漏尽了。秦悦恨不得把砂和水捏一捏,再晒成块,那便怎么也漏不掉了。
午夜十二点。秦悦走出医院,到便利店买了个面包,远远看见马路对面有座教堂。来来回回这么多趟,还是第一次看见。她迟疑了一下,走过去。
教堂门关着,里面似乎有灯光,还有声音。她推门,是虚掩着,轻轻一推便开了。鹅黄色的灯光,很温暖。一些人在祷告。这么晚了,居然还有人。她想到过几天便是圣诞节了,教堂也许通宵开放。秦悦停了停,缓缓上前,找了个位置坐下。
她学那些信徒的样子,十指交叉放在胸前,闭上眼睛。
“上帝你好,”她心里默念,“我不是信徒,也从来没进过教堂。这么晚来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我不晓得说什么好,可是如果不说,心里又闷得很。上帝,你应该是万能的,人世间的一切都能看见,对吧?医院离教堂这么近,你肯定看得更加清楚了——上帝,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人鬼情未了》,说好人死后会上天堂,天堂的阶梯一格格,闪着金光。坏人死了进地狱,被两个魔鬼拖着就走,一点还价余地也没有。而天堂很人性化,要是你有事还会等你,等你事情办完了再来接你——上帝,我家关大明是个好人,肯定上天堂的。他除了喜欢看A片,就没什么别的毛病了。看A片也不是坏人,对吧?——上帝,我求你,让他在天堂里开心点。要是天堂真的可以等人,就让他在人间多待几天。我看不见他也没关系,只要他能看见我就可以了。我这个人比较傻头傻脑,可能过几天就没事了。他不一样,他想得多,爱操心,爸爸怎样,妈妈怎样,一定要什么都看过,才会放心走——上帝,我很舍不得他。非常非常舍不得。这话一直放在我心里,对谁也没有说过。再舍不得也要舍得,这是为他好。小时候我爸爸打我,一边打一边说是为我好。我心想,算了吧,打我还为我好?我现在才晓得,原来为一个人好,别说打了,就是做再过分的事,也是没错的——上帝,我这样颠三倒四讲了半天,你一定听烦了吧。很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祷告过,不晓得应该怎么祷告才对——”
秦悦走出教堂的时候,觉得脸上凉凉的,一摸,全是泪水。
凌晨,关大明睡得很熟。
秦悦走过去,把怀里的药瓶拿出来,里面是安眠药磨的粉。她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整瓶安眠药片磨成粉。倒了杯水,将药粉放进去,调了调。随即轻拍他:
“老公,起来喝点水。”
她扶起他,给他喝了半杯。他睡得迷迷糊糊,喝完又躺下,继续睡。
她站在床边看他。他熟睡的模样真的很像孩子呢。嘟着嘴,像在跟谁闹别扭。她伸出手,轻轻捋了捋他的头发,随即,把剩下的半杯水,一饮而尽。
她脱掉鞋,躺下来,与他并排而卧。病床很小,好在两人都不胖,勉强挤得下。
“人家说,自杀的人,一定会下地狱的,”刚才,她在教堂里这么祈祷着,“我又是自杀,又是杀人,看来百分百是下地狱了。他上天堂,我下地狱。不同路。不过没关系,我这人没心没肺,在地狱里也能过得下去——上帝,我求你,让他在天堂里开开心心的。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了。”
刘姐睡在门边的躺椅上。这么折腾,竟也没醒,还打着呼噜。秦悦想她倒也好睡。
秦悦觉得头有些昏,药效开始发作了。她朝他看。他竟然醒了,有些诧异地看着她。应该是床太挤,被弄醒了。秦悦那一瞬忽然有些好笑——吃了安眠药,反倒醒了。
两人对视着。出事以来,夫妻俩还是第一次睡在一起,有些新婚的味道了。关大明嘴里塞着奶嘴。秦悦拿掉奶嘴,在他嘴上吻了一下,脸不自禁地红了。竟真像新婚了。关大明的嘴唇有些干,像丝瓜筋,可眼神是湿的,是蜜月里的油浸浸的味道。
愈发昏沉沉了。思绪一点点飞走,像勾掉丝的毛衣,扯着一根线头,便整个抽了去。身子轻了,头重了,秦悦眼前开始模糊起来。
她感觉到他的脚在动。
点点;点划点点;划划划;点点点划;点划点划划;划划划;点点划——
她明白了,是“I love you(我爱你)”。
她想说“我也爱你”,可嘴巴不听使唤。于是,她也拿脚在床板拨拉:
点点;点划点点;划划划;点点点划;点划点划划;划划划;点点划——
“I love you”——她回应道。
她猜他应该感觉到了,虽然她眼前已经完全发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可她相信,他一定能感觉到。
她紧紧挨着他。要是他还剩下一只手,她一定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不过现在这样也没关系,她能感觉到他的体温,这样就足够了。她的丈夫,她的爱人,她的宝贝,此刻就躺在她的身边。这样很好,很温暖,很贴心。
爸妈那天劝她要“全身而退”,她嘴上答应,却没往心里去。要是他不在了,她即便“全身”又如何呢?手也在脚也在,心却死了,那不是更加可怕?她不后悔这么做,只是,有些对不起爸妈了。他们把她养得这么大,她是他们捧在心坎尖上的囡囡。秦悦觉得,天底下好像没有圆圆满满的事,顾了这头,那头又顾不上了。不管怎样,总有人难过失望。
刘姐的呼噜声越来越响。到后来竟似带着鼻音,不晓得是鼻涕还是别的什么,像是重感冒。这么响的呼噜声,就算是昏过去的人,只怕也醒了。她竟还没醒。也真是奇了。
“see you(再见)”。
意识消失前最后一刻,秦悦发了这串电码。她想应该是不会再见面了,该说“永别”才是。可是“永别”用英文怎么说,她实在是想不出来了。她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背英文单词总是牵丝绊藤。
不知过了多久,她好像可以站起来了。身体好轻,是飘着的。眼前出现一道门,她推开,里面金光闪烁,一座高耸入云的阶梯,一格格通向天边。隐隐有歌声环绕,很壮观。那一瞬她有些迷糊,想,怎么回事,不是该下地狱吗,怎么竟似看见了天堂。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