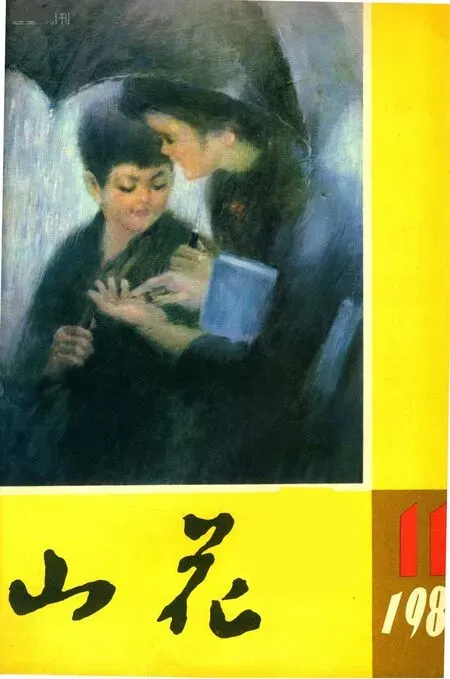生与死的对视
张劲
生与死的对视
张劲
一
当雷雨在葬棺洞外低一声、高一声地嚷叫时,我们正在洞内高一脚、低一脚地探路。雷雨越是呼天抢地,我们越是沉静、肃穆。
先前参观芦笙洞时还是丽日晴空,后来考察葬棺洞时就变成雷雨交加了。生死殊途,阴阳迥别,看来老天爷比人类还深谙其个中三昧。
伴我们同行的是龙里县的两位青年干部——小陈和小吴。小吴在附近的一所乡镇中学当校长,他的祖先就安葬在果里葬棺洞内,汽车路经果里大寨时,他特意下车买了一盘鞭炮带上。小陈是县文联主席,他坚持要带我们先去寨后的芦笙洞探望,他说芦笙洞又叫阳洞、生洞,葬棺洞则叫阴洞、死洞。应该先看近处阳洞,再看远处阴洞,最后从阴洞走出来回到阳光下面,这才符合规矩。于是我们一行人便先去了阳洞。
阳洞果然阳气充足。午后的日光毫不犹豫地、肆无忌惮地泼洒在洞内洞外,宽阔、敞亮的洞厅里挤满了融融暖意。即便是阳光一时占领不了的角落,也有干爽的和风,不请自来地在这里嬉戏、盘桓。据说,过去每至农历正月,周围四乡八寨的苗胞便聚集在这里进行一年一度的跳芦笙活动。其时,欢声如潮,盛况空前,舞者、歌者、观者,无不喜气洋洋,春风满面。青年男女的爱情,老人、孩子们的亲情,朋辈乡邻间的友情,追逐着芦笙、鼓乐、银饰、百褶裙旋转。那几天,寨子里熙熙攘攘,家家户户时兴开流水席,走亲串戚的人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动作跳舞,大嗓门唱歌,欢乐的生命在这里打下了一个个鲜亮的结。
如今,阳洞只剩下阳光与洞而看不到芦笙舞了,跳芦笙活动已迁至另外的露天场地进行。但是洞内曾经烟熏火燎过的石头,还保存着那些被欢乐时光涂抹过的证据。而且洞前来往的田夫野老、牧童马倌也还依然保持着津津乐道、向人诉说前尘往事的浓厚兴趣。
站在阳洞门口,可以遥遥望见对面山崖上的阴洞洞沿。阴洞被树木杂草半掩着,像一场似醒却终未醒来的长梦。
两洞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六百米,一个人从阳洞躺到阴洞,至少也有五六十年光阴,然而五六十年以上的光阴只换来五六百米的距离。此岸打成的生命的结,终将在彼岸解脱。芦笙洞里的芦笙,必然会变成葬棺洞里的棺木。空间性的精彩缤纷,最后都会被时间性的悲怆岑寂没收……因而两洞之间的对峙,是真正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峙。
由是,果里阴洞的名声也就远远大于阳洞。以至于在不少人心目中,阳洞只是阴洞的一个陪衬,一个不愿挑明,却是实实在在绕不过去的陪衬。这看法固然有些悲观,应该说没有死就没有生,二者是互为陪衬的,但微茫的智性之光,终究不能赶走盘踞在多数人心头的死的恐惧的巨大阴影。所以历来参观阳洞者众,考察阴洞者少。

李雄伊作品·66
二
走过一片田野,爬上一座山坡,穿过密密的小树林,便到了阴洞洞沿。阴洞高10余米,宽20余米,不仅阔大、深邃,而且干燥通风,岩壁虽满布皱纹,表情却不似想象中的那般狞厉。有一丛藤蔓,斜斜地挂在洞壁前作悠然状,晃吊着的是秋千似的清风,而不是想象中的余悸。
小吴点燃了带来的鞭炮,我们也各自点燃了一炷香。小吴随后唱起了一支古老苗歌,大意是:
尊敬的祖先们啊,后辈又看望你们来了,
我以歌为酒,请接受后辈们的拳拳孝心。
后辈们不会忘记你们的辛劳,你们的恩德,
你们的在天之灵定会保佑我们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浑厚的歌声里满含着虔诚,还裹着圣洁的探询和叩问。洞内凝重的氛围被划开了一条缝。循缝而入,一行人的目光开始屏声静气地、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棺材组成的暗黄色长卷。
只见从洞内几十米处开始,便依次向前,井然有序地摆放着数百具棺木。棺木油漆早已脱落,一个个长方体灰白黄褐,随地形高低而参差排列,纵横成阵。所有棺木都由坚固的木架支撑着,木架离地面约一两尺高,既可以防潮,又能大体保持平稳。支撑架有4桩和6桩之分,据说4桩为男性死者,6桩为女性死者。女性所以多出2桩,是因为苗族妇女喜爱银饰,亲属担心有人来盗,所以须加固保护。但也有另一种刚好相反的说法,认为4桩乃为女性,6桩才为男性,理由是男性身体沉重,需要多加2桩。
棺木一律都无墓碑,也无墓志铭,甚至还无文字标识。据说,墓碑就竖在后人们的心里,亲属代代口耳相传,脚识眼记,不会遗忘,更不会弄错。先放的棺材离洞口稍近,后放的棺材距洞口稍远,故而越靠近洞口,棺材的年代就越是久远。
曾对苗族文化有过一些了解,我对它的丧葬情况并不十分陌生。
苗族古代丧葬主要有悬棺葬、洞棺葬(岩棺葬)、土葬三种。洞棺葬通常是一个家族的公共墓地,外姓死者不得进入。在家族公共墓地中,死者陈放的方向大体都是头东脚西,而且按其生前辈份,由上往下排列。同辈人排在一个横列,弟在右,兄在左,夫妻则按男左女右排列。进入墓地的死者年龄都在60岁以上,至少也是50岁以上,且都是正常病死者,那些摔死、溺死、难产死、斗殴死等非正常死亡者,是不能葬入墓地的。
从近些年来全国各地苗族考古发掘情况看,洞内灵柩从魏晋南北朝起到明末清初止,历朝历代皆有。就黔省而言,以明清两代居多。明代《贵州图经新志》就曾记载:“镇宁部民曰康佐苗者……有丧则举家以杵击臼,更唱叠和,三五日方置尸岩穴间,藏固闭深,人莫知其处。”清乾隆《独山州志》也载:“黑苗衣服尚黑,故曰黑苗……人死亦哭泣、椎牛、敲铜鼓,名曰:‘闹尸’,葬或以棺木置洞中……。”所以置棺木于洞中,苗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最初是从黄河流域东迁到长江中下游,再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黔、滇、桂等地,人死后魂魄仍希望回归故土,故而停棺木于洞中暂放,且都是头东脚西,目的是为了记住回家的路,准备随时拔脚起程。此类葬式,在黔省长顺县、都匀县、平坝县、惠水县以及贵阳高坡等地,都曾发现其洞葬遗址。

李雄伊作品·67
眼前这处洞棺葬,乃是本地吴姓家族五大支系的公共墓地。葬洞中有两类棺材,一类为平型棺,四平八稳似火柴盒;另一类为高型棺,棺盖之头高高翘起,与今日棺材已无多少差别。平型棺为明代棺木,高型棺为清代棺木。小吴告诉大家,据老辈人讲,吴氏家族原从惠水县摆金乡迁来,历时已有16代人,果里洞葬已有500余年历史。入棺者的年龄、死因以及尸体安置方式,大体和在惠水时一样。洞内存棺,最多时曾达千余具,后因某次失火,被烧毁者不少,如今剩下的已是烈火篡改和时间增删后的残本,以至所存棺木,有的已经变形,有的已经坍塌,有的则只剩下朽木几片,白骨半堆了。这不,一具头骨正仰卧在积尘之中,怔怔地望着洞外,也怔怔地望着我们。不知道他的性别,更不知道他的身世,只知道他的眼窝骨里深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谜语式地费人猜测。
尽管只是残本,这里仍然称得上是一座历史文化信息宝库。那些摩肩接踵、密密实实的棺木方阵,占地约两千平方米大小,俨然如一支特种部队,浩浩荡荡又安安静静。我发现,棺木与棺木之间,支撑架与支撑架之间,彼此的层叠与交错,间离与呼应,都在竭力保持着一定的位置。位置与位置又构成秩序。在鲜为人知的葬棺洞内,在黯然失色的棺材之间,竟然也还保存着某种“秩序”,这多少有些令人讶异。那里面,包含着现代人所需要了解的多方面信息。
就在这支棺木队伍之外七八十米处,还有一座矮矮的土墓,静静地立在荒寂里,像一个多余的单词,孤零零地衼隔置在长卷的外面。它同样既无墓碑,也无文字介绍。小吴说里面原埋着一位亦苗亦汉的乡民。那乡民本是汉人,后来落户本地苗寨,遂改了族属,于是他的后人便选择了这样一种葬式和位置,既安埋在同一洞内,又自觉地保持着与其他棺木之间的距离。但这样做还是违背了吴氏洞葬的严格秩序,所以其棺木最后还是被迫迁出了洞外。这里,剩下的只是一座再无人过问的空冢,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三
人最习惯的事是活着。人最陌生的事是死亡。以习惯之身去造访陌生之境,我们的每一跨步都格外谨慎。这既是因为洞内光线微弱,越至深处就越是阴暗,也还因为对古人的那一份敬畏,生怕一不小心就踩痛了亡者的魂灵。
若干魂灵被岁月的厚被覆盖在同一洞穴里,想来当不至寂寞、冻馁,但他们的后辈仍然担心。因而每年拜祭时,总不忘带去一罐米酒或数碗饭菜,以至于我们穿行其间,常会遇到破碎陶片前来附足攀谈。
敬以酒食,乃是生者对死者的忆念。说实话,葬棺洞里行走,虽然阴森,我们却不感到有多少畏怕,虽然神秘,却不觉得有丝毫险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得自于这种忆念。
消逝本是人的宿命,但有了忆念,逝者的价值便被生者挽留。敬畏也是一种忆念,当然也是一种挽留。逝者先是被棺木挽留。棺木接着被葬洞挽留。葬洞再被青山挽留。青山又被后人的忆念和敬畏挽留。最后,挽留对象与挽留者都被时间挽留。挽留绵延无终,前提是不能中断忆念的链条。
我们的考察与造访,正是为了链条的延续与修复——特别是在今天,在商品经济大潮涌来、传统文化遗产遭到冷遇和颠覆、苗寨中青年人纷纷外出打工的今天。小吴说,每年春节期间,外出人员回乡探亲,长辈叮嘱晚辈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一定要进洞祭奠。其祭品也从昔日的土罐土碗,发展到有了塑料玻璃制品和易拉罐了。晚辈们认为,这是为给亡者传达一种信息:时代前进了,忆念没有断。没有断裂的记忆里,总该也有时尚元素的加盟吧。
阴洞还在向前蜿蜒。洞内有起伏坡度,不大,但棺木区外是乱石区。越往前走,乱石越是嶙峋,道路也越是漆黑难辨,以至要用打火机帮助照明,弄得我们中的两位女士步履维艰。来到一堆人工砌就的石墙前,还有多重石门、石坎,石室、石圈,那是动乱年代苗民躲避兵祸匪患的地方。在洞内避匪,不但隐蔽,且有祖宗灵魂保佑,所以它比洞外要安全得多。据说洞的前端终点处是悬崖,崖边出口有小路可通山下另一个村寨。
领队的小陈和小吴极力鼓动我们继续前行。但此时洞外已是雷雨大作,隆隆雷声和哗哗雨声前赴后进地奔进洞来,搅扰得我们有些心神不定。还有蓝色电光神秘地探头探脑,映在石壁如即开即落的巨大白花。惊愕之余,一行人只好从原路返回。好在初夏的阵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很迅速,大家尽管被淋湿了衣服,到得山下时却已是云收雨霁了。
说来也巧。云收雨霁之时,我们恰好赶到两洞交界处的中间地界,看到了一种平时熟视无睹、现在却颇能发人深思的景观。
这中间地界是一片良田沃土。此时,但见黄黄的油菜荚已经渐趋饱满,过不了多少时日就要成熟待割了。它的这一茬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相信,它甚至已经听见了镰刀的催促,但它依然迎清风而舞,与田鸟共唱。在它旁边紧邻着的是水稻的育秧田。育秧田里正是稻苗青青,一个个幼小的生命正待生长、壮大。抢水打田的农民在附近的田土里,兴奋地驾牛扶犁,正忙得不亦乐乎。
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就在这同一片田野里演示,并行不悖,而又衔接得如此流畅、自然。这便给人一种启示:生与死原来并非都是壁垒森严,不可调和,它还可以呈示为另一种形式。
此时再来打量两边的阳洞、阴洞,只觉得两洞对视如目光。原本剑拔弩张、相互对立的两极,由于有了这么一块美丽的中介地带的加入,其紧张结构已变得有些宽松,有些平和了。生固然可喜,死亦并非一律都是绝望、恐怖、狰狞,它还有可能转化为安详、从容、宁静。人不能拒绝死亡,却可以改变对死亡的态度。这心事,已被田野一语道破。
因此,当阳光重新照亮大地,雨后的青山格外苍翠。我看见,生洞也好,死洞也罢,两洞洞口都有薄雾泛起,徐徐的,粉粉的,柔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