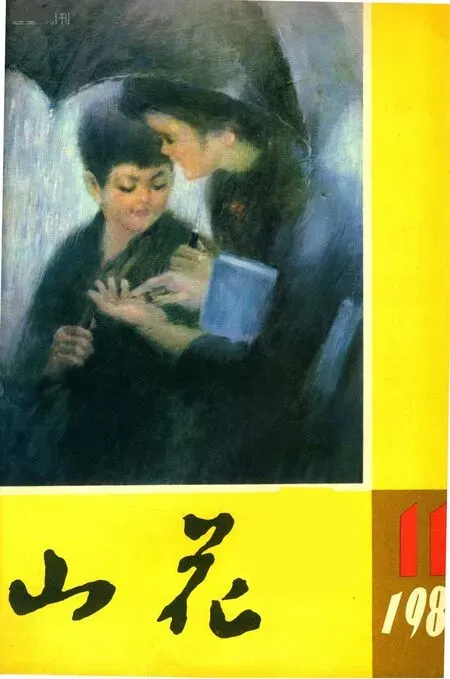永%动
徯晗
永%动
徯晗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来回摆动的床。最好能像列车行驶在铁轨上时发出那种咣当咣当的节奏。我需要这样一种节奏,来保持我身体的某种固定节律,以使我的身心获得安宁。这样一种隐秘的念头或愿望,我在十年前就有了。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在我的内心变得日益强烈,甚至迫切。
有时,我坐在行走的列车上想入非非,看着窗外不断向后移去的树木,田野,山丘或者河流,远处的蓝天,蓝天下的白云,白云下的阳光,阳光里若隐若现的人事与景物。它们如同逐渐远去的时光,消失在我的生命里。又日复一日地在我眼里重现,如同我余下的岁月,在晨曦里将我悄然唤醒——我耳边依然是那有节奏的咣当声,窗外移动的风景依旧。那个念头就会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我能拥有一张可以来回摆动的床吗?
在一天的忙碌过后,在灯光熄灭后的沉沉暮色里,我躺下来时,这个念头也会同样强烈:将来某一天,我能拥有一张可以来回摆动的床就好了!然后,我便带着这样的念想,悄然入眠。睡眠的质量当然极好。安睡。偶尔做梦。像所有人的梦一样,梦境或真实。或荒诞。再正常不过。
很多人都感叹,时光总是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逝去。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我看来,时光总在动。在我的眼前动。在我的身子下动。我能清楚地感知到它的动,只要我眼神稍稍往窗外一望,那景物就变了,怎么会有无声无息悄然逝去之感呢?有时候,我会好奇地想,那些长年行驶在海洋上的海员们,他们对时光的感觉又是什么样子?还有飞行员,他们的感觉又是怎样呢?驾驶着那么一个大家伙,在时空中翱翔,穿越,升腾,俯冲……至于那些开战斗机的军人,我就只有臆想的份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空军的飞行表演,光是观赏,那感觉就妙不可言!我不知道他们从船上或者飞机上下来后,躺在家中的床上是否也会失眠?呵呵,反正我离开了铁轨,或者说铁轨上的列车,准确地说,是列车上那张配给列车长的小窄床,我就会失眠。
失眠,多么可怕的日子。我原来没有想到,它会对我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十年前,我第一次有这种可怕感觉。那晚,我第一次躺在家中的床上无法入眠。一整夜,我的耳朵里出现一种幻听: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是列车行驶在铁轨上的声音。但是,床却没有动。这让我焦虑和烦躁。于是我只得不停地翻身,这引起了我妻子李青的愤怒,她说于大海你想干什么?我说我睡不着。李青在半睡半醒中吼道,睡不着就给滚我出去!我说,我耳朵里出现了幻听。幻听?什么幻听?李青这下彻底醒了。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是列车轧碾铁轨上的声音。李青噗哧一声笑了,她说,我知道你这列火车想干什么,看来不轧你两下,你是睡不着的。我也笑,说,我已经轧过了。李青说,你还想轧!不然,你干嘛在我旁边翻煎饼似的,搞得我整夜睡不成!我说,我真的出现了幻听。李青便有些娇嗔道,你就虚伪吧你!说完便往我身下挪了挪,将肉乎乎的光身子贴住我。

顾铮作品·台北孔庙外
我再说什么,李青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我只好把她当成铁轨,轧上去。然而,接下来,我并没有睡着。那幻听一直存在。整整一夜,它响在我的耳边: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我头痛欲裂,睁着眼睛,直到天明。我第一次体会到彻夜失眠的滋味,它是如此地让人忍无可忍。
患上失眠症后,我渐渐有了一个隐秘的念头:弄一张能来回摆动的床。事实上,我并不是经常失眠。我只是躺在家中的床上才会失眠。每个月里,我大约有十个夜晚是在家中度过的,但就是这十个左右的夜晚,我会彻夜无眠。我总是在李青的身边翻来覆去,她终于相信我在床上翻煎饼,并不是她以为的火车想轧铁轨。
我说,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李青好奇地问。
床。
床?
对。一张摆动的床,或者说,叫床摆。
床摆?
对,床摆。它就像钟摆一样,可以来回摆动。
李青哈哈大笑起来,李青说,于大海,你不是有病吧?
我说,你看我像有病的样子吗?
李青忽然脸一拉,大叫道,我看你就是有病!神经病!说完一个翻转,背过身子睡了。
我对着李青的后背说,真的,李青,我的耳边一直响着那种咣当咣当声。
她不动,语气僵硬地说,你这是有病!跟车跟出毛病来了!
我说,可我在列车上却不会。在车上,我睡得很好,耳朵里也不会出现幻听。
李青一屁股从床上坐起,说,你赶紧换岗!我明天就去找领导反应情况!真是的,从车头到车尾,就那么点地方,你说你,白天黑夜地呆列车上,没有社交,又看不到啥新鲜事物,不出毛病才怪!
我说,这跟社交没关系,列车地盘虽小,可它行走的地盘很大。车上的旅客来自天南地北,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怎么会看不到新鲜事物呢?我有些不服气地辩解着。
李青不再理我。
我也不再尝试让李青理解我。如果做妻子的执意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心理问题,再多的解释也是无用的。只是,想要那样一张床的念头,更加强烈地遏制了我,它使得我对身子下的这张床更加充满了不适感。
这样的次数多了,李青开始流露出对我的厌恶。她说,于大海,你就是贱!好端端的双人床,软乎乎的席梦思,安安静静的家,你说你睡不好,不是贱是什么?
我说,是有些贱。
不是有些,是贱得狠,贱得要命!李青气急而骂。
是贱得狠,贱得要命。我附合着。心里却在苦笑,要是家里的床也能像列车那样摇个不停该多好!那样,我就能睡着了。
李青说,于大海,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你这是病,是强迫症!要不,你让医生给你出个证明,就说是列车上的咣当声,把你弄出了幻听。让领导把你从列车上调回来,怎样?

顾铮作品·台北师大路夜市
我摇摇头。我从李青无可奈何的眼神里看到了绝望。
我想,我怎么能从列车上往地面上调呢?我每天就指望能回车上睡个好觉,如果调回来,岂不是一夜都睡不成了?恐怕不出十天,我就得死掉。我想起一些熟悉的人和事,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我凑近李青,有些神秘地说,你还记得咱爸吧?从列车上退下来,没过两年就死了。还有我二姑,你大伯,你想想看,他们从列车上退下来后,是不是都没活过十年?你见过咱们单位那些……从铁路上退下来的老列车员,有几个活过七十岁的?
李青愣住了。过了一会,她突然骂道:神经病!你再这么神经下去,我们离婚!说完便怒不可遏地搬进了女儿的房间。
李青的过激反应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神经病吗?是我的精神出了毛病?我当然不相信。
在列车上,我一切正常。工作上从未出过任何差错,饮食与睡眠更是没有任何问题。我能有什么毛病呢?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有什么问题。精神没问题,身体更没问题。其实,我早就弄清了我失眠的原因——我只是习惯了那种动。想想看,一个总在动着的身体,即使是在深度的睡眠中都在运动着的身体,你让它突然静止下来,躺在一张一动不动的床上,耳边也没有那种熟悉的咣当声,这个身体怎么会不出毛病呢?
失眠,正是身体对这种非常生活的反应,是它再正常不过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我看来,我身体的异常表现,与列车在铁轨上行进的速度与速率都无关系,因为相对于行进的列车,我身体的速度是静止的。这一点,任何一个有一丁点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与它有关的,是振动。它只与列车在铁轨上振动的频率有关。换句话说,我在家中之所以失眠,是因为我的身体离开了这种振动,失去了这种频率。
咣当咣当的震动声,就是列车和我身体振动的频率。如此休戚与共的振动,我的身体怎么会不做出反应呢?就像一只在真空中振动的弹簧振子,只要没有外力去改变它,它就会一直振下去,振下去。对于我而言,让我离开列车,就是那外力。这正是我在行进的列车上,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这一年我四十五岁,李青三十八。她比我小七岁,看上去还算年轻,还算貌美。我们同在南城铁路集团工作,我在乘务部,刚当上列车长不久,每月一大半时间都在列车上。按李青的说法,这叫奔波。李青说,你啥时候才能停止这种奔波啊!可是,我停不下来。就算我的心想停下来,我的身体也停不下来了,它成了我身体的惯性。
李青在公司票务处,每天可以正常回家。我们十岁的女儿于洋还过着懵懂的幸福日子。从小到大,她基本跟着她的漂亮妈妈。只是这种局面很快就将改变,李青将不再是我的妻子。从此以后,作为我的前妻,她将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职业“小三”,不,是“中三”,或曰:中年小三。因为李青怎么说也已是快满四十的女人,而且还带着我们的女儿于洋。
这不是李青的错。它是我的身体不肯妥协的结果。
与李青离婚后,我一直在做一个调查,或曰暗访。整整十年里,我暗访过的人,不下三百名。无疑,这些被暗访者,他们都是铁路职工,而且都是从列车上退下来的列车员。

顾铮作品·台北市立美术馆一景
作为一名暗访者,我的身份也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名聊天者。一名他们曾经的同行,与他们有着共同的感同身受的经历。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有过像我一样的失眠现象,但都属于轻度。有的甚至可以轻到忽略不记。但随着他们回归到地面生活,这样的失眠,也很快就消失了。只有极少的几个人,身体与我一样的顽固,因为长期的失眠,镇定药与安眠药成为他们长期的生活件侣。他们为失眠所困扰,却找不到失眠的原因。他们在我面前大都有一句共同的感叹:这人可真是贱,过去跑列车多辛苦,在闹哄哄的车上睡得照样香得很,现在轻松了,安静了,倒还失上眠了!
再不然,跟你来上这么一句:这人啊,可不就是劳碌命!过去跑惯了,现在闲下来,却闲出病来了!
总之,他们的说法大同小异。但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到惯性,提到动。摆动。那种不停歇的摆动。那种究竟是谁把这种惯性和动给我们的呢?
我自然不敢说出我的妄断与臆测。我总是在对他们的安抚中结束我们的聊天。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悄悄地写在我的日记本上,自己和自己分享,就像《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所为。
我想起我死去的父亲,他也是一名铁路职工,五十五岁那年,从列车员的岗位上退下来。退休后,他只活了两年就告别了我们。他的死因曾经令我们全家人感到蹊跷,我记得他那两年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心烦”。母亲说,你爸总是心烦,睡得不好。
“他是烦死的。”这是我母亲的原话。
我现在回想起父亲退体后那两年的生活,总觉得窥探到了一些他身体的隐秘,我不能对父亲的死因做出臆断,但我可以推想,父亲也一定患上了失眠症。因为母亲说过,你爸总是心烦,他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这就是说,父亲也有过许许多多失眠的夜晚。父亲的睡眠究竟是怎么个不好法,我如已不得而知。因为对此知道得最多的人,业已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无法去找这个惟一的目击者、我的母亲去求证。
与李青离婚后,我并没有像她预言的“要不了一年,你就会被人送到精神病院去”。相反,我的睡眠变好了。因为离婚后,我基本没有离开过我所服役的那趟列车。在列车休息,或者我休息的日子,我总是会央求我的同事们把我带上另一辆行进的列车。这种时候,我一般是以代班的名义出现。对这样的好事,我的同事们自然求之不得。他们善意地嘲笑我:你老婆跑了,只好把列车当老婆压了。他们甚至建议我在列车上随便姘一个,“反正她们在车上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陪陪你。在车上陪你,回家了陪老公。怎么样?”
对于这些并无恶意的玩笑,我不以为然,并抱以同样暧昧的回应。
天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我的身体保持一种“动”。对于一具只有处在“动”中才能保持安宁的身体,我只能努力去适应它,而不是让它适应我。可以说,我是被它同化了,也可以说是它异化了我。总之,我和我的身体,我们在对彼此的同化或异化中暂时相安无事。
从某种程度上言,我和我的身体,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要想让他们和平相处,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我的身体获得一张床——一张可以来回摆动的床。对,一个床摆!从某种意义上言,它也是我生命的钟摆。它必须随着我生命的延续而动。于我而言,这是一种永动。是一张“永动床”。
然而,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永动机一样,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永动床。但找到一个类似的“永动床”是不难的。对我而言,它就是一辆行进中的普通列车,K字号或者T字号的。作为一名列车员,找一张这样的床来安放自己的身体,眼下并不难。我担心的是有一天,我在铁轨上再也找不到一辆这样的列车,它们将被各种名号的高速列车所取代。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到那时,我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观看日出与日落,都是另一码事。
列车成了我的家。在列车上,我找到了我想要的安宁。离婚后,我把房子和所有财物都给了李青。这让很多人不能理解,包括我的前妻李青。刚离婚的时候,我去看她和女儿于洋。见到我,李青总是不能掩饰她眼里的诧异,她说,于大海,你看起来不像有病的样子呀,你净身出户,不是就为了摆脱我吧?
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心里又没有别人,我干嘛要摆脱你?
她好奇地看着我,说,你还失眠?
我说,早不了,我在车上睡得很好。
李青看着我,脸上露出了费解的神情,似乎在问,这人怎么还没进精神病院?
我会意地笑笑,心想,这辈子你恐怕永远也见不到那一天。
离婚后,李青似乎过得并不快乐。她没有再嫁人。这个年龄的女人,正是旱不起的时候,她人还年轻,又天生一副好脸蛋,为什么不找个男人再嫁呢?
我说,我们都离了,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嫁了?
她说,拖着一个女儿,还能嫁什么好男人?
我有些内疚,说,要不你把女儿给我?
李青不禁大笑,说,给你?你不是说笑话吧,于大海!让她跟着你,在列车上天南地北地跑,跟你一样过那种奔波不停的日子?她嘲讽的目光和语气,让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我说,你要是不想嫁,娶一个进来也行。
李青说,于大海,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
我想想是这个道理,就不再提这个话题。有一次我休假,又去看女儿,我把她带到公园里玩,她拉着我的手,路上突然对我说,爸爸,我妈当上小三儿了。
哦?我奇怪地看着于洋,她知道“小三儿”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是个老板,我妈妈说他很有钱,他给我妈妈买很多礼物,也给我买很多礼物。不过,我不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又不是我爸爸。
女儿的话让我很吃惊,她才十岁,我原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其实她懂得很多,这让我对女儿深怀内疚。
其实,爸爸不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实在是因为我……我在家里的床上睡不好觉。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女儿明白这一点,难道我能告诉她,我想要的只是一张来回摆动的床?
当上“小三儿”后的李青,显然比以前快乐了许多。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李青,那个人是个什么样子?听于洋说他很有钱,是个老板?
李青哈哈大笑,说,什么样子?他和你一样,精神也有毛病!李青说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认识的吗?
我好奇地看着李青,等着她揭开谜底。

顾铮作品·行人优先
有一次,他临时有急事,要出差去武汉,又正逢春运,票难买,就托人找到了我。找我的人说他很有钱,我如果愿意帮忙,他会重谢的。我想,他既然这么有钱,怎么不去买飞机票呢?机票虽然紧张,但买当日南城飞武汉的全票还是没问题的吧?我问他为什么不买机票?找我的人为难地说,陈老板有恐飞症,就是恐惧坐飞机。我当是个玩笑,就给他弄了张当晚从南城到武汉的软卧——还记得那次我给你打电话,让你留个软卧的事吗?
我想起来了,李青是打过一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她留一张软卧。这还是我们离婚后她第一次找我帮忙。那个来找我的人,我也还有印象,是个气质不错的男人。样子高大健壮,眉目间透着成就感与自信,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
我点点头,表示我还记得。
事后,他果真给了我重谢。李青指着酒柜中一瓶巨大的XO说,那,这瓶酒就是他当时托人送来的。一张火车票,照说换这瓶酒的零头都不够吧?我不明白这人到底有啥意图。可他又能对我有什么动机呢?我们当时连面都还没见过。我猜这人不是脑子进了水,就是有两个钱烧得慌。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李青说完看着我,一副卖关子的样子。
我不吭声,只一味地看着李青。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我知道她驾不住我这么看她。果然,她笑起来,说,告诉你吧,这人是真的不敢坐飞机,说是他请人算过命,在陆地和水里都没事儿,在空中就可能有事儿。所以,为了一张火车票,他才敢出这么大的本。
我笑笑,继续看着李青。
想不到的是,他后来又找我帮忙了,这一次,他找熟人要了我的电话,直接找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李青微笑地看着我。

顾铮作品·台南草祭二手书店门口一景
我不接话,下面的事想也能想到,李青长得又不差,完全配得上他。可是李青说,想不到我没费什么劲,就勾上了他!我还以为攀上他有多难呢!李青流露出的,完全是一副沾沾自喜自轻自贱恬不知耻的神情和语气。
这么说,不是他诱惑你?我有些失落地问。
人家是谁?要诱惑我这个半老徐娘?他那么成功,那么有钱,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
李青脸上与语气中透出越来越浓郁的下贱色调,真的让我有些忍无可忍。可这又关我什么事呢?她已经是我的前妻,我不是希望她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吗?让她这个年龄的漂亮女人旱着,那是不人道的事。我告诫自己的内心要保持平静。
我说,既然他怕坐飞机,多买几份保险不就行了?
李青不禁哈哈大笑,她说,于大海啊于大海,你真不愧是我的发夫!你跟我当初一样,问了一句一模一样的傻话!我就是这样问他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
我好奇道,怎么回答?
他说,我才不买保险呢,那样老婆只会嫁得更快!我死了,人家赔得越多,她越好嫁,这样赔本的生意我不做!哈哈哈,于大海,你说你怎么没人家智慧,离婚时,你一个光人出了门,把什么都给了我,你说你傻不傻,你就不怕我嫁得更快?人家对老婆孩子怎么就不像你一样呢?李青的眼睛居然红了,闪出一丝泪光来。
李青的话把我的心情弄得酸楚起来,心里顿时充满了对她的歉疚。我说,他对你好吧?小三儿就小三儿,能给这样有身份的男人当小三儿也不错。
可惜在他身边,像我这样的小三儿不止我一个。李青酸酸地道,不过他总是有用得到我的时候。李青居然用了“用得到”这样卑贱的字眼,这可不像她一贯的谴词方式。
我的前妻李青就这样给人当起了“小三儿”。不过,李青说起来,倒没有别的小三们那特有的理直气壮神采飞扬。她话里虽透着贱样,可眼神却是有些无奈的。
不失眠的日子是快乐的。十年来,我每天在列车上南来北往,像窗外的风景一样,送走冬天,迎来春天。我睡在列车上那张属于我的小床上,在那固有的频率里,感受着时光的欢欣奔跑,就像我身子底下这辆永不疲倦的列车,就像那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风景。但是,总有一天,我将失去这张小床。随着日子在铁轨上的铮铮流逝,我已经逼近我的退休年龄。退休的那一天让我感到恐惧——拥有这样一张床的我,如果不再是一名列车员,将只能是一名乘客。如果那样,就算作为身体的那个我不再失眠,可作为精神的那个我呢?他将永远流亡在路上,并从我的身体里跑出去,为下一步的行程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那将是怎样一段永无归宿的流浪之旅啊!
这样一想,我的内心就失去了安宁!
最好的解决方式,自然是找到那样一种来回摆动的床,即便它不在行进中的列车上,只要它有那种振动的频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开始疯狂地迷上了两件事:上网,逛家具城。上网的目的,还是为了逛家具城。在我五十五岁的年纪上,我成了一名痴迷、冥顽、执着、且不折不扣的老网民,不是网龄老,而是年纪老。按人们的话说,很有一点老不正经。像我这个年纪的网民,他们上网的目的,肯定不会像我这样怀有如此低级的动机:只为了找一张可以来回摆动的床。

顾铮作品·台湾文学馆内的孩子们
找一张可以让我睡眠中的身体动起来的床,这愿望是如此强烈。回到地面上的日子,成为我在网络和家具城之间的疲惫往返。我跑遍了南城几乎所有的家具城与家俬店,随着退休日子的临近,我在希望与绝望中煎熬:寻找、放弃,放弃、寻找。找找找,找床找床找床,找一张让我安生的床!
终于有一天,在南城一家豪华的家俬城里,我发现了希望。
“您说的是一张会动的床?”家俬城的老板问,口气里夹杂着大蒜味的浓郁与热情。
“对,价钱可以不考虑。”
家具城的老板听出了我的意思,态度越发地热情。他向我推荐一张价格昂贵的水床,并破例让我在那张贵重的样板水床上试躺一下。我躺上去,那水床果真发出哗啦啦的流水声,并随着我身体的移动来回摆动。遗憾的是,这种摆动很快就停下来了,只要你不再翻身,那水床就一动不动,与一张普通柔软的超大席梦思并无异样。而且水流的哗啦声,也不是我习惯的咣当声。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张水床的功用,让它真正“动”起来,我只得隔一会就翻一下身子,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正在油锅里躺着的煎饼,等待被一只锅铲翻过身去。但我等不到锅铲,我只能自己翻动自己。睡在这样一张床上,就算我不再患上失眠症,也得患上多动症。这种只适合对儿童描述的病,把它冠在一个五十多岁就要退体的老头身上,说出去是个多么丢人的笑话!
显然,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永动床。它不是我的床摆,更不可能成为我生命的钟摆。家具城的老板还在激情洋溢地向我推销这张床的功用,他打开床头的一个电源控制器,说,您瞧,哥,这床还可以调水温,哥您想要什么温度就什么温度,绝对冬暖夏凉,一个天然空调,保哥您睡上去延年益寿!
这人一听就是东北口音,且是铁岭口音。这几年,这种口音随着一帮娱乐小品与脱口秀的走红,正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流行,并企图走出国门。我在列车上几十年,对全国各地的口音早已熟悉无比,对各种方言的判断,可以精确到县一级的城市。这个来自铁岭的家俬老板继续向我游说:哥您瞧,这床多好!哥您可值得花这个钱,睡这样儿的床,保哥您多活二十年!
我在列车上已经被数不清的东北人叫过“哥”,这耳熟能详且亲热得让人起腻的叫声,我听到过估计能有几万次。眼下我当然对此岿然不动。
我用模仿得十之八九的铁岭口音对家俬城的老板说,不好意思哥,这床不适合俺,俺要的是它自己能动的床。
哎呀妈呀,碰上老乡了!哥您是铁岭的呀?俺看老乡的份上,再给您多打些折头,哥您看咋样儿?
我只好改用南城口音告诉他,这水床的确好,但它真的不是我要的那种床。
不就是张会动的床吗?要不,我请人给哥您专做一张?
老板及时发挥了他商人的机敏与耐心。这让我眼睛一亮,盯着铁岭老板问,这床可以做?
当然,我以前就是搞机械的,给它安个动力,它不就动起来了?
那太好了!老板您果真能请人做?
这有什么难啊,您说,您想让它怎么动?是像摇篮那样动呢,还是像小船那样动?
火车!像火车行驶在铁轨上那样动!
哎呀我的妈,那可不成!您这要求太高了,像火车那样动,那得多快的速度呀,哥您是要床还是要车啊?
不是,不是快的问题,是振动。我伸出手,在空中做出相应的手势与动作,一边在嘴里模仿出那种有节奏的咣当声。
哥您可真是个怪人!家俬老板望着我,用手掩住嘴,努力克制着想笑的欲望,弄出一脸怪异的表情。
我只好向他谈起我的工作,解释我要这样一张床的原因: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担心自己的身体习惯不了,所以想要一张这样的床。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哥您放心,我一定找人帮您订做一张这样的活动床!铁岭老板热情地承诺道。
不是活动床,是摆动床!能像钟摆一样有节奏的摆动,也可叫它床摆。我特别强调道。
老板大度地笑着,冲我挥挥手,说,我知道您的意思,让它像火车一样上下一颠一颠的,不就得了?再给您安一段火车在铁轨上的录音: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是这样不,哥?
我放下心来,高兴地留下了一笔诚信金。
接下来的事,就是等待着那张床的问世。等待它来到我的身边,并给我带来身心的永远安宁。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那个家具城老板的电话。他告诉我,我要的床,他已经请人做好了。
不过,得先给哥您声明,这床可能会很耗电。电话里传来那老板浓重的铁岭口音。
“耗电倒没关系,只要床好用就行。”能量只能相互转化,这一点我知道。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法违背能量守恒定律。
那您啥时来看看?
“很快。”
我想见这张床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年轻时候对李青的渴念。这趟列车正在返回南城的途中,只要两个多小时,它就可以停靠在南城漂亮的新站台上了。
车一到站,我就给家俬城的老板打了电话。
老实说,看到那张床的第一眼,我很失望。它就是一张普通的原木床,它看起来工艺并不复杂,我试着躺上去。铁岭老板接通了电源,床动了起来,一种奇妙的感觉升上来,我果真找到了那种熟悉的晃动感。原来,床的底部有一台微型电机。但是,这种奇妙感很快就被另一种感觉所取代,床底下的电机发出急促而沉闷的哒哒声。这哒哒哒的声音,就像一记记闷锤敲打在后背上,让我的身体感到莫名的紧张。
怎么样哥?这床您满意吧?
我努力地辨析着床底下的哒哒声与列车行进在铁轨上的咣当声,眼里露出了迟疑。
铁岭老板说,哥,这床可不是普通的床,它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这世界上,除了哥您,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看上它,是不?
我从铁岭老板软中带硬的语气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不管怎样,这床我必须买。是啊,这世界上,除了我,还会有谁要这么一张奇怪的床?铁岭老板没说错。
我说,这床我要了,可是,它发出的怎么是哒哒哒的声音?不是我想要的咣当咣当声。

顾铮作品·我们是美丽的
铁岭老板一拍头,说,俺该死!忘了给哥您放录音!您瞧,录音开关就在床头,这声音可是再真实不过了,是我半夜里专门跑到铁路边,贴着路基录下的!
声音的确很真实,是列车行进时的咣当咣当声。只是它无论怎么真实,都无法掩盖床底下那种混杂的哒哒声。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付清了床款,让家具城派出的送货车将它运进了我租来的小屋。
哒哒哒,我低估了它的威力。听久了,那是一种令人想发疯的声音。事实上,这张床不仅不能解决我的失眠问题,反而让我出现了久已不现的幻听。这幻听不再是咣当咣当,咣当咣当。而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终于对这张高价买来的床感到绝望。我就在这样的绝望中迎来了我的退休。
退休后,我的前妻李青经常来看我。她已经四十八岁,也已经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离婚后的十年里,她分别给三个身份不同的男人当过“小三”。眼下,她业已进入更年期的身体,已经对扮演这一角色失去热情与兴趣。她退出了“小三”的生涯,开始了安静的独居生活。
我们的女儿于洋早已上大学。两年前,她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没在国内念过一天大学,就直接开始了她的留洋之旅。于洋是个争气的孩子。我们的离异和她妈妈的“小三”身份,一定让她感到了无比强大的驱动力,驱使她发奋和努力。她终于越过太平洋,把她可笑的老爸老妈永远甩在了大洋的此岸。
李青有时来找我聊聊天。她来的时候,一般是晚上。白天她还要上班。她一进门就说于大海,咱们于洋来电话了没?我说于洋不给你打电话,当然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她说那可不一定,她心里可惦记着你呢,每次来电话都问,我爸还失眠不?要不要从美国寄点药回来?这孩子可真有良心,你可是一天也没带过她!
李青和年轻时有了明显的变化,到快老时竟然变得有些咋咋呼呼起来。
我指着铁岭老板为我特制的那张床,说,这玩意儿,一点用也没有,能不失眠吗?
李青噗哧一笑说,于大海,你干嘛不要求公司返聘你?这样也好为你省点买床的钱。要不,你去列车上做义工吧,啥也不要,就要一张床位就行了。
我也笑起来。李青现在对人十分宽容和理解。如果年轻时她能对我这么容忍,兴许我们就不会离婚了。我说,我现在每隔几天就上一趟车,重温一下旧梦。退休后这点钱,就准备扔在路上了。
李青说,这样好这样好,就当是旅行了。等我退休了,也陪你去坐火车。说实话,在铁路系统干了半辈子,我还真没去过几个地方呢,不像你,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嘿嘿笑道,不是大半个中国,是大半个中国的铁路线。
李青说,都一样,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退休后,我也坐火车去旅游。我就不相信,人在列车上呆久了会下不来,会得什么失眠症。于大海,你以前是骗我的吧?
我不作解释,随她怎么想吧,反正我这辈子骗谁也不会骗李青。失眠又不是什么好滋味,谁不想睡得又香又甜,梦里抱个娇媳妇呢?可我不行。我的身体静不了,它离不开列车上的摆动。

顾铮作品·心有旁骛的选举造势者
不出门乘车的日子,失眠就像魔爪一样,攫住我的夜晚。这种时候,我总是无计可施,只有起来上网。我曾经闭上眼睛,无数次地尝试让自己的身体像火车一样摇晃,我假想自己是在一列行进的列车上,并在嘴里发出阵阵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但是,我的努力毫无用处。我丝毫也不能摆脱失眠对我的折磨。有一天半夜,我坐在电脑前,忍不住把这些困惑与痛苦写下来,并将之冠以标题“寻找永动床”。我把这个求助的帖子发到了网上。
很快,我就收到了各种天才的回帖。这些回帖中包含着各种物理学的设计,有单摆的,弹簧振子的,杠杆的,活塞的,滑轮的……这些设计融入了种种物理学的原理,另外还有力学的,电学的,电磁学的,还有仿生学的。有一位网友甚至提到了地震波:地震波既有水平方向的横波,又有垂直方向的纵波。这位网友说:“遗憾的是,我也不知该如何制造出这两种波,而又不引发地震。”
伴随着各种奇特的构想,网友们还附来了精心设计的图纸,有的还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其准确程度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三位数!天啊,我们的网民中竟有如此诸多的天才!我不得不惊叹科学的伟大,终于理解什么叫“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谁说我们中国人缺少科学的想象力与创造的才华?如果不是为了生计奔波,广大的网民们中说不定就能诞生出几个国产的牛顿与爱迪生!
“寻找永动床”的帖子,很快就成了网络热帖,被网友们顶到了各大论坛的榜眼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回帖,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内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的惊喜,网民们多么可爱,网民们多么热情,网民们多么善良,网民们多么智慧,网民们多么天才!
我的邮箱里被各种奇思妙想的邮件塞得满满的,阅读这些邮件,成了我退休后最大的快乐。我从中精心挑选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连同他们所设计的图纸一起打印出来,找到了那位南城家俬城的铁岭老板。老板一见这些图纸,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他抖动着脸上的肥肉,说,哥您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行,图纸您放下,我马上请人去做!
但这些图纸一旦落到实践上,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床做了一张又一张,图纸改了一次又一次,工艺也改了一回又一回,南城家俬城的那个铁岭老板最终对我要的床失去了兴趣。最后,他居然说了句颇有水平的话:您想要的永动床,只有上帝才能造出来。
如今,那个“寻找永动床”的求助帖子依然挂在网上,它不再是被网民们狂顶的热帖。就像许多流行过的网络热词一样,热过一阵后,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这就是网络的力量,也是网络逃不掉的局限。作为一个步入老年的失眠者,我依然在寻找那张可以来回摆动的床。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就像我不知道我人生的终点在哪里。好在我每隔两天就会去坐一次火车。前两年,我是一个人上路。现在,是两个人。李青也退休了,她执意要在火车上陪我,我只得从命。南城站台的同事们一见到我俩,就笑着招呼:老两口又坐火车玩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