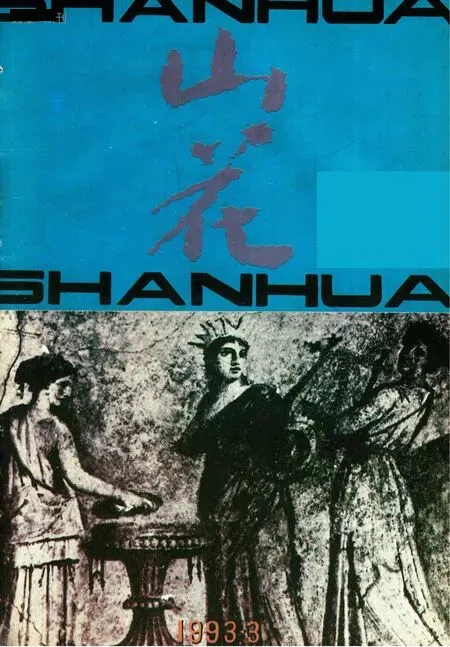在诗意与幽暗之间穿越——张学东短篇小说论
张富宝
在诗意与幽暗之间穿越
——张学东短篇小说论
张富宝
无疑,短篇小说是最简单也是最困难的一种小说文体。说它简单,是因为它篇幅短小,便于掌控,常常作为小说家创作的“入门功课”;说它困难,是因为它是最接近于诗的一种小说文体,也是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一种小说文体,——它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需要深厚的思想境界,这对于青年小说家来说的确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短篇小说的成败完全可以视为青年小说家创作成败的一杆标尺,因为短篇小说作为其小说创作的源点和开端,具有源发性的意义,不仅最能显示一个青年作家的艺术才情与禀赋,也最能显示其文学的精神气象和格局。对于张学东来说也是如此,短篇小说在其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我们进入其艺术世界的最好通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短篇小说都是有难度的写作,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在70后作家群中堪称突出。
一
读张学东的作品,总能感到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也就是说,其作品中的很多场景和细节,往往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特别是他小说中的人物仿佛就“潜伏”在我们身边,他们的身上总会让读者读到自己的一些影子,读到你过往的一些生活和情感,包括你的一些记忆、梦幻和感动,甚至一些欲望、惆怅和挫伤等等,尤其是童年时期的那些晦暗不明的情绪、梦想和爱恋,那些挥之不去的焦虑、失落和困惑,在张学东的笔下更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这种熟悉感和亲切感的存在,充分说明了作家对生活的忠实和热爱,对生活体验与生活真实的精到的艺术把握。《寸铁》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中描写的男孩子玩游戏时对枪的那种依恋,对枪的火焰和威力的那种喜爱,对持有枪的那个人(如能制枪的“汪铜”)的那种崇拜,仿佛一下子就把人带回了童年的情境之中。其实,在我们的青春记忆中,也许都有汪铜那样的玩伴,那样一个“少年英雄”,“他手里的那支火枪在我们这里是一个神话,我的一双眼睛是这个神话最有力的见证。”的确,在我们过往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柔软而温暖的东西,所以与它们的相遇总会让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感和熟悉感,有一种别有意味的趣味感和生活感,——我觉得这正是好小说带给人的一种诗意,它能很好地把生活与想像连接在一起,让人流连忘返、回味不尽。尼采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1],也就是说,人生中可能充满了苦难、不幸与悲剧,但面对它时,我们不应该一味去痛苦、忧伤与绝望,而应该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关注它,去欣赏它,去超越它。我觉得在张学东的小说里面,他正是把人生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加以审视和表现的,所以他的小说就具有了一种特别的诗意。

叶永青三块石头布面丙烯150×200cm2005
进一步而言,我觉得这种“诗意”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这种诗意来自作家那种深广的同情和悲悯,没有同情和悲悯,就不会有诗意。所谓“同情”就是在写作中,作家是完全和他的人物贴在一起的,他是从人物的处境出发,设身处地去表达他们的心灵,传达他们的情感,走入他们的世界,同他们一起呼吸,一起欢乐,甚至一起哭泣。而所谓的“悲悯”就是站在一个超越性的视角,对这些人物进行一种关怀和包容,让作品充满一种“祝福感”[2]和“诗性正义”[3]。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应该能够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张学东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譬如《剃了头过年》中母亲的“笑”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诗意,其实这种诗意就是人性之光,它像灯一样照亮了生存的苦难和黑暗。小说写快要过年了,家中却一点过年的气氛也没有,爷爷的死使整个家里显得阴郁、沉闷。但是因为奶奶和母亲的坚持,父亲还是给五个孩子推了一天头准备过年。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年三十那天父母被游街批斗,父亲甚至被污辱性地剃了“阴阳头”。这突然的变故几乎粉碎了孩子心中对“年”的所有幻想,家里的气氛变得更为严肃、凝重。然而这时候母亲“不合时宜”的咯咯的笑声让人为之一振,它顿时冲开了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霾,母亲不仅把父亲从头到脚扫了个干净,并且还对几个孩子说“你们几个都站过来,让我好好扫扫吧”,终于小说把“一个沉重的关于生活、社会、历史的故事,转化成了人性力量的故事”[4],“剃了头过年”这个“老理”焕发出一种巨大的救赎力量。可以说,母亲的“笑声”里包裹的正是作家的同情和悲悯,它使张学东的小说作品具有了“深远的意境与不俗的气韵”。[5]
其次,这种“诗意”指的是一种“灵魂的记忆”,它更多地源自于我们的童年时期,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的生命之中。所谓的“灵魂的记忆”其实是一种深沉的爱,这种“爱”,是对生活的关怀,是对生命的体贴,是对诗意的信仰。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种爱还意味着对文字的爱,对文体的爱,对自己笔下一切事物的爱。正是因为这种爱的存在,所以我们常常能从张学东的小说中读到那种特别的诗意,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妙的相遇——没有电光火石,但也刻骨铭心。在那一时刻,你会发现一种情感的暗流迅速地涌向了你的全身,彻底地征服了你,让你有无限熨贴之感。这样的一种感受,其实正是文学独有的魅力,正是文学独有的功能,它总是以特有的形象、情感、思绪给我们诗性的滋养,让我们的灵魂不至于钝化、干涸和贫乏,——这也正是文学的那种独有的“诗意启蒙”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同于“理性启蒙”,它不是用理性、规范、道德、逻辑和思想等等来对人进行规训,它是以情感对情感、以心对心,是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感化。比如说《寸铁》当中,小主人公“我”对小女孩“小扁子”的情感和心理,就让人回味无穷。“我只好伸手去接那盒火柴,却不小心碰着了小扁子的手掌心,里面热乎乎的,就连那盒火柴也投射着那些微热,那是女孩子的特有的阴柔温度,它带着娇羞虔诚谨慎和略微的慌张。最重要的是(值得坦白的是),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生活,我以为女孩的手应该是这样的,既温暖又潮湿,或者还应该有点清凉的感觉,将它捏在手里你会倍觉怜爱与疼惜”。这段文字极为准确、传神地把那种敏感的、细微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把那种处于懵懂时期的、对性意识的初体验诗意地呈现了出来。这正是一种“灵魂的记忆”和“诗意的启蒙”,在张学东的小说中,这样温润的文字和细节随处可见。想想看,如果没有了这种东西,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地单调和难堪。无疑,张学东对人的那种细微心理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尤其对“少年人”的那种心理状态的把握,——他能把“少年人”那种丰富的、复杂的,有时是晦暗不明、深不可测的一些东西,层层盘剥、鞭辟入里地揭示出来。事实上,这已成为张学东较为明晰和成熟的一种艺术风格。
最后,这种“诗意”是一种懵懂之美,是一种青春之美,这与作家叙述视角的选择和故事内容本身有关,更与作家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有关。对懵懂之美,青春之美的书写是张学东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张学东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的短篇、中篇小说中,在其长篇小说《西北往事》中更有集中的体现。我们发现,在张学东的小说中,儿童往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双重的角色和功能,既是叙述者又是行动者,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他的存在使得小说获得了一种叙述学上的张力。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张学东的叙事动力首先来自自身的成长经验,正是“从自我出发”的创作欲念驱动着他不断勘测童年这块“富矿”。因此,善于运用儿童视角进行叙事,把小说放置在过去的历史空间中展开,使其充满空隙与迷惘,回忆与想象,犹疑与彷徨,这已经成为张学东小说的诗意源泉之一。进而言之,儿童视角本身就是一种诗意叙事,本身就具有一种迷人的真实感、懵懂感和诗意感,它往往带着纯真、圣洁和至善的光辉。事实上,真实感、懵懂感和诗意感正是张学东小说美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儿童视角是一种本色化叙事,往往能祛除道德化的议论和理性的说教而本色化地捕捉原生态的生活世界,——那是一个忧伤的、彷徨的、焦虑的世界,那是一个感性的、情感的、形象的世界,那是一个矛盾混杂、真假难分、善恶莫辨的世界,或许,那也正是小说家的世界,是张学东最为迷恋和倾心的世界。因为在张学东看来,世界并不是清晰的、完整的、和谐的,而是危险与美丽、幸福与忧伤、矛盾与困惑并存的,它需要艺术家的烛照与穿越。此外,儿童视角是一种浑沌叙事,因为儿童总是以一种好奇的、梦幻的、问询的眼光观察和打量世界,他眼中的世界总是朦胧的、浑沌的和纷杂的,他往往能从事物丰富的表象直观到事物被遮蔽的本质,因此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儿童乃成人之父”(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在我看来,这种“诗意”,可以不是那些完美的、正确的、光荣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有时可以是一些忧伤、疼痛、遗憾还有失落的事物,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些残破的、污浊的、带点丑陋的东西,这正是一种“感伤的诗意”。波德莱尔说,神秘和悔恨是美的特征,忧郁和不幸是美的伙伴,因此,他把美定义为“美是某种热情而凄惨的东西,它有点朦胧,让人猜测。”[6]张学东的“感伤的诗意”正如波德莱尔的“美”一样,也充满浑沌与幽秘的意味,需要细加品位和“猜测”。
二

叶永青单飞布面丙烯200×150cm2006
张学东是一个很有控制力的小说家,对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更是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他的短篇小说熟谙“小”与“大”的辩证法,常常能在细小的地方显现出大景观来。从小处入手往往是短篇小说的“天性”,它不可能容量太大,不可能太铺张,不可能如江河之水汪洋恣肆,它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面用极简洁的笔墨来传达更多的东西。所以说,要从一个小的切口“切”进去,但是不能局限在那个“小”上,而是要从里面见出一种大的、纵深性的东西。“切”这个词让人感到有一种精准和锐利,也让人感到有一丝痛快和畏惧,它仿佛医生手中的银光闪闪的手术刀,直达病痛的中心——这无疑已成为张学东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切”,而是切口的“纵深”,是切口的典型性、丰富性与复杂性,是切口的社会历史文化含量。短篇小说的真正难度在于,它要在小与大、轻与重、快与慢、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想像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因为过分注重艺术技巧往往会使其显得矫揉造作、空洞轻巧,过分偏重内容又容易使其肿胀笨拙、缺少轻灵的意味。可以说,张学东的短篇小说大都是平衡感很好的作品,不仅切得“精准”(技艺精湛),而且更有大的“纵深”(内涵丰厚),这正是他区别于其他小说家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并不贪恋、炫耀和玩弄艺术技巧,而是更注重作品的力量、气势和境界。
具体说来,张学东短篇小说的“纵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张学东的小说常常触及到广阔的历史空间、丰富的时代信息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张学东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很感兴趣的作家,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的叙写往往渗透着现实的意味,对现实的关怀又往往隐含着历史的景深,这种独特的写作视角大大拓展了其作品的意义空间,他的短篇小说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这一点,如《喷雾器》、《送一个人上路》、《等一个人回家》、《放烟》、《羔皮帽子》等等莫不如此。不难发现,张学东对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变迁以及人的命运与遭际情有独钟,对20世纪60、70年代的时代风云难以释怀,他总是企图在裂变与匮乏的时代境遇中审视人类生存的困境,考量人性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艺术敏感,也是一个作家的道德担当,正是在这一点上,张学东与其他70后作家鲜明地区分了开来。譬如《送一个人上路》写曾任生产队长的祖父信守承诺,为绝户饲养员韩老七养老送终的故事,小说在“轻盈结构中寄寓了沉重的历史感”,“展现了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人物心理和精神道德上的巨大变动”(陈思和语)。[7]小说触及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纷繁变乱的社会转型期,当曾经的农村革命所许诺的“乌托邦”化为云烟的时候,谁来承担历史的后果和责任?在这篇小说中,祖父是以一种民间道义的方式,以一种素朴却又庄严的方式,甚至不惜与家人为“敌”实现了送韩老七“上路”的承诺。与此同时,小说还展示了祖父所代表的祖辈与其子辈之间在精神价值、道德观念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前者作为历史之“重”,后者作为现实之“痛”,它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作品变得深沉而开阔,——这正是张学东短篇小说的不凡之处。

叶永青画鸟布面丙烯300×200cm2006
其次,张学东的小说触及到了波诡云谲的人性幽微,启发我们要警惕事物的“表象”并要进一步深入到它的内里,见微知著,以小观大,充分把握事物以及人的内在世界的复杂性。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8]我觉得这一点用之于张学东的小说也颇为恰切,因为他的小说也“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常常把人带向“冥漠恍惚之境”。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张学东小说背后的幽微与黑暗的力量,我觉得那些东西才是最惊心动魄的东西,那也是张学东最善于表现的东西。所谓“幽微”是指一种晦暗不明的几微状态,一种不可测度的存在与奥秘。所谓的“人性幽微”,是指人的复杂而隐秘的人性状态,人的难以察觉的无意识心理状态,它有时候是指人在极端境遇中所迸发的人性之光,但更多的时候是指那些潜伏着的非理性的私欲和恶念,那些隐藏在人的本能之中的贪婪与阴暗。在人性幽微之处,往往最能显现出人的弱点与缺陷,人的困顿与挣扎,最能显现出瞬间的升华与沉沦的较量,刹那间的善良与丑恶的争斗。小说《司空见惯》一如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写的是平凡细微的生活:星期日丈夫在外钓鱼,在家休息的妻子用丈夫忘带的手机接了一个疑似女人的电话,于是妻子的内心便再也无法平静,种种怀疑和猜忌连绵不断,莫名的惊恐与不安使她如坐针毡,最后在愤怒中游逛了一天的妻子等来的却是丈夫遭遇不测的噩耗。同样,在《海绵》中,我们看到一次小小的纠纷一步步酿成了人命大案;在《羔皮帽子》、《扑向黑暗的雪》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人性善恶美丑之间的纠缠……正是在如此微小的地方,张学东极为精准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状态,他让我们在不断地审视自己的同时心生一种颤栗。
最后,张学东的小说还触及到了权力体系、权力结构以及思维惯性对人的创伤,——作品浅层表现的是庸常的人生世相,深层揭示的却是世俗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不仅写出了人在世俗生活中被同化、异化的过程,而且揭示了沉潜在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权力意识对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人物思想行为的支配与操控。譬如从表面上看,《寸铁》是一个关于少年复仇的故事,实际上,我觉得这篇小说表达的不仅仅是复仇,而更是对权力结构和权力社会当中的人的悲剧的一种思考,它展示的是权力对弱者的无微不至的伤害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性的变异和扭曲,我觉得这才是这篇小说中最深刻的东西。当居于权力顶端的生产队长用铁锹劈杀汪铜家的大花狗时,他伤害了汪铜;而当汪铜为了报复胡队长时,他同样居于权力中心,甚至更为残忍地杀死了胡队长家的狗,并且伤害了无辜的小扁子和“我”。这其中的暴力逻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最后所有的人都成了权力的受害者。同样,当《应酬》中的处长对出租车司机进行疯狂地殴打时,正是一种“权力无意识”和现实焦虑推动他去施暴,潜移默化的“权力”成了他们的共同伤害者。正如评论家汪政所说:“在张学东的作品中,这些伤害的力量有时并不仅仅在哪个个体身上,有时它就是一种默契,一种从众的选择和氛围。”[9]如果说短篇小说中权力伤害主题还不够集中明朗的话,那么在长篇小说《超低空滑翔》中,张学东则直接把笔触对准了权力体系、官僚机构的象征——航空局。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另外的两个人,一个是写出《城堡》的卡夫卡,另一个则是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权力结构作了深入的描述,并对个体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败进行了犀利的刻画”。[1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学东正行进在这条路上。
三
张学东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中大都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在有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直接,在有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含蓄,甚至在有的作品中是通过那种表面的黑色幽默或诗意情境来表现的,需要细细挖掘和品味。美国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仪式。”[11]显然我们所能看到的电视新闻对悲剧事件的阐释往往是片面、武断而表层化的,跟张学东小说中读到的那些东西大为不同,张学东所感兴趣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的“悲剧”事件和它最终的结果,而是它背后的造成悲剧的深层次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张学东对小说有他独特的理解,他的小说总是企图告诉我们某种被遮蔽的“真相”。就像小说《寸铁》当中汪铜的悲剧,从直接的原因来说,是因为恋母情结导致的变态心理,但是我觉得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才是这篇小说关注的重心。那么,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现实情境,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还有那种隐蔽的无处不在的权力结构与权力体系。
不过,在企图告诉我们真相的同时,张学东往往又巧妙地模糊或者说解构了这个“真相”,使得一切看似显而易见、顺理成章的东西顿时变得晦暗不明。小说《寸铁》的最后有一段补叙,看起来不经意,但非常有意味。“我还听说那晚跑去报信的人好像看见胡队长从汪铜家的院子里一跩一跩地打着哈欠走出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把一件看似那么简单清晰的事情在瞬间给推翻了,由此引发了各种新的可能性。其实这句话,显示的是小说的一种复杂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困惑和疑问,张学东把“问题”又重新抛给了我们,他实际上没有给我们任何结论。“谁知道呢”是一种思考的、探索的状态,它表明独断论永远是不可信的,悲剧永远是一个疑问,正是这种“疑问”把历史和现实强行带入我们的生活处境之中。因此,“谁知道呢”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叙事张力,它甚至颠覆了前面所有的故事叙述,使小说带上了“复调结构”的特征,它也构成张学东小说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譬如在短篇小说《喷雾器》、《送一个人上路》、《扑向黑暗中的雪》、《羔皮帽子》、《司空见惯》等作品以及中篇小说《坚硬的夏麦》、《谁的眼泪陪我过夜》、《艳阳》、《清水浑浊》等作品中都带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说,我觉得小说家最重要的不是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观察和结论,而是要给我们带来一种困惑和复杂性,让我们不再用一种单一的视角去看问题,而是学会用复杂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正是小说叙事的思维智慧和现实意味。

叶永青伤痕布面丙烯200×200cm2007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吸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的行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相浮现出来”。就像《寸铁》中汪铜在无意之间用枪对小扁子的那种伤害,就像《应酬》中处长对出租车司机的伤害,其实就是“一种无法预期的状态”,而且是一种无法预期的“必然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可怕的,最让人恐惧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些貌似偶然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无法预知,难以逃避,而这些东西往往会导致惨烈的悲剧。当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又往往只关注那些直接的、外在的因由,而常常漠视或忽略了那些生长在晦暗之中的“存在面相”。因此,张学东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关注悲剧本身,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迄今未知的“存在面相”。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茉莉香片》,写的是一个瘦弱的有点女性化的男学生聂传庆的悲剧故事,他有些莫名其妙地爱上了父亲曾经的恋人的女儿言丹朱,最后在山上莫名其妙地想掐死她。小说最后写道:“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跑不了”成了聂传庆一生的悲剧状态,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命运”,张爱玲写得近乎残酷,她深刻地写出了爱情的悲剧与人性的悲剧。同样是写悲剧,我觉得张学东更为开阔些,更有社会历史容量,他把悲剧置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拷问之中,于是那些汪铜们的悲剧,贱生们的悲剧也因此超越了个人的悲剧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的悲剧是“跑不了”的,而张学东笔下的人物的悲剧呢?
注%释:
[1][德]尼采:《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编译,三联书店1986年,第105页。
[2]李建军:《祝福感与小说的伦理境界》,见《文学因何而伟大》,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李建军认为小说家应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表现出“健康而温暖的道德感”,显示出“一种伟大而崇高的伦理境界”,从而体现出一种美好的“祝福感”。
[3]参见[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努斯鲍姆认为文学和情感能够带来畅想和移情,能够带来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文学对于那些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能够使得读者和旁观者尽量深入和全面地掌握事物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一种“诗性正义”。“诗性正义”要求读者尽量站在“中立的旁观者”的位置,尽量以旁观者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同情地去了解每一个人,并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世界进行反思,对事物作出中立和审慎的裁判。
[4]张新颖:《母亲的笑声、现实和叙述——谈张学东的几篇小说》,《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5]张学东:《作家的进与退(创作谈)》,《西湖》,2008年第11期。
[6][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页。
[7][9]张学东:《应酬》,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69页,第58页。
[8]叶燮:《原诗》,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0页。
[10]http://new s.xinhuanet.com/book/2010-10/08/c_12635648.htm
[1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7页。
- 山花的其它文章
- 智慧的劫掠与死者的狂欢——从鲁迅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