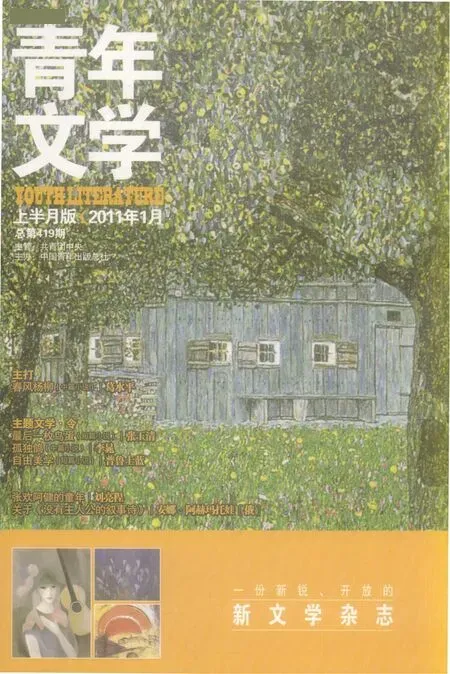找寻自己的地域性[评论]
文/红孩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失眠,尤其是在凌晨三四点钟。索性起来,在炽亮的灯下看书。看熟悉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偶尔也看散文。我的总体感觉是,大凡有重大成就的作家,其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譬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孙犁、汪曾祺、陈建功、铁凝。
二〇〇八年,我在《文学报》发表了《鲁迅没有得过鲁迅奖》一文,在文中我提出看一个作家或诗人是否成熟,或有无大的成就,要看三点:第一,这个作家的作品在推动民族的文化思想进程中是否有大的担当;第二,小说家是否塑造出经典人物,散文家是否有名篇,诗人是否有名篇或名句;第三,作家或诗人在艺术表现上是否有所创新,尤其是在散文、小说上能否形成自己的地域语言风格。不用说,在现代作家中,我们有相当多的作家能够进入这个层次。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就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开始步入文坛后,我们不难发现,在小说、散文、诗歌,包括报告文学的创作里,我们的作家几乎全军覆没。想来,文学是多么悲哀!其实,文学并没有怎样,问题是发生在人身上。这些年我一直在编各种散文年选、大系,同时还编了五年的年度争鸣小说选。每当面对年度的大量作品时,我总希望能发现一篇卓尔不群的作品,但每次都失望了,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我几乎看不到一篇我所期望的。

■美术作品:东山魁夷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是当下的小说缺少以下一些基本的要素。第一,小说是叙述文体,但不能只叙述而没有描写。当下的小说,你几乎看不到大段的对山川、河流、草原的描写,即使对人物的刻画描写也很少;而更多的是像老太太的絮絮叨叨,很琐碎,很无聊。第二,小说要塑造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渐入,文艺创作的各种表现手法纷纷被国内作家所接纳、效仿。在注重形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作家在主观写作上发生了本质的转化,即:由过去的我看我说我想变成说我看我想我,具体讲就是作家由关注社会转变成关注自己——也就是整体向内转。这样一来,小说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必然要发生转变。我曾经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即:作家写作是从我出发,以我们的阅读接受结束。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在西安的一次散文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就是:“从我走向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发出对文学的呼唤。记得贾平凹会后对我说:我们搞了几十年没有说清的问题,你今天给说明白了。后来,在二〇〇九年第一期《小说选刊》上,贾平凹在给一位业余作者的信里,标题也用的是“从我走向我们”。
由此,我想谈谈葛水平的小说和散文。葛水平出生在山西农村,是典型的六〇后作家。关于六〇后作家,前些年《青年文学》等刊物曾给过密切的关注。这代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四清”和“文革”时期,成长于七十年代。可以说,他们是生长在政治挂帅、经济贫穷的时代。即使八十年代考上了大学,其所学的知识也是苍白的。而生活经验呢,比起生于五十年代的知青作家,他们也少了许多厚重,形象的说法是,先天不足。八十年代,当文学如火如荼时,这批六〇后大都在学校,这样就使他们整体失去被社会认可的机会。等到了九十年代,当六〇后要登上舞台的时候,文学已经整体向内转了。向内转的直接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了现实,开始回避矛盾、躲避崇高,进而使得作品越来越私人化、小众化了。文学与社会的脱节,势必会造成文学与读者的脱节。因此,文学不可能再出现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再出色的作家也很难靠一两篇(部)作品而闻名于文坛。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学圈子里,有的人已经出了十几本书,甚至得过什么大奖,可一到社会上就什么也不是。有人说现在的文学其实是回到了它应有的常态,过去那种用文学去图解政治、去喧嚣政治的轰动效应,很不正常。我不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文学是对社会的反映。当下的文学,为什么会遭到社会的冷漠对待,还不是我们创作者本身冷落了社会?多年前,一位军旅作家在谈到生活和创作的关系时曾说:一个冷淡了人民的作家,人们没有理由不冷淡他!这话影响了我很多年。
我以为,像葛水平这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是不缺少生活的。比起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作家,他们还有着一定的历史责任感。那为什么这批作家没能担起文学的大梁呢?我想,原因至少有这样几点:一是在思想意识上,对国家、民族缺少大的担当,即使是文化的担当,也远不及建国十七年的那批作家和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二是在文学作品的厚度上,缺少划时代的具有宏大叙事的作品;三是在创作技巧和语言上没有独特的创造性,有相当多的作家没有从文学规律上去解决问题,而沉湎于对结构和词句的具体细节进行推敲,就像光研究刀工了,却放弃了整体菜系的总体把握;四是知识缺乏更新,尤其对当下发生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即使触及了也是对生活的滞后描写。我这样说,或许刻薄了些,但现实确实如此,何况我也身在其中呢!
就葛水平的创作来说,我喜欢她鲜活的地域乡土语言,这也是她有别于其他女作家的显著特征。同时,她对农村农民从血液里有着先天的观照与忧患。因此,她的作品常带有一定的阳刚之气。然而,光凭这些,还不能担当起一线作家的重任,至少她的文字还需要打磨,要向乡土文学大师赵树理、孙犁、刘绍棠学习,使文字更节制更准确更文采飞扬更体现浓浓的文化氛围。这是我对葛水平所期待的,也是我对六十年代作家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