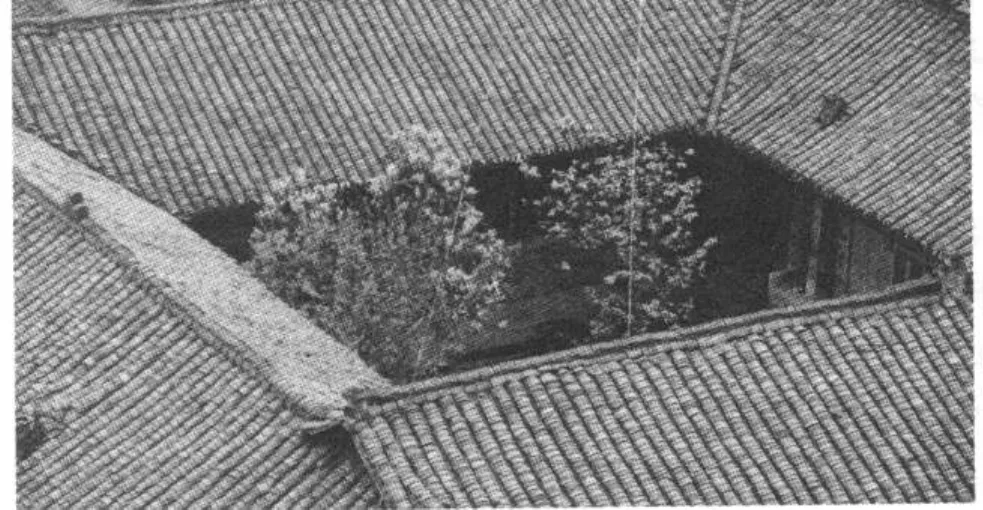纷乱
□许松涛
纷乱
□许松涛
A那个小姜,离开大院也有好几年了吧。至今,我依然一直在怀念这个小伙子。当时他才十七八岁光景,八月里穿着一件灰白的单衣,正在门卫室忙来忙去,不亦乐乎地布置他的理想色彩很浓的小家。他考虑的不是没有道理,批发了些酱油、味精、食盐、肥皂和打火机之类的日杂商品,摆在简陋得可怜的货架上。这一切是他从这60户人家的日用所需考虑的,按理也能多少为他挣点收入。可是这个院里,精打细算的主妇斤斤计较惯了,算计着过日子。久而久之,鲜货变成了陈货。小姜的货卖不动。可能是小姜给人的感觉有残疾,他的一双眼睛总是朝天翻白眼,说话虽然入情入理,语速也快,口齿清爽,但有一个不好的面相,让人们一见就心生恐惧,也许这相貌,把女人们给吓跑了,虽然他很买力,很诚恳,但时代已经看不上这些。初来时工资微薄,他没有任何要求。我每次下班回来,都看到他在挥舞着大扫帚清扫甬道,或蹲下单薄的身子细细拔地砖缝、场院上的杂草,尤其是盛夏季节,烈日下,他的薄背心汗湿了贴在背上,可见嶙峋的根根肋骨。小伙子的勤快感染了我,有时与朋友相聚剩了些酒、烟什么的,立即想到他,想着他也该多少尝一尝这些男人都喜欢的东西。我这样做,也就一两次。每次他接住时,脸都刷的一下红了,有些羞涩,也有些激动,是被别人尊重的那种快乐。刚来时不愿谈吐,人家也很少与他谈吐,后来与我有些话说,话不多,人腼腆,心里是透亮的,能过事。冬天他上楼到各家各户的门前清扫,用抹布擦楼梯扶手上的灰,手冻得裂开一条条血口子。我劝他别擦,擦也等天暖了再擦吧。他摇头,仍固执地擦完每家每户的楼梯扶手。现在,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忠诚的门卫了。在他呆的两年时间里,我们院没有发生过一起治安事件,公共卫生也是一流的,被市政府评为“模范楼院”。现在这块唯一的招人眼前一亮的牌子,仍挂在院门外墙的一侧,虽是已如人心一样锈迹斑斑。一言难尽,可还是足可追忆,足可给人们一个提醒。
秋天来了,小姜单独向我吐出一句心里话:“我要走了,亲戚介绍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听到这话心里很酸,觉得我们亏待他了,冷落他了。我早先听他说过,这里一直不给他涨工资。现有的年薪只管粗茶淡饭,一点剩余也没有。想想一个才近二十岁的青年,身有残疾,家在农村,如果这样耽搁下去有什么奔头?不能一辈子呆在这里看门护院吧,就是一条狗也未必能做到,主人也不至于这样款待一条狗吧?
他一边用蛇皮袋装拣着酱醋瓶子,一边幽怨地对我说:我不想呆在这里了,我知道有人故意不给加工资,就想挤走我,抢我的饭碗。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听的人就不好问明,说的人也不必明说。这就是小姜给我的分寸感,只能替他惋惜了。一辆摩托三轮正在一旁场地上等他,也没有一个人出来送他。或许,他是故意悄悄走的。一个有些心灰的人。这很容易理解,要走,没有留恋的,倒不如不声不响地离开,给自己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吧。我没有过多的祝福,握了一把他的瘦削的手,代表了我想说而说不清的一切。如今我常常回想起这个小青年,他的勤劳,他的质朴,他的忠厚,他的不幸,他的残疾,还有他的不可能被涨工资背后的那一重暗伤……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谁能替他改变这一切?
嗨,到现在我还是称他为小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清楚他的乡土在何方。
B也就在众多的青年小夫妻恩爱得像胶化了似的时候,大院里有一对小夫妻彻夜难眠。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烦恼恰是别人期望的。为了赶走烦恼,当然先是请产假,看医生,找偏方,然后又是服大量的药,然后还是请长假,甚至不惜找专人陪护。使尽解数,肚皮还是没动静,或一有动静立即就流掉了。恨自己肚子不争气,让家人空欢喜一场,空忙活一场,空叹息一场,花钱,出力,还揪心。一看别人的小孩,一天天从无到有在院子里哭爹喊娘地满院乱跑,她就不由自主发抖,怪自己的肚子总不见动静。原来如花似玉的丽容,日渐在这种渴望而不可得的烦恼中煎熬,枯萎,身体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流产中瘦得弱不禁风。我偶尔见到她在楼底下走动也心生怜悯,大院里的人一见到这情景都想帮一把。可是,别的事还好说,她这个事,有力也使不上。从她家三楼向外搭起的厨房铝合金窗户里,常能看见一个八十多岁的头发花白的老妪身影颠颠簸簸。老人天天给这位孙媳妇递茶倒水,或者做些吃的给她滋补。无疑少妇请了长假静候佳音的。有没有求过送子观音很难说,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关乎子嗣繁衍的大事。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在众多人心里还是泯灭不掉的。这个女人年纪轻轻,如花似玉,却被一场生育大仗打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还遭人嘲笑白眼,谈何幸福美满?然即便是这样,仿佛还不是命中的沉重一击,又一波风浪仍在等着她接受蹂躏的摧残:弟弟突然患上尿毒症,急需大把金钱去挽救垂危的性命,这火烧眉毛的钱,又不知从哪里着落。祸不单行的厄运把青春的娇容霜侵似的打得黄皮寡瘦。百无聊奈中,我看到离小区不足百米外的一处新门店里的主人,正是刚刚流产不久的这个女邻居。店门口一处醒目的大招牌,写着锅贴饺、鸭蛋、稀饭之类的价码。我走过去,尽量享受这并不给人好心情的早餐。傍晚,我正在人流熙攘的广场散步,忽见摆着许多儿童玩具地摊的过道上正是她,立即蹲下来去挑选,她立即向我推荐什么最好,什么最让男孩喜欢。我该买点什么给即将回老家过年的小侄子呢?我也替她难过,是什么使她想去批发玩具摆地摊的,是不是心中的那种原始天性的母爱?她一定无数次幻想过,假若上帝有个宝贝赐给她,她就是这个世上最幸福最富有的女人了,即使没有了其他,给她个孩子什么不幸都愿意接受。那时她将买许多许多玩具给自己的孩子。只要有孩子,她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可怜的女人,刚刚尝到爱情的甜蜜就陷入灾难的重围,差不多卷入困顿绝望的漩涡,生活的笑脸被污秽苦恼涂满,被贫穷和死亡的压力打击得回不过神来。她还是那样让人惊诧地挺住了每一天!这股力量又是怎么诞生在她的心里的?地狱一般的暗无天日,给这个女人带来的将是什么命运的摧折?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仍不敢想这件事情。乡风对不怀孩子的女人很无情,素有“养个母鸡不下蛋,拎起往下摔”之类的民谣。舌头底下压死人,即使别人不说,自己的心理关怎么过得了呢?值得庆幸的是她终于怀上了,分娩了,现在孩子也走路了,能口齿不清地喊她一声妈了。每每打量这个皮肤白皙路还走不稳当的“小伙子”,心里就有一股陶醉的潮湿涌出来。
真得替他们庆幸,为母子暗暗喝彩!天遂人愿,毕竟想要的来了,虽然来迟了,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磨难,但毕竟如愿以偿了,多少还是个圆满的结局吧。只要想想,世上还有多少平凡的人,因为一个普通的愿望终生求索而不得,那又该怎样挺下去呢。“生活,意味一切都得挺住。”这是外国一个哲人所言,也是对无数的不幸者的安慰与歌赞。毕竟走过来了,回看万水千山,也不免宽慰几许。
现在这个年轻的妈妈正是给他的孩子买玩具的时候了。我没有看到她的孩子有玩具。她有了孩子,她卖过玩具,还劝我买过她的玩具,我相信每个妈妈都挖心割股地对自己的孩子真好,那又是什么夺走了妈妈手中已经拥有的那一大堆玩具呢?一个傍晚,我遇见这位年轻的妈妈,问她当初的那些玩具放在哪里,她的回答让我心凉:早就让给别人了,广场上卖不动,占用了资金,冤,就脱手了。当然我没问亏没亏,像这样的倒手买卖不问也可想而知,我何苦再去撕结痂的伤疤呢,太不仁慈了,不地道了。就在这之前,小偷撬开了她家的防盗窗子,并盗走了她的手机、她丈夫裤袋里的几百元现金。她连报警的想法都没有,这事就算被“黑下”了。两口子,不怨也不恼,仿佛已经“神马都是浮云”了,生活让她淡定从容多了。不报案的事,在僻远乡村很多,能捂的都捂了,这是体谅警察的辛苦,也是为了少折腾自己吧。看起来是对小贼的放任,实则是对小偷的可怜。就这样的人家还偷,不是没长眼,就是没长心!消息传开,大院里人莫不破口大骂蝥贼。这小偷,要不就是穷得揭不开锅,顺着楼洞爬上去,万一摔死了怎么办?理智点的似在替贼想,这样的“被摔死”的小贼也不是一个两个,难道他们偏喜欢这样冒险、这样玩火,甘做亡命之徒不成?这样一想,倒也是很后怕的。
C楼道里黑洞洞的。声控灯用过几年之后一律不听话了。一个楼洞五层,门对门一对邻居,公用一盏楼灯。越往楼上,要过的楼道梯级越多。假若最顶上的一只灯坏了,那么两扇门的对邻必有一个先得自觉地买一只灯泡。先买了就买了,不便向未掏一分钱的对门去言说,以免落个表功之嫌,还遭腹诽,公用嘛。一盏灯泡毕竟要不了多少钱,劳神是劳神点,安装费点心思,气力,需得找门房,扛铝梯。上五楼的顶口,是个切切实实的粗活,铝梯虽是活动的,然而毕竟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确不方便。但自己为自己服务嘛,也兼顾了邻居,也就懒得计较。说服自己的方法很多,譬如,不妨这样想,一个人夜里喝酒回来,爬楼梯不慎,摔得鼻青脸肿不说,还摔折一条腿,在医院花掉几万元,找保险公司赔付,转昏了头未必就遂愿;又要给手术医生送红包,还落个终身残疾;还得在单位年终考核不合格时扣工资扣奖金,甚至耽误了早晚接送孩子,多不值呢?你说买个灯泡值,还是损失一大堆值!这家的老婆过去老是骂男人喝得醉醺醺的晚归,后来突然不骂了。人问其故,她老实坦言:曾看过一篇报道上写着,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家,为防贼防盗,每天给自己门外放一双42码的男人鞋。这个十分怯懦的行动感动了许多人——被报道的那个寡妇就每天这么战战兢兢度日。这哪里像人过的日子啊!听话的也明白了:这个女人,还算不糊涂。后来这家老婆对男人的骂声销声匿迹了。男人回家也比过去早多了,酒也渐渐被疏远了。
当然也有人家就是不缴看门护院的费,明知没理由,办法就是躲和拖。躲,就是不给你人影看;拖,就是催了也白搭,没态度,没言语,没行动,没效果,甚至效果更差,搅得院里老崔头疼,悔不该当初进来时没一家一户签个协议。六十家共居的小区,物业管理费几乎没收过一分。当然,这都是由推荐出来的一个七人管理委员会义务代劳的。老崔是委员长,麻烦都交给他终决。为小区安全起见,干脆请了个老头当门卫,每户年均出100元作看护报酬,兼算垃圾运送费。院内卫生清扫,楼梯楼道擦抹,甬道野草清除,还有人来人往监视,夜间开门放人,也是一摊子事,并不轻闲。可是,有户人家,主人就是连年拖欠,到年关就锁门走人,把责任推给远在北京做装潢的男人。男人偶尔进家也像贼一样,悄悄地来偷偷地走,像是打游击,生怕被义务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逮住了,但还是露出了尾巴。委员会的几个人进他家,堵门说理。那家女人放风,推托房子已准备转买给外地人,自己不想在此住了。弄得物业小组成员很为难,好不容易去封门捉鳖,说理就是油盐不进,打官司得不偿失;不打这个官司吧,又让看门老魏头三天两头喊着要走人,声音里带着要挟的味道。就是这样的老实人也禁不住“横”了,兔子急还咬人呢!这年头,若请个保安花费更大,保安若是自盗起来,也许更不安全。大家盘算着还是留住老魏头要紧,于是妥协,答应决不少老魏头分毫。可这边没给的费用又老悬着,颧骨很高的女人就住在我家楼下,他的老公在楼梯上见到我灰头土脸,就是为催费用的事,他的承诺被老婆推翻了,狼狈的神态好像阳痿。我可怜他又恶心他。这恶心并非因这一事引起,这一家子总不愿在卫生间里排泄,异味耀武扬威地往上冲,常弄得我家的窗户形同虚设。夏天闷得慌无法通风。冬天好多了,低温不再帮那一对儿女三口之家囤积的粪便臭气嚣张。
就在这家女人喊着欲搬家后的日子不久,冷不丁他家猛地又请来了师傅上楼顶通道安装天线接收器,就是那个微型锅状物,直弄得我家的人抱怨放乱了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水管子。这令我有些心烦。看来,为了逃避电视台收费,这家人是不打算装数字电视了,干脆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私下安装另外一套既便宜又隐蔽的设备。根本就不是要搬家的举动,不知在其他居户心里起什么反响?五十九户人家都对这一户摇头,甚至有人把怒气迁到她的一对儿女身上。“世上这么蛮不讲理的人,儿子讨媳妇,女儿嫁婆家,人家都会隔二十四条田埂,能找到好人家么。”话是这么说,理是这个理,大家都是从泥田里洗脚上岸的,说出来的话直不楞通的,也不避讳谁。可是,总有较上劲的,吃生米遇上嗑生稻的。这家的女人当家,总把垃圾随处丢,还是看门老魏过意不去,逢人便说,“真是要不便,把垃圾扔到我门口垃圾车里算了,还能叫你拿下来么?”这个“你”,没人愿意给她传话。她的反常行动,反而让老魏头更加头痛,甬道里,过路边,墙根下,偶有这么一袋,那么一袋,随手丢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袋,自然全是她家的,这给老魏头找来更多麻烦。按理,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过的日子也不算差,竟然让自己的垃圾也东躲西藏。受害者是老魏头,他还得每天捡,每天送,不捡不送就发臭,一发臭老魏头就觉得对不起人,拿了亏心钱,也给人家留下话柄子,坏了自己的口碑。老魏头气得眼珠子发黄脸泛青,又不肯丢下老脸去求她。无处发泄,就打牌。幸好有几个老太婆闲了无事,每天下午在他的门卫室里陪他玩牌,他才慢慢消了心头的气,否则一定堵得慌,说不定还堵出个病来!
毕竟,在这个大杂院,从不同地方聚拢的人,在这里有缘无缘地相见了。出入一个大门,发生过许许多多杂七杂八的事,痛快的,不痛快的,都数不清。小姜的饭碗弄丢了,小夫妻算是苦尽甘来,不给看护费的还是拖欠着,院子里的人们,日子还得照样往前过,像流水,像落花,各色的梦继续做着。活着的人,幸与不幸的人,当回事的,不当回事的,就各做各的,理由五花八门,人们评头论足,说话间,有气愤,有淡然,习惯了一次又一次将过往心头的垃圾抹掉,虽然又会沉积新的垃圾,似水流年的杂院,形形色色的乱象,将与人们的恩怨一起,让时光的尘埃一起卷走。每个时代都是一条滔滔奔腾的大河,顺流直下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那退潮的河床上的泥沙,或是那宽阔河面上漂零的零叶,寻找的是貌似明确的方向,沉淀的是善良者的恩泽。
责任编辑 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