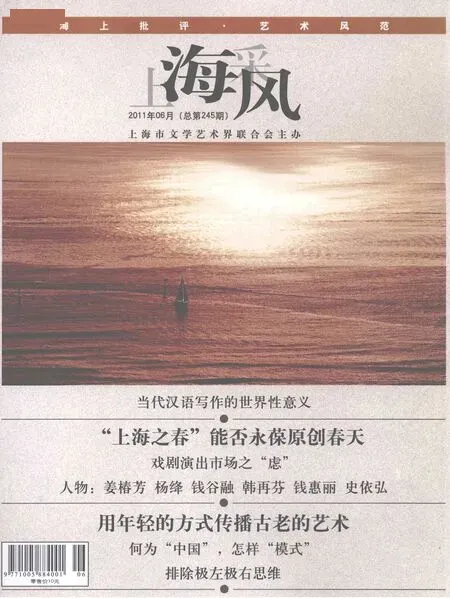报纸文化版的“消瘦”或“消失”
文/金 星
报纸文化版的“消瘦”或“消失”
文/金 星
一直很关注冯骥才,一是他因人高马大而鹤立鸡群,二是作为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常有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据报载,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于梅地亚两会中心举行的主题为“政协委员谈文化建设”的记者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有的媒体版面有过分娱乐化的倾向,甚至于只有娱乐版而没有文化版了。即使现有的文化版,大部分也都是政治效应的文化版,纯文化的信息特别少。“所以我希望媒体能够把文化版和娱乐版分开,给文化更大的空间,使文化跟大众有更多的联系”。而在记者会快要进入尾声时,冯骥才又特意提醒在座的记者给媒体的老总带回他的这个意见。笔者留心了一下,时至今日,各媒体的大大小小的老总,似乎也没有什么反馈的声音。这或许已在冯骥才的料想之中,也难怪他要经常性地愁眉深锁。
现在所谓的文化版,就传统的纸质媒体而言,就是指报纸的副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申报》的“自由谈”、《庸报》的“另外一页”以及《晨报》的“副镌”等,注重文以载道,都是相当有名的副刊,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也留下了很深远的影响。著名报人赵超构就曾说过:“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同为著名报人的金庸也深有体会地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对于报纸而言,新闻为攻,副刊为守。”很显然,副刊文化品位的高低也就决定了这张报纸本身的品位,事实上也影响了读者的品位,甚至多少显示着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文化素养、文化自觉程度及审美趣味。常说人有人品,其实一张报纸也理应自有其报格。1941年,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长后把丁玲调去主持文艺副刊,他见到丁玲的第一句话就是:“副刊决不是报屁股,决不是甜点心。”丁玲也非常赞同博古的这一看法,她后来回忆道:“他说每版都可以放文化稿件,如果有最好的文章,放在第一版头条也可以。”同样,创刊于1949年1月17日的《天津日报》为何至今独放异彩,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有了著名作家孙犁所主持并因他而传承下来的《文艺周刊》。孙犁曾在《我和文艺周刊》一文中说:“虽然是个地方报纸副刊,但要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并用这种风格去影响作者,影响文坛,招徕作品。”他还确立了文艺副刊必须与时代同步,高唱时代主旋律的现实主义风格。而如提及《大公报》,就总要说到曾在那里编过副刊的行家里手沈从文和萧乾。斯人已去,遗风犹在,现在的几张大报,如《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文汇报》的“笔会”副刊、《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等,以及一些地方性的报纸副刊,都各具特色,大有可观,也每每使人获益匪浅。
但也正如冯骥才所忧虑的那样,原来媒体的文化版和娱乐版是分开的,但现在是混在一起,甚至于慢慢地只有娱乐版而没有文化版了。也有人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副刊的“消瘦”或“消失”。在文化的名义下,媒体的娱乐版急剧增多,而且越来越品位低下,看来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一边是孤灯清影,茕茕孑立,一边是热闹非凡,几乎人人趋之若鹜。可能有人会振振有词,说娱乐也属文化。从广义来说,娱乐是可以包括在文化之内,但文化的主体与本质并非娱乐,而重在“文治教化”。虽然,娱乐与文化都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人化”的现象,但需要明确的是,娱乐只是人的一种需求,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与排解,更是一种单纯的“欢娱快乐”;而文化则显示人的一种追求,一种与无教化的愚昧和野蛮相揖别的“文治教化”的追求。文化的英文对应词——CULTURE,原指耕种与对树木禾苗的培养,后引申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这与我们所提倡的“文治教化”完全相通。媒体如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仅是一种短视,更是一种引领责任的缺失。相反,在事实上也可理解为一种退让,甚至是助长与合谋。
泰戈尔曾不无悲哀地预言,“弃绝精神是人类灵魂最深刻的表现”,这难道会最先在以宣传文化为己任的媒体身上得以生动地体现出来?想来可笑,但也由不得使人惶悚。还是龙应台说的较为具体,她认为有什么样的副刊,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新闻传媒是“社会的守望者”,既要贴近读者又不能盲目地迎合读者,随波逐流,而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社会责任感。靠暴力、色情、猎奇取悦读者,追求“星、腥、性”等庸俗化的内容,大肆渲染一些表面花哨引人,内容却低级无聊的东西,最终可能会带来始料不及的负效应,既无法真正留住读者,也有悖于“社会守望者”的道德与责任。自然,这样的“社会守望者”,首先还得守住自己,从自己所编所写的每一个字开始,如此,才算是骨格清奇非俗流。

金星 报纸副刊编辑,文化时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