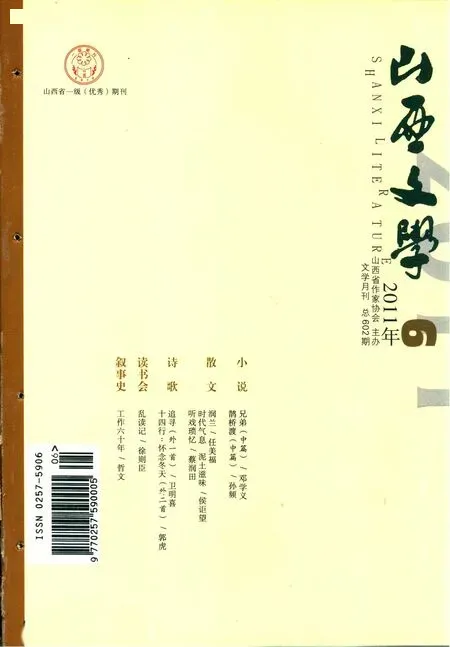工作六十年
哲 文
工作六十年
哲 文
1958年6月下旬,我从部队转业来到算是第二故乡的太原市。到市人事局报到,接待我的军转办干部征求我对分配单位的意见。由于我在早两年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认为是缘于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工作所致,渴望改变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当时,全国已掀起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序幕,各行各业单位都急需增加人员,我提出希望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军转办干部让我先休息两星期,在家等待分配。
未分配工作前,我住在二哥家。当时二哥在山西省公路局工作,但仍住在原来工作单位华北工程局的职工家属宿舍。是一座解放后新建的三层楼房,是该局科长以上干部的家属宿舍。二哥不是科长,却是业务骨干,又是解放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到特殊照顾,也住进了这座宿舍楼。每户室内面积约四十平方米,有两间住房和卫生间、厨房、阳台以及室内上下水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原市设施齐全的职工家属宿舍。八口之家(母亲、二哥二嫂、三个侄子、一个侄女,再加上我)居住,略显拥挤,但已经令人羡慕,全家人都很满足。度过八年军旅生涯,重新回到母亲和亲人身边,感到非常温暖和踏实。
两个星期后,我被分配到太原市重工业局。我向重工业局人事科长提出希望到该局所属古交钢铁厂当工人。他明确告诉我,按政策规定转业军官只能分配干部工作,不能当工人。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太原市工业、商业、农林水利等部门,都在筹建各类技术学校。我被分配到市重工业局新成立的太原钢铁机械学校任化学教员。学校设在太原市郊区阳曲镇市重工业局几年前新建的砖瓦厂。不知什么缘故,工厂建成后未投入生产,厂房一直闲置在一片杂草丛生约五十亩的土地上。学校校长由市重工业局一位民主人士副局长兼任。我是这所学校第五名报到的工作人员。之后,又陆续从下放干部中抽调二十余人,组成学校的教职工队伍。筹办阶段,一部分人员担任校舍修缮和物资准备工作,一部分人员担任招生工作,我在招生组。学校设置两个学制三年的中技(中专)班和四个学制二年的初技(技工)班。中技班招初中毕业生,初技班招小学毕业生。学校在全省范围招生,计划招二百四十名学生,约五百人报考。考生中只有少数太原市的应届初中毕业和小学毕业生,大多数是省内各县的农村子弟。考生的年龄差距很大,报考中技班年龄最大的二十六岁,比我还大一岁,报考初技班年龄最小的十三岁。9月1日开学,录取生报到时看到学校的条件很差,大失所望,大约有十分之一放弃了就读机会。由于学校人力、物力都不具备办学条件,当时正值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市重工业局决定,全校二百余名师生员工,除年老体弱人员外,全部拉到古交区冀家沟公社两个生产大队参加大炼钢铁劳动。兼任校长年龄已五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不能带队,市委组织部派了一名年富力强的党员干部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主持学校党政工作。全校当时只有党支书一名共产党员,不够成立党支部的条件。全校约四十余名共青团员,建立团支部。可能因为我是转业军人,又是有八年团龄的老团员,重工业局指定我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除负责全面工作外,在一个生产大队带领学生劳动,我在另一个生产大队带领学生劳动。
全民大炼钢铁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要求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铁生产任务,并提出在较短时间内赶英超美的奋斗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许多机关学校在院内建起了土高炉,称之为土法上马。古交区盛产铁矿和煤炭,几乎所有的生产大队都建起土炉炼铁。所谓的土炉炼铁,就是挖一个约60至70立方米的大坑,底层为木材,第二层大块煤炭,第三层排列无数水泥圆筒,筒内装满铁矿石和从民间收来的旧铁器皿。点火后用鼓风机吹风助燃,并不断往坑内加煤炭,经过二十四小时冶炼,出炉产品,既非铁也非矿,是铁矿石和旧铁器凝结的圪节。每周按上级下达的产铁计划指标,如数填报产量。每周有一天高产日,就按计划指标的一倍半填报。上级只要报表,不验收产品。生产出来的圪节,就随便堆放在野地里。据说后来用作修路的基石。大炼钢铁高潮期间,也正是农业秋收时期,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部分投入大炼钢铁,丢下农业生产,造成了丰产不丰收。为了解决燃料问题,砍伐了大片山林。这种状况,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都心知肚明,一级哄骗一级。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的成果,成为“皇帝的新衣”。
在冀家沟公社大炼钢铁三个多月,随着全国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的降温,我们学校二百余名师生员工于12月中旬返回学校。由于三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大家都十分疲劳。加之,学校还未具备开学上课的必要条件,市重工业局决定提前放寒假,只留少数员工继续为开学上课做准备工作。我是留下参与筹建工作的一员,整个寒假只在春节期间休息了十天。1959年2月正式开学上课。市重工业局副局长不再兼任校长,太原市市委组织部派来的支部书记也回到市委组织部。重工业局分配来了一名专职校长。学校教员数量不足,每个教员每周教课二十余节,职员更少,除校长外,只有一名管总务的工作人员,一名会计兼出纳,一名校医。学校不设教务处等职能科室,也不划分教研组。学校领导分配我教两个中技班的化学课并兼任班主任,此外还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承办教务处和办公室的具体工作,算是身兼五职。每天实际工作量在十二小时以上,忙得不亦乐乎。1959年4月,全市评选劳动模范,当年称跃进模范,市总工会分配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团市委评选优秀团员和出席太原市第八届团员代表大会代表。经过学校全体教职工和团支部大会的评选,并经学校领导批准,我被评选为全市跃进模范和优秀团员及出席市团代会的代表。5月1日劳动节那天,市政府在新建路礼堂召开全市劳模大会,市委书记李琦等领导向一一走上主席台的劳模授“跃进模范”奖章。
1959年,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得到了荣誉,失去了爱情。1958年我转业到太原后,与在大同市工作的女朋友,也是我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同班同学,约定在当年国庆节期间结婚。因为带领学生在古交山区参加大炼钢铁,无法抽身请假,商定推迟婚期,改在1959年春节期间。1958年国庆节后,我随学校党支部书记赴北京参观全国教育改革展览。参观后我奉命到张家口市调查我们学校一位教员的情况。张家口市离大同市很近,我请了两天假去看望女友,还在北京买了两床缎子被面。在大同市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并到市郊云冈石窟游览。我们商量就在大同市办理结婚手续,因为我没有带结婚登记所需相关证明介绍信,只得作罢。回太原不久,因为一封信引起的以讹传讹,造成了误会,她的母亲很不满意,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她提出了分手,并把两床缎子被面和我曾寄给她的多张照片退回。其实,我们分手并非单纯误会所致。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只有同学之谊,而无爱恋之情。自1948年秋我们初中毕业至1958年春十年期间没有见过面。1957年,不知她从哪里知道我的通讯地址,给我写来一封信,通了几次信后,就确定恋爱关系,商定了婚姻事宜。之所以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因为我们同学多年,算得上青梅竹马,也算得上门当户对,彼此了解且有好感。1958年春夏之交,她到北京出差,约我去会晤,我们学校驻地辽宁省锦西县离北京很近,我请了两天假到北京。这是我们初中毕业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恋爱非常理智,缺乏激情,按现在的时髦用语,没有来电。两次相聚连手都没有牵过。俗话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既无执子之手,当然不会与子偕老。我一生中,一次婚约,两次恋情,都无果而终,有缘无分。
1958年8月,太原市在大跃进期间,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类中专技校,因为不具备办学条件,进行了大调整。部分学校撤销,部分学校合并。太原钢铁机械学校,一分为二。一个中专班两个技工班与太原市轻工局办的太原轻工业学校,合并到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二·二二技校”。改名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归属太原市教育局领导。另一个中专班两个技工班,迁到太原市古交工矿区,划归太原市古交钢铁厂领导,成为厂办学校。教职工也一分为二,年龄较大者和女教师分配到设在市区的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年轻的教职工,由我带队分配到太原市古交钢铁厂技工学校。钢铁厂派一名老干部任学校负责人,我仍然以教师身份协助他工作。学校既无正式建筑的教职工办公室,也无学生和教职工宿舍,临时搭建十几顶帐篷,权当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在开学典礼上,工厂领导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学习延安精神,克服困难,艰苦奋斗。教职工吸取反右派运动的教训,对学校现状不做任何评论。学生情绪很不稳定,讲怪话发牢骚。说什么二十年前延安办窑洞学校,二十年后工厂办帐篷学校,是一大进步。还说中央领导号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上”,我们学校是没有条件创造不了条件也要上。家住太原市的几名学生自动退学。学校在一无校舍,二无必要的教学设施,三无优质教师的极度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半年,实在撑不下去,经太原市政府批准,撤销了古交钢铁厂技校,全校师生员工也合并到太原工业专科学校。
1960年2月,合并到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后,我被分配在理化教研组任化学教员,教两个中专班的化学课。当时,从工厂调来一批干部和老工人,担任专职的红旗班主任,教师不再兼任班主任。我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在当时太原各类学校中,是办学条件最好的,各科教师齐全,大学毕业的教师占到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有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有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和实习基地。已婚的教职工每人分到一套一间半房的家属宿舍,单身教职工两人合住一间集体宿舍,有专门的教职工食堂。那一年没有开展任何政治运动,教学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合并两个月后,学校改选校团委和各个团支部委员,我被选为校团委委员兼教师团支部书记,当然都是定额选举。
1960年6月,经同事介绍,我与现在的老伴结婚。当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改称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后果已经显现。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物资极度匮乏,老百姓的口粮和一切生活用品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原打算结婚时举行一个茶话会,因为缺乏糖果和香烟招待客人,我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到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领回了结婚证,在一家小饭店共聚晚餐,凭粮票买了两碗馄饨四个包子。晚上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我们的洞房,是妻子单位分配的在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七点五平方米的房间。套用现在的时髦用语,就是蜗居。因为房间太小,只能摆放一张单人床加半块床板,一张二屉桌,一个独凳,一个铁炉子。两口箱子放置在床下,名副其实的四徒空壁。唯一的奢侈品,是我用两个多月工资买的一台美多牌收音机。收到的唯一礼品,是教研组全体同事签名题写恭贺结婚志喜的粉红色虎皮纸横幅。学校离市区有二十余里路程,距一路公交车站也有两里多路程,而且公交车车距四十五分钟,回家很不方便,婚后我平时住在学校集体宿舍,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大杂院很小,原来住户搭建的厨房已占满了院子,我们想搭建一个小厨房已无空地,春夏秋季节只能把铁炉子放在房门外。如遇下雨天,就用一个大铁盆反扣在上面。平日我和妻子都在各自机关食堂吃饭。妻子每天下班时从机关茶炉房打两暖瓶开水回家,备她一个人饮水和洗漱。星期日点燃铁炉,烧洗衣水和做简单的饭食,也就是熬一锅小米稀饭,炒一个青菜或搭配一个酱菜。当时每人每月供应三两猪肉,偶尔也炒一个肉菜。馒头或窝窝头,各自从机关食堂买现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吃饭成为大问题,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体重从1958年的一百二十斤,下降到九十四斤。在学校食堂吃饭,主食凭粮票随便买多少不受限制,但每人只限买一份菜。为了以菜代粮填饱肚子,包括我在内的青年教职员工,吃完饭后留在食堂不走,等待大多数人吃完饭后,食堂剩下没有卖完的菜,每人可以再买一份。我记得一个星期六吃午饭时,特意多买了五个窝窝头,准备带回家当做星期日的主食。在公交车站等车,公交车迟迟不来,看到手袋里的窝头,控制不住食欲,寅吃卯粮,把带回家的窝窝头吃了一个。之后,仍然馋得流口水,就又吃了一个。就这样在等车的一个小时内,连续吃了五个共计一斤粮的冷窝头。第二天星期日,只好分食妻子从食堂买回来的主食。为了填饱肚子,我曾用八成新的棉军衣,与近郊区农民换了五十斤山药蛋。有一次八岁的外甥从西山矿区到市区来看望我,正赶上吃午饭,好像是吃包皮面(外层白面,内层高粱面)。外甥端起饭碗后问我:四舅,管不管吃饱?我虽然笑着说,管饱管饱,你尽管吃,心里却涌上一阵苦涩和酸楚。那些年,在太原大街上行走,几乎看不见一个胖子。在澡塘洗澡,大家赤裸相见,看得更清楚,多数人都骨瘦如柴。偶尔看到一两个胖子,问起他们的职业,不是卖肉的就是炊事员。验证了一句俗话,“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中专学校的学生每月供应三十多斤粮票,比教职员多十几斤,但仍不能保障身体健康的需要。为了保持学生的体力,学校停止了晚自习和早操,体育课改为自由活动。

2005年,与昔日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合影,前左六为作者
当时,对我来说,穿衣不成问题。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和薪金制以后,军官在节假日可以穿便装。上世纪五十年代,市场上没有卖衣服的商店,部队军官几乎人人都在缝纫店量身定做便装。我每月薪金七十二元,又是单身,没有家庭负担,一次就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中山装,购买了几件质地较好的衬衣和时尚的T恤。加上原来在部队的军装,共十余套衣服,足够我穿十多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穿西装被视为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我把西装上衣改为学生装。直到市场上有了不要布票的涤卡和的确良以后,我才添置衣服。
结婚后,住房问题一直困扰了我近二十年。第一次住房是坐东朝西的东房,又没有可通风的后窗,夏天烈日直晒一下午,房间犹如蒸笼。每天晚饭后,我和妻子在马路边坐到深夜才回房就寝。有一天,妻子的二姐从农村老家来太原看望我们,住在我家。找了几家旅馆都没空房间,我只好在火车站的长条凳子上睡了一夜,一只美国制造派克钢笔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岳母来伺候月子,因为房间小,我临时借居妻子单位的集体宿舍。妻子五十六天产假期满,岳母回去照料自家的一大摊子事情。妻子上班无暇照料孩子,雇人又无住处,只得把孩子送到妻子老家农村,让一个生孩子后婴儿死亡的农妇奶养,每月奶养费十七元。当时农村新生儿死亡率高,在农村寻找奶妈并不困难。大孩子的奶妈患结核病,传染给孩子,两岁时患结核性脑膜炎,后医治无效夭折。从结婚起到1998年,我先后换了七次住房,每次换房都有所改善。我现在有两套设施齐全的房子,子女结婚后也都购置了新房。从我七次换房,见证了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犹如一场噩梦。老百姓的日子尽管过得很艰难清苦,但是,当时社会人群贫富悬殊不大,老百姓吃不饱,各级官员也吃不饱,官员都比较廉洁,少有腐败现象。老百姓只嫉恨老天爷,对党和政府没有抱怨,自觉自愿与国家共克时艰,坚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1961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我年届二十八岁,当了整整十一年青年团员。按团章规定,自动退团,免去校团委委员和教师团支部书记职务。同年腊月初六,我的长子出生。是日是阿尔巴尼亚国庆日。当时,中阿关系正处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美好时期。为庆祝小生命诞生,给孩子起乳名“阿庆”。那个年代,中国人给孩子起名都寓含政治意义。起名解放、建国、国庆、抗美、援朝、卫东的孩子比比皆是。正当我和妻子沉浸于初为人父母的欢乐之际,太原市工业专科学校奉命撤销。大、中专学生分配到市属国营或集体所有制中小企业。技工班学生分配到市商业局蔬菜公司、服务公司、公交公司。少数学生自愿回家务农或自谋职业。学校教职工中,有专业技术教专业课的教师分配到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工矿企业。教基础文化课的教师,少数分配到市属中学任教,多数分配到各区所属小学任教。我被分配到南城区亲贤小学。我参加工作的十年间,已六次调动工作。从兵团级单位调军级单位再到师级单位,转业后分配到县处级技术学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却是人往低处走。但每次调动我都愉快服从,认为是正常的工作需要。这次分配到小学,我感到十分委屈。当时,小学教员是人们最看不起的职业,男教师找对象都很困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不称职或有一般历史问题以及犯错误但不够判刑的人员,都打发到小学就职。我为此找到学校分管人事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汇报思想,要求分配到中学任教。我的理由是,我教过八年中学和中专化学课,都称职胜任,受到学生的欢迎,1959年还被评为太原市跃进模范和优秀团员。学校党委副书记说话很直爽,没有冠冕堂皇讲大道理,直截了当告诉我分配到小学的原因:第一,没有大专以上学历;第二,家庭出身不好,又是“中右分子”。他还说,现在到处都在精简裁员,你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潜台词是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听了他的谈话,我才知道自己是“中右分子”,是打入另册控制使用的干部。这次下放到小学任教,是变相的贬罚。我再无话可说。
亲贤小学所在地亲贤村,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全村一千多人。学校有六个班级,每班不足三十名学生,都是本村农民子弟。学校包括校长在内共有七名教师,其中含两名民办教师。
我是学校中年龄最大,工资最高,资历最深的中专下放教师。同事们知道我的经历后,对我十分同情和尊重。因为我在中学和中专学校都是教化学课,校长分配我代五、六年级两个班的自然课。工作很轻松,只是生活上不方便。学校没有食堂和宿舍,只有一个烧开水和供教师热饭的铁炉。学校离我家有十余里路程,没有公交车。我买了一辆除车铃不响其他部件全响的二手自行车,每天带上中午饭,早出晚归。半年后,南城区教育局在离我家很近的南海街新建一所小学,从区属各小学抽调教师。承蒙组织照顾,我被调到这所新成立的小学,仍教自然课。生活不方便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市区儿童比农村儿童调皮,上课时做小动作和说话现象很严重,课堂纪律不好。我缺乏管理儿童的经验,过不了课堂纪律关。学校调整我改任体育教师。小学体育课主要是游戏。男生打球、赛跑、跳高、跳远;女生踢毽子、跳皮筋。大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我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出事故。在任小学教师这一年中,由于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寒冬季节日复一日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我突发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红肿疼痛,不能行走。在南城区医院治疗近一个月,病情有所好转,出院后,走路仍然很困难,妻子刚生孩子,无力看护我,只好在二哥家住了一个月,由年逾古稀的母亲照料我饮食起居。病愈后回学校上班。校长告诉我只要我找到接收单位,区教育局同意调出。我去了几家化工厂,毛遂自荐,都被婉言谢绝。我沮丧到了极点。在走投无路时,想起了在太原市卫生大队任大队长的老战友郭满海。他是抗日战争前参军的老同志,放羊娃出身,从部队看护兵逐步成长晋升为助理军医、军医、团卫生队长。1953年我们同在志愿军卫生部工作。他在干部处,我在医政处。1954年又先后调到解放军八十七速成中学,他是学员,我是文化教员。1958年则同时转业来太原。天无绝人之路,找他帮忙调动工作。他满口答应说,只要你不嫌卫生大队名声不好,随时都可以来。卫生大队及所属各队的干部多数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工人中除少数郊区农民出身外,大多数都是劳改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其中不乏阎锡山军队中级军官,级别最高的有一位中将、一位少将,还有太原市沦陷时期汪伪政权市政府市长。职工成分很复杂。当时,社会上人们认为卫生大队是藏污纳垢的单位,也有人调侃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我当时只想快些离开小学,已顾不了许多。何况我的出身也不好,俗话说乌鸦不嫌猪黑。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办好了一应手续。
1963年春节后,正式到太原市卫生大队上班。卫生大队下辖三个卫生队和一个修理厂,大队部设业务股、财务股、人事股和行政兼党总支部办公室,共十二名干部。我分配在业务股。全股三人,一名股长、一名股员和一名以工代干的卫生检查员。我虽然只有高中二年级肄业学历,却是大队部干部中学历最高的小知识分子,又有在大机关军委卫生部和志愿军卫生部工作两年的锻炼,很快就熟悉了业务。两个月后,随市卫生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和卫生大队队长到北京、天津参观学习环境卫生管理经验,并由我撰写参观取经报告。处长看了我写的参观报告后,大加赞赏,甚至怀疑是我请他人代笔撰写的。随后,我根据京津两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经验,结合太原市实际情况,起草了太原市环境卫生工作各项规章制度。我的业务和文字写作能力以及工作表现,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大队的一切文稿都由我起草或修改。1963年底,我被评为卫生大队的先进工作者。卫生大队及所属各队干部,每周都要跟班劳动一天。当时,没有清扫清运机械,清扫街道、清运垃圾、掏运粪便和收运生活污水(许多街道没有下水管道)都是手工操作。我过去的一些学生和熟人,看见我跟班劳动清扫街道,以为我犯了错误,被贬为环卫工人。为了不使我尴尬,假装没有看见,不打招呼。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实行多年的干部参加跟班劳动制度自动取消。经过三年多的跟班劳动,我干过清扫大街、清运垃圾、掏运粪便等各项劳动,成为熟练的环卫工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市掀起了红卫兵撵人的高潮,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被注销城市户口,由红卫兵押送原籍。太原市离北京市较近,受到首都撵人行动的影响,各单位在领导的授意下,由红卫兵出面,也纷纷把所谓有问题的职工及其配偶和子女遣送回原籍。当时太原撵人的做法,称为“一批(斗)二抄(家)三滚蛋(回原籍)”。红卫兵在被撵对象家门口,张贴“勒令什么什么分子某某某,限几日内滚回老家去”告示,然后,由单位出具介绍信,到被撵对象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迁出户口手续,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卫生大队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较多,按百分比计算,是全市撵人最多的单位。卫生二队有一名出生于赤贫家庭的环卫工人,因父母无力养活,卖给本村一户地主当儿子,成为地主的养子,也被撵回原籍。在太原市撵人行动高潮期间,我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十分幸运的是,我没有被遣送,躲过一劫,又一次在政治运动中平安过关。究其原因,第一,卫生大队队长是我的老战友,得到他的保护;第二,我是卫生大队所谓的“笔杆子”,还有使用价值。太原市各单位撵回原籍的职工,在撵走后的三个月内,又都回到原单位上班工作。
1972年,我的老战友,太原市卫生大队队长郭满海调到太原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爱卫办)任主任,在他的要求和斡旋下,我也同时调入爱卫办任科员。太原市爱卫办共有五名工作人员,主要工作任务,在城镇每年开展两次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突击卫生运动,在农村开展以“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良饮水、厕所、畜圈、炉灶、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市爱卫办负责制定下达工作计划和组织检查落实情况。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各县、区爱卫办负责。我的具体工作,起草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以及召开动员大会市领导讲话稿。工作很轻松,我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逍遥派,优哉游哉,心情愉快。加之,经常深入县区和大型工矿企业检查卫生,受到盛宴款待,体重增加了十多斤。
1974年,太原市卫生大队工会主席孟庆林调到太原市妇幼保健所任党支部书记。孟庆林、郭满海和我,都是部队转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属一派群众组织,私交甚笃。孟庆林希望我去市妇幼保健所任秘书。经过孟、郭和我三人协商,郭满海同意我去市妇幼保健所工作,但必须兼顾市爱卫办写材料的工作。市妇幼保健所除党支部书记、传达室门卫兼烧锅炉的工人和我三名男同志,其余二十多人都是女性医务工作者。市妇幼保健所是一个宣传预防妇女、儿童疾病知识,开展妇女病和儿童健康检查及普查普治的纯业务事业单位。我的工作任务,在支部书记和所长领导下,做行政事务工作,撰写普及预防妇女病、儿童常见病的宣传材料和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任务很轻松,平均每天不足两个小时工作量。
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撤销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卫生办公室,恢复太原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建制。卫生办公室主任和其他“支左”解放军调回山西省军区卫生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即靠边站的原市卫生局局长张培根恢复工作,重建市卫生局领导班子和调配各职能科室干部。市妇幼保健所党支部书记孟庆林调任市卫生局政治处组织人事科长,我调任市卫生局办公室科员。仍然担任写材料工作,起草全局性的文稿和审核各科室起草的文稿,由局领导签发。也常随局领导到各县区卫生局和市辖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现在称调研)。“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处于半瘫痪状态,各项医疗卫生工作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全市卫生事业停滞不前。为了拨乱反正,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序开展,重新建章立制的工作很紧迫很繁重。加上全市性的各项卫生工作会议也很多。需要起草的材料都由我一人承担,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工作。虽然很忙很累,但心情很愉快,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当时,我已年过不惑,工作二十多年,仍然是一名普通科员,不是带“长”的干部,局领导对外介绍我的时候,很少明确介绍我的职务,而是以调侃奉承的口气介绍我是卫生局的“笔杆子”。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文字写作能力有限,只不过是“塘里无鱼虾子贵”而已。当时流行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充其量我算是个会抄的“笔杆子”。“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各级单位的工作总结或领导人讲话稿,整体框架结构都是下级抄袭上级,县抄市,市抄省,省抄中央。文稿内容要求突出政治,穿靴戴帽;成绩要讲够,讲得满满的;经验要讲透,上升到理论高度;缺点和存在问题,点到为止,强调客观原因。文风不正,假大空套话连篇。文稿形式,用词遣字,一般都是炮制一个响亮的大标题和一连串对仗工整的二级标题,多用一些排比句。每次拟草的公文稿交领导审稿时,领导未看之前,首先问其中的提法有无出处。我回答是出自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和中央文件,紧跟中央的部署。领导说,这样就好,千万不要独出心裁。
1976年7月,河北省唐山市及周边县区发生7.8级大地震。根据山西省卫生厅的统一安排,太原市卫生局派出二十余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救护队,由市卫生局副局长程国才带队,于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赶赴唐山市滦南县参加医疗救护工作。我随医疗队做行政事务和联络工作。目睹大地震后的惨烈场面,心灵震撼终生难忘。当时,中国正值特殊年代,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通信不畅,交通阻隔,新闻封闭,七十二小时黄金抢救时间延误,全国人民又处于贫穷状况,无力支援灾区人民,国家强调自力更生,谢绝国际援助等诸多原因,抢救力度和灾后重建速度可想而知。试想,如果能像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党中央、国务院在最短时间,做出强有力的决策,举全国之力,从中央最高领导到十万精兵、无数支援者、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奔赴一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创造出一个个生命奇迹,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就会大大减少。
1977年6月,在粉碎“四人帮”半年后,我被提拔为太原市卫生局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局领导找我谈话表示,早就应该提拔了。对于这次升迁,我没有丝毫喜悦和激动。我当了二十多年科员和教员,已习惯处于被领导地位做一些具体工作。实际上担任副主任后,我的工作和工资、福利待遇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多了些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开始进行整顿。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开展城乡卫生清洁运动。山东省城乡清洁运动成绩突出。山西省组织以省卫生厅长李学敏为总团长,全省各地市卫生局长为分团长的十一个分团,共计近百人的超大型参观团赴山东学习取经。先后参观了青岛、烟台、潍坊、黄县等市县清洁卫生工作,顺便游览了当地旅游胜地。我任太原市分团秘书,在参观结束的第二天,总团召开参观总结会议,由各分团长汇报参观取经心得。总结会议前一天,我把起草好的汇报发言稿,交太原市分团长、市卫生局长张培根审稿。他看了之后,说我起草的发言稿没有突出政治,单纯业务观点,就事论事,没有彰显山东省工农业发展的大好形势。要我重新修改。我提出个人意见,认为参观爱国卫生运动成就汇报材料,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报告,主要突出山东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成绩和成功经验,并表示自己修改不好。局长听了我的意见,很不高兴。说你不修改,我自己写。局长是1937年参军的老干部,转业时是副师级干部,完全有能力写这样的汇报发言稿,当晚他连夜写了发言稿。我也连夜修改原稿。第二天清晨,我把修改并誊抄后发言稿交给他。他在总结会议上的汇报发言,采用了我写的发言稿。这件事我冲撞了局长。1979年全国调整职工工资,调整比例为职工总数百分之四十五。按照我的资历和工作表现,本该从行政二十级调升为十九级。但是,我没获调升。后来,一位副局长私下告诉我,局长认为我太骄傲,要杀杀我的傲气。通过这次调资,我体会到自己历练不够,胸无城府。翌年,第二次调工资,调资比例为百分之二,全局只有二人,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调升为十九级。后来,第三次调工资,调资比例仍然为百分之四十五,我再次调升为十八级。
1983年春节期间,在我离乡三十三年之后,第一次携女儿回乡旅游。因为我和兄姐都在解放初期离乡北上参加工作,家乡已无任何亲人,回乡只能算是一次旅游,而不是探亲。当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行驶到吉首市郊区大田湾时,骤然产生“少小离乡老大回”、“近乡情更怯”的激动和感慨,不禁热泪盈眶。到吉首市后下榻表弟张昌俍家。第二天,我和女儿在表弟的陪同下,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走遍了吉首市主城区大街小巷。主城区的街巷和民居比之解放前的所里镇变化不大。我家驻地厂坪街,基本上保持原貌。我家的旧居火砖大屋已成为湘西自治州医院职工家属宿舍,外观没有变化。听表弟说,大屋内共住十余户职工,屋内格局变化较大,大房间分隔成小房间,一层走廊分隔成十余家的厨房。为避“胡汉三回来了”之嫌,我和女儿没有走进大门,只在门外驻足几分钟。吉首市老一辈亲戚都已辞世,同辈表亲在我离开所里镇时,他们都还在幼年,彼此已无印象。在吉首市主城区和乾州镇逗留一星期,看望了几家亲戚和儿时玩伴及唯一健在的老一辈街坊邻里周兴友大叔和大婶。到乾州镇参观了母校湘西民族中学(原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学),看望了原十三中学校长、世兄钟醒钟先生、数学老师吴鼎新先生、地理老师向达先生。这几位老先生都已年近古稀,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故乡虽无亲人,但故乡情结挥之不去。近三十年来,我七次回乡旅游,重温旧梦。
1983年,国家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改革,超过六十岁的领导干部原则上都要离退休,起用有文化的中青年干部。1984年,太原市爱卫办主任、我的老战友郭满海离休,我“二进宫”又一次调到太原市爱卫办工作。第一次是科员,这一次升任副主任(副处级)。市爱卫办主任由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太原市委主委秦国栋兼任,另一位党员副主任主持工作。爱卫办的编制,由七十年代7名增加为12名。新配备一辆面包车。
1985年7月,我向市爱卫办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0月,经中共太原市委直属机关党委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却多年夙愿。
1986年,中央爱卫会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随后,山西省人民政府批转山西省爱卫会文件,号召全省人民积极投入以提高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为宗旨,以清洁、整齐、美观为目标,以净化、硬化、绿化、美化、亮化为内容的创建卫生城市和卫生农村活动。全省各级政府视评卫生城市为政绩,加强领导,加大投入,深入、持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省城乡卫生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87年4月,山西省爱卫办组织全省创建卫生城市工作检查、评比活动。太原市爱卫办和雁北地区爱卫办联合组成检查团第一分团,省爱卫办指定我和雁北地区爱卫办主任为正副团长,对长治市和晋城市所辖市区和县城进行为时一个月的大检查。长治市和晋城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接待检查团规格之高,服务之周到,令我惊讶不已,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检查团下榻的宾馆,是当地最好的宾馆(当时还没有划分等级),每名团员住单人间,副团长住两间房套间,我作为团长被安排住所谓的总统套间(实际是专为省级领导准备的)。每间房内都摆有水果、饮料、香烟。每日三餐尤其是午、晚餐,菜肴之丰,品质之佳,是我们这些普通干部从未见过,更未吃过的大餐。检查团检查城市卫生时乘坐的车队,由警车开道。每检查完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时,由已检查过的县政府分管副县长陪同乘车到两县交界处,下一个县的分管副县长已在那里迎候。在两市检查时,两市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陪同检查一天,分管副市长和市委宣传部长全程陪同。这次检查卫生与1972年太原市卫生检查团到大同市检查卫生时所受接待情况天差地别。当时,除检查团长住单人间外,男女团员分别住两个大房间,每餐都是普通便饭,并且向检查团收取粮票。时隔十二年的两次检查对比,说明了两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初显了超规格公务接待和公款吃喝的腐败苗头。
1987年12月,太原市荣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太原市爱卫办为褒奖市辖各县、区在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中的贡献,以学习全国著名国家卫生城市福建省三明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为名,组织各县、区爱卫办主任赴三明市参观取经。顺路到广州市、珠海市、深圳市、厦门市参观旅游。参观厦门市后,参观团解散,自由行动,各自或结伴返回太原。我从厦门到江西南昌市旅游两天,转车到九江,看望在某军工企业职工医院任院长的老战友,他陪同我乘他的专车到庐山游览。之后,我乘船到湖北黄石市,看望五舅父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我儿时的玩伴和初中同班同学杨秀松。在黄石玩了三天,由表妹陪同,乘船到武汉市游览了两天,探望了在汉口工作的表姐和在汉阳工作的高中同班同学瞿直愚。这次旅游为期一个月,参观游览了九个城市,报销差旅费近4000元。这是一次典型的公款旅游。

1987年,在长治检查创建卫生城市工作,左五为作者
1988年5月,我调到太原市结核病医院任行政副院长和院党委委员。这所医院是山西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医疗技术水平最高、建院时间最早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我分管财务科、总务科、膳食科、保卫科和党委宣传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轻松的活儿,只动嘴不动手。日常事务有各科科长具体抓,重大工作和重要决策,有院长和院党委书记负责。我每天上午上班后,到全院各处巡视检查一遍,再到我分管的科室询问有无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批签支出单据。每天上下班和外出工作有专车接送,每星期总有几次接待上级部门和驻地有关单位检查工作人员,陪吃陪喝。在医院工作一年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发福,“将军肚”凸起,体重骤升二十多斤,出现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症状。
1989年冬,得悉大哥重病住院治疗,我请假回沅陵看望,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沅陵冬季气候阴冷潮湿,室内没有取暖设备。我在北方生活了几十年,已不适应湘西的气候。到沅陵二十天后,我又一次突患风湿热(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也住进了大哥所住的医院,与他同住一间病房。几十年来,兄弟俩有过几次聚晤,但都来去匆匆。这次难兄难弟同住一间病房,是一次难得的机缘。有了充裕的时间聊天,说到一些有趣处,都不禁开怀大笑,忘记了疼痛,起到了精神疗法的作用。在沅陵度过1990年春节后,大哥的病情有所好转,我的病也已初愈,假期已到,日夜兼程回太原。由于旅途中受了风寒和劳累,旧病复发,住进太原市中心医院治疗。按照我的职务和级别,只能住普通病房。市中心医院唐绪元院长是老熟人,高干病房的主管医师原在市结核病院,经我介绍和疏通,调到市中心医院,他们二位特意照顾我住进高干病房。在我住院期间,为给年轻干部腾位子,我改任调研员。没有具体工作牵挂,高干病房的医疗和生活条件很好,我乘此机会彻底治愈所患各种疾病,在医院泡了四个月病号。
1991年初,我被借调到太原市卫生局,编撰《太原市志·卫生篇》。经过两年时间搜集资料和撰写,完成初稿并报送太原市地方志办公室。1993年12月,我年逾六旬,办了退休手续。退休证上注明,革命工作年限43年,退休金每月265元。1994年1月,接受市卫生局返聘,组织编撰《太原卫生志》,由我担任常务副主编和总纂,每月劳务费200元。在编撰《太原卫生志》期间,受聘兼任《山西通志·卫生篇》特约撰稿人,撰写其中“爱国卫生运动”篇章。《太原卫生志》出版后,受聘于太原市爱卫办。这是我第三次到市爱卫办工作。前两次是正式工作人员,第三次则是打工人员。主要任务,编撰《太原市爱国卫生运动史略》,兼负公文核稿工作,每月劳务费300元。2000年夏,太原市爱卫办主任康树芬调任太原市妇联主任。邀我去市妇联工作,从事公文稿件审核。每日工作半天,每月劳务费400元。由于对妇联工作不熟悉,一年后,以身体欠佳为由,请辞了这个工作。2002年3月,受聘于山西省卫生厅,担任《山西卫生年鉴》责任编辑。也是每日工作半天。每月劳务费1000元。从2002年3月至今,已在省卫生厅打工9年,编撰《山西卫生年鉴》(2002-2010)共9卷。期间,参与《山西省卫生厅简史》和《山西省卫生援外三十五周年》编辑工作,担任文字编辑。2009年,山西省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批转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制定的山西省第二轮修志规划,省卫生厅承修《山西省志·医疗卫生志》,要求2013年底完成初稿。省卫生厅于2010年6月,组成四人编撰班子,指定我具体负责编务统筹,担任总纂,每月劳务费增至3000元。老伴和子女都认为我年事已高,退休后又持续工作十七年,应该歇下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宿舍院里,有人讽刺我“要钱不要命”,有人调侃我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莞尔一笑,说自己是废物利用。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也非为钱打工。只是觉得退休后生活太单调,有点事情干,充实一些。退休十七年来,一直参与山西省和太原市卫生史志编修工作。编修史志已成为我晚年的事业,有一种使命感,欲罢不能。编修史志,有机会赴各地收集修志资料,参加在全国各地举办的修志培训班、研讨会。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首府和名山大川旅游胜地都曾留下我的足迹,满足了我对旅游的愿望,扩大了眼界,愉悦了心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除了极“左”思想的禁锢,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甩掉了出身不好的紧箍咒,得以舒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现在全家八口人中六个成年人,有五人是中共党员,有海归博士,有处级干部,有会计师、政工师,外孙在国外留学,孙女在市里最好的中学读书,全家生活稳定,衣食无虞。我现在最大的愿望,老天爷假以时日,在我有生之年,完成《山西省志·医疗卫生志》总纂任务。届时,我就算工作了六十多年。哈,这个记录也算不错。
责任编辑/陈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