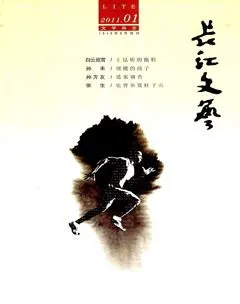冬天降临村庄
干草垛
当家中的老黄牛能卧在牛棚里悠闲地甩着尾巴时,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就来临了。冬天,人们收割完庄稼,把一粒粒粮食装进仓库。麦子、谷子装进一人高的瓷缸,防虫防鼠,红薯、地瓜藏在地窖里。甜津津的甘蔗,在菜园挖出近一米深的土坑埋下,在雪天里抽出一根,水津津的入嘴。蚕豆、黄豆拥挤在蛇皮袋里,翻年出手就能卖出好价钱。
在这样的丰收季节,干草垛也一定码得整整齐齐。干草是牛冬天的食物,牛对于干草,就像人们经过春种秋收后,面对万物凋零的荒凉,只剩下满仓的粮食一样,干草是对牛任劳任怨的犒劳。作为一个农家,永远不会忘记在冬天为码一方干草垛。牛是农村最忠实的劳力,犹如家庭中的男人,支撑或包揽了繁重的劳作,这便是牛一生的生活。
细心的家庭常常把草垛码在牛棚的一角,靠墙,占一角,避风遮雨。草垛上常倚着一些农具,犁、耙、铁锹、锄头,也许还布满灰尘,或残缺不全。仔细想想,有时又觉得牛更如这些一样的农具,是一件有生命农具。如果牛棚不够大,便要在禾场一角选一处平地。在一边打进一根木桩,留半截在外面作为支撑点,地面铺一层厚实的塑料布,把草垛一捆一捆地靠林庄码在塑料布上。然后把草垛顶再盖一层塑料布,用木棒、石块压紧,再用绳子两边扯牢固,这样不怕风雨的侵袭。草垛是不能渗入雨水的,否则生虫长霉,腐烂的草牛吃了要生病,对牛来说,一个冬天是漫长的,它们永远属于忙碌的田野。
小山似的草垛堆起来,要靠积累。不像麦秸,从麦田收割回来后,经过脱粒机呼呼一响,吐出来后便堆积成形,也不像豆梗,打下黄豆那么几袋,而秸梗却有一大堆。河沟池溏边的小草是不能堆成草垛的。这里的草只能在每日清晨,太阳刚露出红脸,大地笼罩着雾气,枝叶上挂满水珠时,牵了牛直接来啃。但作为牛越冬的食物,这种矮小、细茎的草是没有嚼头的。夏季,当炙热的太阳西落了,或在忙里偷闲,提了竹篮或背着背篓,装上镰刀,深入棉田、菜地、梨园,那里的草经过肥料的滋养,生得青绿肥厚,齐小腿长,晒干后是牛冬天的美食。
割回的草不能淋雨沾水,带着露水的草需及时在太阳下炙晒,满满一背篓晒干才那么一小捆。而且割草也不能心急,只能隔几日到地里转一圈,日积月累。最后还要选个大晴的日子,把以前割回晒干的草再翻了来晒几遍,这样才耐放不变质。放学回家的孩童总会在草上坐着,打滚、翻斗筋,玩扑克,松软的干草上舒服着呢!也有猫狗卧在干草上,喘着气,伸着舌头,挂着尾巴望着嬉戏的孩子们。傍晚时分,从田里回来的大人把草收成几堆,随手抽出一把,捏紧了在手中旋转着,做成草腰子,用胳膊肘,盖紧草堆,捆好,码成形。这沾满灰尘的干草,是牛一冬的依靠。
禾场
每家屋前留出一块空地,土层平整,士质硬实紧密,经过长久的雨打日晒,地面已是枯黄色,这刻意修整的平地就是禾场。
禾场设在正屋前,大都没有固定的形状规则,也许左边建有牛棚猪屋,或者右边搭间鸡舍柴房。禾场是人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它不像运动场,非得讲究长宽面积。在乡村,如果你成家立业要另辟台基新建房屋,那还得多花一份工夫规划出一块土地作为禾场。首先用铁锹铲除生长着的杂草灌木,再拖来新鲜的土块填高填平,从地势、土质上都不可马虎。这样的禾场,鸡鸭可以自由地在那里觅食,不必担心人类的趋赶。晒麦子时,俨然一块天然的席子,能够做到粒粒归仓。人行来往过路,却也是一条宽敞大道。禾场小像庭院,一定要用砖石围成一圈栅栏,杜绝家禽的来访。再辅以花草绿藤,甚至铺上水泥,做好精致的装饰。
六月,金黄的麦子收割完,用板车拉回家,摆放在禾场。请来脱粒机,邀来左邻右舍,拿着扫帚、铁叉、蛇皮袋。发动机带着脱粒机轰轰响起来,人们各行其事,弯腰,扬手,小跑着,没有话语,只见尘土飞扬,一切都有条不紊。此时,禾场呈现出愉悦的繁忙与生活的紧凑。黄豆,尖硬的秸梗,紧闭的豆角,在太阳的催促下,吱吱炸裂开来,金色的豆粒扑向禾场的怀抱。金秋十月,棉花盛开,捡回的棉花要经过数日阳光的暴晒才能卖出去。禾场是晒花的主要场地。在禾场一边划两条平行的直线,在线上每间隔一米左右打下一根拳头粗的木桩,然后在两排木桩上各拉一根铁丝,用铁钉固定牢,搬来用芦苇梗做成的铺架。棉花便躺在铺架上享受阳光的热情。
有学子放学回家,搬了桌椅在禾场做作业,这里亮敞开阔,不会影响视线。做完作业,他们用木棍在禾场画了各种游戏图形,蹦蹦跳跳,有说有笑。小鸟在禾场上空滑翔,叽叽喳喳。有时还有成群的蜻蜓,蝙蝠召开盛大的舞会。阳光从地面缓缓滑动,最后消失在天际。
冬天,喜悦、安静的季节,丰收后的轻松温馨了整个禾场。往日急匆匆的脚印,自然风雨的侵蚀,禾场已变得而目全非。时光的磨打,留下一道道沟痕,牛蹄印、扫帚走过的线路,木桩打下的小洞。遗留的麦粒,冒出新芽,在寒风里瑟缩。用双眼丈量禾场与阶沿的高度,便会发现禾场己被重担压矮了一层。
禾场像经历了一场生活的丰收大战,创伤日渐凸现。风开始肆虐,男人们扛了铁锹,推着单人车,来到池塘边,或者空旷的野外,一车一车拉回土块。细心地把沟痕坑道抚平填高。要想禾场耐用,保持原有的结实,就搬来石磙,套上牛,在禾场了上转几圈。经过石磙数十圈的忙碌,禾场便恢复原有的模样。新鲜的泥土铺在禾场,迎接冬天的考验。
冬天降临村庄,新的轮回即将开始。
水沟
冬天的江汉平原气候干燥,多风少雨,河流进入枯水期。在乡村,如果一条河流不能够蓄半池水,保持一分清凉的水气,那只能叫水沟。水沟延伸在田间路旁,不像溪流放声自然的音乐。但在村里,水沟的面积却并不少,因为它们对于人们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矩形的棉田,网状般错综复杂的水沟若田地的血脉,纵向的水沟每隔一畦田必有一条,像用巨齿梳理过一样,匀称自然。横向的水沟把整块的棉田分成几段,它们汇聚了田地积聚的所有流水,排向外围的溪流。田地的庄稼和人的生命一样,水是维系生命的血液。水沟吸收沉淀下足够的水分,排泄多余的流水,庄稼才不至于生涝。
田地一块挨着一块,生长着的庄稼淹没了条条水沟,远望整块的田地若渲染铺陈着绿的原料。循着小路向前走,一条条水沟若隐若现,见首不见尾。水沟两坡长满杂草,经过流水的冲洗,叶上残留有污水漫过的痕迹。几只鸭子划来划去,不需要猛扎身子就能扑到食物。在田里劳动的人们,从没过人头的庄稼地里走出来,在水沟边放下农具,摘下头上的草帽,垫在身后的草地上,屁股落下来,仰头把腰间的水瓶向嘴里直灌,然后抹一抹额头的汗珠。有马车从身后的小路驰过,扬起的灰尘散落下来。
耕田的牛累了,渴了,主人会牵它到近处的水沟喝水。水沟因为不够深,流水量也不大,积水并不怎么清凉。但疲劳的牛仍会迫不及待地把嘴伸进水中,咕唧咕唧一口气喝好,然后摇摇头,昂头望着远方长哞一声,极有兴致地引吭高歌。遇到水牛,忙里偷闲,趁机溜下水,极力把庞大的身体没入水中,翻几个滚,爽快地浸泡着。庄稼遭虫践踏,人们会背了喷雾器,挑了水桶,提着农药,来到水沟,找一块好下脚的地方,用自制的勺子装满水,调进农药,洒向庄稼,这可是丰收的保障呀。
如果天旱,久不下雨,大小水沟干涸见底。孩子们寻着合适的机会,拿了鱼篓,提着盆桶,卷起裤脚,下到水沟捉鱼。如果叉开双手指头,翻开稀泥,还有泥鳅、鳝鱼。孩子们脸上挂着笑容,乐趣遮掩了溅在身上的稀泥,半天下来能捉数十斤,拿回家是可口的饭食。但是天旱久了,庄稼就需要抗旱,村里会组织得力的劳力,掀开原有的机井,抽水几天几夜。清凉的井水便激动地扑向大小水沟的怀抱。
挖沟在冬天算得上是一件大事。冬季,庄稼收割归仓,卸下繁重担子的人们又想着来年的丰收。淤泥填满水沟,底床抬高,要是连降大雨便会影响水沟的排水量。为了确保来年流水通畅,各家都要把自家庄稼地周围的水沟拓宽挖深,挖起来的稀泥是庄稼的好肥料。人们身穿棉衣,戴着手套,挥动铁锹,在风霜中满头大汗。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