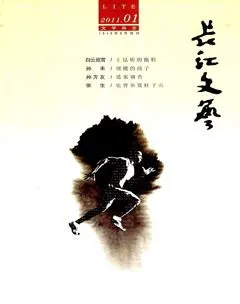漫说古韵今声一笔吟
在学习诗词格律与创作格律诗词的过程中,我曾根据自己的初步体会写过一首七律《诗词创作感怀》:“闲情逸趣贵如金,白发江湖感悟深。烟渚莲荷驱暑气,锦囊诗草润冰心。唐风宋月千秋醉,古韵今声一笔吟。何必苛求枫落句,但题老叶寄知音。”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倡导“古韵今声一笔吟(简称‘一笔吟’)”。所谓“一笔吟”,是指在依照诗词格律吟咏“古韵”(即创作格律诗词)的同时,采用白话文的形式,将自己所吟咏“古韵”的意思(“诗意”或“词意”)写出来。下面,先举一例《鹧鸪天•咏梧桐》后,再谈一谈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倡议的理由,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鹧鸪天•咏梧桐
一木悠然百啭莺,芬芳不解寄伶仃。无心斗艳枝无恙,有意修身荫有情。 冬让暖,夏遮晴,经寒历暑自由行。莫嫌片叶容颜瘦,但借秋声尽赤诚。
【词意】梧桐悠然自得,春莺也为之感慨。可惜芬芳馥郁的花卉,却不理解其中的心愿,总认为它孤独而寂寞。不愿争妍斗艳的梧桐,没有任何烦恼,只想好好修炼自身,并将深情蕴含于枝繁叶茂的浓阴之中。 冬天落叶飘去,为温暖的阳光让路。夏天浓阴遮日,为炎热的人们消暑。梧桐本身却不在乎夏顶烈日,冬冒严寒,自由自在地打发岁月。当秋风吹来的时候,可不要嫌弃梧桐叶子消瘦的容颜。这些树叶之所以无声无息地落去,那可是因为梧桐希望借着秋声来表达自己赤诚的情怀啊。
一、古韵今声一笔吟,可通过“古韵”与“今声”的比较,以展示中华诗词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是中国文学桂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其极为明显的民族特色、极为精练的表达形式、极为丰富的情感语言,极为深邃的思想内涵、极为独特的艺术风格、映射着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灿烂光辉。只是近代以来,由于众多原因,使得本为中国瑰宝的中华诗词,却被“老龄化”了。也就是说,当代的格律诗词爱好者,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一些诗友们,还坚守在这块古老的园地上,并默默地耕耘着,成为他们抒写性情、陶冶情操、品味人生的一个重要平台。
值得庆幸的是,上个世纪下叶以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诗词的呼声不断高涨,一批有胆、有识、有韵之士,用他们的“口”和“笔”,为传承中华诗词而不懈努力。然而,迄今为止,中华诗词被边缘化、“小众化”的现象并未根本改变。为了让中华诗词真正得到传承与发展,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提高现代人对中华诗词的认知度问题则是不可回避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过:“看来好像很奇怪,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这就是说,世界上每8650927a9fea70fda60b70216045146e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诗歌,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不同时期诗歌的体裁也就不同。就拿当代诗坛来说,为什么“新体诗”较“旧体诗”(即格律诗词)有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呢?恐怕与“认知度”问题不无关系。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从小接受的就是白话文教育,所以对格律诗词的陌生感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为了传承中华诗词,近些年来,很多解读与欣赏唐诗宋词的书籍相继问世,让许多读者又有机会领略到格律诗词的风采,激起他们学习诗词格律与创作格律诗词的兴趣。这一做法,对于学习与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诗词是很有成效的。但是,今人翻译古人的诗词,总免不了有“考古”的成分。一首经典诗词,不同的译者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当然,对于古人的诗词作品来说,也只有留给人们去作“考古”式的理解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今人不熟悉古人所习惯的思想感情表达方式。例如,辛弃疾《太常引》上片的后几句:“把酒问嫦娥:被白发、欺人奈何!”究竟真正问的谁?怪的又是谁呢?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闻一多先生有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将诗词格律比作“镣铐”,将诗词创作比作是带着“镣铐”跳舞。其实,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它的美也离不开“镣铐”,难也离不开“镣铐”。为了提高当代读者对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的认知度,必须通过一种途径,让他们认识“镣铐”的作用。如何找到这个“途径”呢?阅读唐诗宋词的译文给我们以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将“古韵”(格律诗词)与“今声”(用白话文写出诗意或词意)一起写、一同读,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对于当代人来说,学习与传承中华诗词,既可通过对照阅读古人的诗词与今人的译文这样的“两笔吟”,以充分了解与品味那些经典诗词的深刻内涵,又要注意认识格律诗词的表达方式,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在阅读格律诗词中学习与掌握诗词格律知识,进而创作格律诗词。当前,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一批诗词爱好者,他们的创作经历大多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遗憾的是,现代诗词爱好者的作品也往往处于“封闭”状态,只是在诗词界“圈内”进行“闭路循环”。为了打破这种封闭状态,让格律诗词能从“圈内”走向圈外,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所以,笔者提倡当代诗人创作格律诗词可以尝试“一笔吟”,进而为当代不太熟悉格律诗词的读者,提供一个很熟悉的参照系。通过这种对照方式,今人既可以正确了解同时代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可以逐步认识格律诗词的表达方式,进而通过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比较,最终认识到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所特有的魅力。
二、古韵今声一笔吟,有助于诗词作者提高用字、造句、谋篇的艺术性,更好地“言志”与“抒情”
创作格律诗词尽管有其特定的格律要求,但是,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它必然是由字组成句,由句组成篇。在熟悉格律诗词创作的基本要求,诸如诗词的“平仄、押韵、粘对、对仗”,以及诗的“起、承、转、合”或词的“起、结、过”这些谋篇的结构性要求以后,最为基本的应是掌握格律诗词的修辞手法与语法特点,进而适当地用字、造句与谋篇。但是,由于格律诗词更多地受到句子长短、字的平仄、韵脚用字、对仗规则等方面的层层限制,所以,格律诗词创作在炼字、酌句、谋篇方面,往往要求更加精炼概括,并体现出跳跃性更强的特点。这种“跳跃性”还让格律诗词的修辞手法与语法特点,同当代人熟悉的白话文相比,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对于今人创作格律诗词(特别习作者),尽管其语言风格应注意与时代同步,但毕竟是经典格式,免不了穿着“唐宋衣冠”(或者说,为了避免“口号式”诗词语言,还是需要一点古韵风味),如果同时进行“古韵今声一笔吟”,对于更好地遣词、造句与谋篇,全面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可能会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
事实上,格律诗词的艺术形式,往往会通过赋、比、兴这些表现手法来实现。按照南宋学者朱熹的说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当然,赋、比、兴这种表现手法,也同样是其他文学体裁经常使用的表现方法。问题在于格律诗词中的赋、比、兴,是在严格的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对仗、粘对等要求下运用的,这样必然导致格律诗词独特的语法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
(1)句子成分的省略:如陈子昂的《感遇》:“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这两句诗的意思可用白话文表现为:“因盖云构(高耸入云的建筑),而把山林伐尽,因做瑶图而用珠翠烦(很多)”。
(2)由于句子的省略,常用修饰词语取代中心词语。如有些诗词中,作为主语或宾语的中心词被省略了,而代之以修饰词。如刘克庄《贺新郎》中词句“记得太行山百万”,用白话文表示则是:“曾记得,太行山上驻扎义军百万”。又如有些诗词中,作为谓语动词的中心词被省略了,而为状语所取代。如李贺《雁门太守行》中的诗句“角声满天秋色里”,用白话文表示则是:“号角声在满天的秋色里回荡”。
(3)句子成分顺序的变换,诸如谓语或宾语前置等。如贾岛《题李凝幽居》中的诗句“僧敲月下门”,用白话文表示则是“僧在月下敲门”。又如苏轼《蝶恋花》中的词句:“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用白话文表示则是:“绿水环绕着的静静的人家,燕子在自由自在地飞舞。”
(4)词类的活用,包括名词用作动词和形容词,形容词用作名词和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和副词等情况。如杜甫《泛江送客》中的诗句:“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用白话文表示则是“热泪满面,沿着劝人多饮的酒杯而下,忧愁连心,伴随着吹响怨曲的笛子而生。”
(5)从修辞手段来说,为了使诗句或词句紧缩、精练和符合诗词的声韵等要求,在诗词创作中还经常使用字的省略、字的倒装、词的倒装、句子的倒装等表现形式。
(6)用典,包括运用事典与语典,也是格律诗词创作较为常见的一种表现方法。所谓用典,也就是对前人语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的引用。一个恰当的用典,可以用精炼的语句包含丰富的内容。但若不知道典故的来龙去脉,读起来就很难懂了。
正是由于上述特点,当代人(特别是习作者)创作格律诗词,其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均不同于用白话文写作。如果在初步写出“古韵”之后,再用白话文写出这些句子的意思,也就是“今声”,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琢磨那些字、词、句,看看它们是否是诗词的语言,能否正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特别是通过“一笔吟”,对照“古韵”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