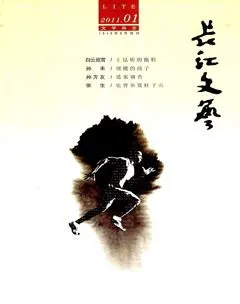也曾负笈桂子山
五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拥挤的地铁里痛苦地计算着还有几站能下去,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个男人在电话里用口音很重的普通话粗声粗气地直呼我的名字,很兴奋地说他第二天就要到上海来,叫我去见他一面。可他的声音对我来说,却显得异常陌生,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我只好借口在地铁里太吵听不清楚,问他是谁,他这才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原来,他居然是我大学的室友戴岳。他是贵州人,大学毕业后就去了贵阳工作。那时我们的联系方式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和多元,除了一个家庭通信地址外,连电话都没有,更不要说手机,EMAIL,QQ和MSN这些先进的玩意了。记得刚毕业那一年,他还写过一张明信片给我,可自此之后我们就彼此音信皆无了。而这次为了到上海后能见我一面,他在无线电波里几乎辗转大半个中国,像前些年那些搞传销的发展下线一样,不屈不挠地找了分布在天南海北的五六个同学,才终于联系上了我。
而就在戴岳报出他的名字的这一刹那间,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们自1991年夏天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离开武昌桂子山那座终年飘着若有若无的木樨香味的校园,已经快二十年了。而华师西区5栋49号,当年我们的宿舍,自从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
相信不管是谁,对于自己的母校,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我至今仍无法忘记1987年9月初新生报到那天的情景。当时,我是由一个在武大数学系读书的老乡送到华师的。他帮我背着随身携带的行李,带着我从武大出来,穿过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一路步行到没有斑马线,也没有几辆汽车的窄窄的珞瑜路。而当我在马路对面终于看到华师的简洁朴素的“同”字形的校门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仍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踏进大门,迎面就是那条两边有着粗大的法国梧桐的通往桂子山山巅的华师校园的大路。或许因为这条路是条上坡路的缘故,我才突然意识到脚下所走的这条路是那么长,又是那么的美。我觉得,这似乎就是我长长的人生的开始。因为从那一天起,我就好像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师中文系,离开过文学。而似乎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向自己设立的那个遥远的人生目标往前走,往上走,开始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走,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无意识的生活习惯。
其实,直到我走进华师的校园,我都对这所以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为骄傲和卖点的大学没有更多的认识。当然,当时的我,不要说对华师了,就是对整个武汉地区的大学,基本上都一无所知。我是河南焦作人,在我们当地学文科的学生心目中,有名的文科高校只有北大,人大,北师大,还有南开。而很多南方的高校,像武大,中大,复旦,以及我后来读研究生的南大等,都像是遥远的传说,其影响感觉似乎与我们河南的“北大”即坐落在开封古城的河南大学与省城的郑州大学相似,而且老师也鼓励大家考北京天津的学校,所以我们对武汉的高校的印象几乎是一片模糊。再加上那时既无网站,也无如今颇为时髦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所以,高考报志愿时就靠老师的几句话和不会说话的一本印刷质量低劣的薄薄的高考招生目录来决定取舍。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从小在部队长大,对军队很有感情,所以很想读个军校。我有个亲戚在石家庄装甲兵学院读书,受其影响,我一度也很想去这个学校读书。但一来我父亲不同意,二来我的眼睛有点近视,只好忍痛放弃了。而这种遗憾,直到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同样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女孩做女朋友,才算释怀。我是个比较恋旧的人,因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重庆读的,后来才回到故乡焦作,所以,我想,既然不能投笔从戎,那为何不借读大学的机会到巴蜀故地重游一番呢?说不定我也会像我的老乡李商隐一样,在雨夜的浮图关,写出“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这样的传世名句来。可报志愿时,我才陡然发现,时为理工科大学的重庆大学不招文科。可想而知,我有多么失望。甚至,这种失望的心情直到此刻,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这一刻,还难以释怀。因此,我觉得,不仅理工科大学应该办文科,而且真的都应该办成综合性大学,这样才能给予考生更多的选择,设若当初重大有文科,我去了重庆,我的今天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不过,那样的话,我也就不可能来写这篇文章了。虽然,我作为一个硬朗的重庆人,多少有点瞧不起成都人的娘娘腔,可作为补偿,我还是选择了远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然而就在我以为马上可以到成都吃龙抄手和夫妻肺片的时候,邮局送来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却赫然印着“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大字。我这才想起,为了多一次录取机会,我还自作主张填写了提前录取的志愿,而我当时随便填的学校就是这所武汉的“华师”。
老实讲,我高考发挥不错,是当年我们焦作市的文科第二名,但我并不是在考大学上有什么远大理想的人,因此也不觉得以那样的分数没上北大之类的学校有多遗憾。可没能去成都尤其是没能去重庆读大学,以慰我的怀旧之情,始终是我的遗憾。也许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会到重庆工作也未可知。命运总是有自己的逻辑,谁知道呢?
不过,虽然对考上华师这所学校没有准备,但我对能被中文系录取倒是觉得很好。因为,我虽对上什么大学没理想,可对以后自己做什么,却老早就有着比较“远大”的理想,那就是成为一名作家。而要想当作家,以我那时的思想觉悟,当然非读中文系不可,受此理想引导,我的高考志愿不管哪个学校基本上填的都是中文系。所以,当我在华师图书馆前中文系的新生接待站办手续时,忽然看到有条“欢迎来到中国最大的中文系”的红色标语时,不禁有种得其所哉的感觉。因为,以我当年的一颗幼稚的心判断,华师中文系既是“中国最大的中文系”,那自然也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中文系,而“最大”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其实就是“最好”的代名词。这让我不禁有点喜出望外,因为没想到自己居然歪打正着,能有幸到这么牛的中文系读书,那我的作家梦自然也是指日可待了。而以我在华师所度过的四年光阴以及后来的经历证明,直到今天,华师中文系也仍然是中国最好的中文系之一,但是否中国最大,或亚洲最大,以及这个口号是在什么背景下又是何人创造出来的,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但这句口号还真让我这个多少有点虚荣心的人激动了好一阵子。因为按当年我们的任课老师的说法,即使华师中文系的实力尚不能进入全国前几名,但最起码,我们是武汉乃至中南地区最好的中文系却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虽让同城兄弟武大A7EFdgjRTc213J7Y+IQNrNmkwAsVkwlAgUUOa2lot9w=中文系的人如骨鲠在喉,可也是没办法的事。但现在看来,可能是老师的自尊心使然,其实当时武大中文系的实力和华师也在伯仲之间。
而一个大学或一个系之所以好,无非是老师好和学生好。老师好,学术水平高,才会有社会影响,同时,也才能更好的教导学生。学生好,人聪明,有理想,将来走出校园后,也才能贡献社会并影响社会。而我认为,那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好的老师,比如教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徐纪明老师讲起课来总是声音洪亮一字一顿,不知何故,他一直对我们87级青眼有加,他的一句常常用来旌表我们的话几可作为我们中文87的“级呼”,那就是:“87级是中文系的一面旗帜”。可能是大家对他印象太好或太深,爱之深切,有时亦难免尴尬。黄曼君老师是教我们现代文学的,对于他,我们早就是未闻其声,已知其名,谁不知道他是唐弢主编的那套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参编者之一呢?而参与这套著作编写的学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这一学科中的佼佼者。不过,那时他们是学科的中坚,现在如尚健在,也都已是泰斗级的人物了。其时黄老师正当壮年,头发乌黑,穿深色正装(非西装),很是严谨,一副方形玳瑁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又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以至于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古板严肃的老派人物,但实际上他上起课来却是天马行空。一次他竟然从自己游玩黄山时买的一根竹子拐杖讲到郁达夫的小说风格,而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其中的联系。田蕙兰老师是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唯一的女老师,她真的是蕙质兰心,像个和蔼的老阿姨,讲着讲着就会停下来,从老花镜上面看着教室里我们这些东倒西歪麻木不仁的家伙,问大家理解了没有。当然,每到这时,课堂上总是鸦雀无声。可到了她的学生吴建波来上课,就不一样了。吴建波大概研究生刚刚毕业,恰值青春年少,他面庞白皙,戴着一副稍微有点圆的文静的黑框眼镜,站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再加上一身黑色的学生装,显得身材瘦削,风度翩翩,其气质犹如一个“五四”爱国青年,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那颗滚烫的中国心掏给我们瞻仰。他在课堂上朗诵闻一多的诗歌,情深处几乎让我们这些无动于衷的鳄鱼坠下眼泪,而谈到周朴园对侍萍的情感,又让人莫名的忧伤。一次我在历史系的楼前与其邂逅,为了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我特地掏出用很多饭票换来的平时根本舍不得抽的绿色“摩尔”薄荷香烟,殷勤地劝他抽上一支。他虽声称自己已经戒烟,可还是没有拂我这个学生的情意,在我用打火机给他点上那支细细的香烟后,他轻轻地又深深地抽了一口,似乎把那根烟的灵魂也吸到了自己的肚子里去。这让我很怀疑他说的自己已经戒了烟的话是否是真的,因为我当时有个非常狭隘的观点,像吴建波老师这样的偶像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不抽烟呢?否则,他写作和思考时的“烟丝披里纯”(inspiration)从哪里来?与他同样在我们同学中深孚众望的教当代文学的老师还有王又平,用武汉话来说,我们当时感觉他是最“抛”也即自我感觉最牛逼的老师。但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们是在他的讲座上认识他的,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批评一切,不仅批评作家,批评现实,还批评我们。有次他在7号楼做了个讲座,他一口气把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所有作家不管男女老幼全都狠狠地批了一遍后,忽然话锋一转,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们一通。那时还没有话筒,但他声若洪钟,说作为我们华师中文系的学生,如果既不关心中国的文学,也不关心中国的政治,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让我们这些听他讲座的人如遭雷击,面面相觑之余,恨不得找个地方一死了之。可天地良心,那天7号楼,底楼的大阶梯教室人都几乎坐满了,可他还觉得人来得太少,因为有的讲座甚至连教室外的走廊上都站满了人。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教授,同时也作为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作家,我也偶然应邀在大学里讲讲文学,可每次只要能来十几个人我就谢天谢地了。不过,可能这是中文系老师的风格,比如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我还听过章开沅校长的高足、历史系青年教师马敏博士谈辛亥革命的讲座。他在演讲时颇为从容,谈起当时虽时尚却很“落后”的“新权威主义”时,似乎也非常淡定,并无褒贬,他无论语气还是心态都平和得多,颇有一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感觉。前些年看到报纸上说他当了华师的校长,从照片上看,他的头发比当年少了很多,当然额头也比过去亮了很多。俗话说只有有智慧的人才会有此福相,他能当上华师的校长,想非偶然。
实际上,我们在校时就已知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一直是华师中文系的特色和强项,而1949年后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由华师的老师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出色的老师。即以现在比较苛刻的眼光看来,如果从史料的确凿,观点的持正和客观,华师中文系老师撰写的这套中国当代文学史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十几年来,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国内的很多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都仍然把这套教材作为中文系研究生的考试参考书,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部文学史的学术价值。
现在想想,虽说中文系的老师似乎无论男女皆有一个好嗓子,但其中真正翘楚还应该是教我们音韵学的朱金声老师。他才真是个帅哥,高大威猛不说,还有一口可以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资深男播音员赵忠祥一争高下的嗓音,颇有磁性。并且,他还精于国际音标的发音。可我跟着他学了一个学期的音韵学,除了知道些类似“平水韵”这样的名词外,并无所得。而且,我不仅音韵学没学好,我对整个语言学都一知半解。但语言学当时却是华师中文系的拳头学科,之后的词汇学,语法学,还有大谈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理论语言学,我似乎都没弄明白过。对于语言学,我们很多同学都像我一样不得其门而入,竟然把系里发给我们的邢福义老师的一本谈语法问题的书全都低价卖给了街道口的一家旧书店。据说后来邢老师一日在此旧书店中看到自己崭新的大作居然一本一本整整齐齐地码在旧书架上,痛心得几乎要当场晕厥。但让他更痛心的事还在后面,当他提出要把这几十本书全买走的时候,见利忘义的店主竟然以原价卖给了他。估计这花了他不少钱。不过,这正说明了他的这本书的确很有价值,它理应值这么多钱。
尽管中文系当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言学领域实力颇强,可我自己真正喜欢的却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我至今仍记得教我们先秦文学的佘斯大老师边讲述边在黑板上用白色的粉笔写下《诗经》的某些词句或《易经》的一些卦爻辞时的情景。而我们崇拜的也不仅是他对先秦文学的深厚的学养,还有他那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其实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书法家。一些老生告诉我们,汉口不少商店的门牌即为他亲手所书。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华师中文系历史悠久,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就是曾经的元老之一。可惜的是他老人家早在我们入校之前就已仙逝。但是,据称得其真传的女婿石声淮先生却还健在。有次他给我们做了个讲座,好像是谈如何做学问的,可我资质鲁钝,除了他的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外所获实在不多。
教我们文艺学的老师中,给我们上文学概论的年轻的修倜老师恬静而温和,和我同寝室的阮辉煌爱屋及乌,对文艺学也着了迷。有次,他还在自己的作业中对修倜老师的一个观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她还特地找时间和阮辉煌认真地探讨了一次。有修老师模范之前,相信现在广东一所中学任教的他也一定是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后来修倜老师还给我们上过电影课,其对电影的博学和热爱,让少年老成的黄夏林也深深为之折服。须知这颇为不易,因为在我们寝室的几个人中,黄夏林很早就喜欢上了电影,在我们还在写诗写小说的时候,他已经不仅开始写起了小说,他还写起了被我们视作天书的电影剧本,每天夹着一本法国电影学家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在校园里晃来晃去。修倜老师在电影方面的造诣得到他的首肯,自然也让我们对修倜老师更加崇拜了。可黄夏林如今把自己文学和电影的才华都用在写广告词和拍广告片上了,他早已是南宁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总。有次他来上海出差,已是满头华发,我们一起回忆了当年在桂子山度过的难忘的文艺生活,似乎把他的记忆唤醒了,他激动地向我表示,他要回去把公司关了写作。还好他没这么做,否则他很有可能在这个商业时代变成个奢侈的乞丐。
而王先霈老师的中国批评史的课,因为是选修,我只上了一节就放弃了。当时我已经是大四,正忙于恋爱,有时与女朋友在校园里闲逛时,偶尔还会撞见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王老师昂首走过。不过,我已经提前上过他的课了,当时我的班主任范明华老师让我誊抄他和王老师一起合著的《文学评论教程》的修订版的书稿,还真是学到了不少文学评论的知识。我也曾偶听胡亚敏老师的叙事学,可是由于其理论实在过于复杂和艰深,只好中途退场。前年我在杭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碰到现已成为著名学者和文学院院长胡亚敏老师,她的发言依然要言不烦,层次清晰,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看来我此生是很难企及了。
同样,教我们外国文学的老师也各有千秋。我比较欣赏的是教我们俄苏文学的朱宪生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经常用俄语给我们朗诵普希金的诗歌,让人不由得为俄语的颤声着迷。他其时可能正在研究丘特切夫,所以常把自己翻译的他的诗歌朗诵给我们听。有一次,他还拿出他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那时还叫列宁格勒)拍的颇为稀罕的彩色照片给我们传阅,以体会博大的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多年后,我听一个朋友说他已调到上海师大中文系任职,可我们却一直无缘相会。因为同在上海,真希望哪一天我们能够再次相遇。他十分念旧,我的室友苏勇强考研究生时曾去找过他咨询相关情况,他不仅热情接待,还真心地建议他若真的走投无路,可在下年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其实,苏勇强虽然贵为我们中文系87级的“名人”,身为著名的走廊歌星,弹得一手好吉他,且善篮球和蹴鞠,但却因经常逃课,再加上学习成绩实在一般,在朱老师心目中当并无甚印象,可作为昔日的学生,苏勇强有事相求,他还是尽力帮助,此举让人颇为感怀。还有就是给我们上英美现代派文学的邵旭东老师,他“美”气逼人,因刚从美国访学归来,穿着比较时尚,除一条皱巴巴的瘦腿牛仔裤外,还总是穿一双当时无比昂贵的美国原版的耐克运动鞋,并不时在课堂上蹦出一两句英语,与我们大聊美国风情,很让我等视美国为神话的“哈美族”颇为折服。但我的同学,原系长跑健将,现任教于汕头大学中文系的张卫东博士对他的印象却不甚佳。因为张卫东觉得旭东老师的课美国生活讲得太多而美国文学讲得太少,兼之他素来对西方文艺理论颇为痴迷,故相较之下,在他心目中,教我们美学的邱紫华老师更有魅力,还有就是当时喜欢对大家唠叨海德格尔的余虹更值得一提。让人叹惋的是,余虹后来在人大遽归天国,实属英年早逝。不然,张卫东肯定会更加推崇他。
可话说回来,虽然讲了这么多的华师中文系的“掌故”,其实作为一个本科生,我对当时的老师们的言行的了解很是浮泛,而当年在中文系87级那一百多号人里,我并不是个出色的热爱学习的学生,甚至说平庸也不为过。再加上我从大一起就开始和武大的一个女孩谈恋爱,一有空我就到武大玩,所以,不仅平时与同学们交往很少,就是与上面提到的那些老师也并无多少交往。他们那些精彩的课程有的我也只是稍有涉猎。更为遗憾的是,还有的老师的课可能只是在课表上有,我却从来也没上过。其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受八九年学潮的影响,我们上半年基本上都没上课,下半年则是基本上没课上。而我直到现在还纳闷,当时的那些课是怎么考过去的,又是怎么有成绩的。现在思量,很有可能是老师们网开一面,都给我们及格了。所以,有一天,我和华师中文系的学长,现与我在同济大学中文系共事的喻大翔教授聊天的时候,我终于良心发现,惭愧地对他说,虽然我拿的是华师的本科文凭,还拿到了如假包换的学士学位,但我其实名不符实,若从实际受的教育来看,我最多只是个华师中文系的三年制大专生而已。
一次,我偶然浏览网络,看到现已摇身一变为温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苏勇强博士的简历时,几让我以为时光倒流了,原来,他在介绍自己本科毕业于国立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时,还在其后厚颜加了一句评语:“根正苗红”。但此语让我在哑然失笑之余,也让我细细地考究了一番,若从在华师中文系所受到的学术的训练而言,我觉得他的话并不为过。自1991年夏天离开母校到现在,二十年来,我也曾碰到过很多从其他比较好的学校的中文系毕业的同龄人,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觉得就知识的传授和基本的素质而言,八十年代华师中文系的本科教育还是很过硬的。前些天,我到北京出差,抽时间到在北师大工作的李霆鸣博士那里小坐了一会。当年霆鸣与我并不是一个宿舍,只是因为异常仰慕长期下榻在我们寝室的武汉著名校园诗人兼华师桂子山诗社社长黄光辉,他经常来我们宿舍打“拖拉机”,所以也与我相熟。他毕业不久就到北师大读硕士和博士,属于“学者型诗人”或“诗人型学者”。因为他不仅写诗还主搞诗歌批评,所以至今与黄光辉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像中国的那些伟大的诗人一样,黄光辉毕业后即投身仕途,如今已是鄂西的一个县的父母官,因此,他已不再像在华师时那样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点根蜡烛边抽烟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经常写一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对于黄光辉创作上的这一转型,霆鸣予以充分地理解和肯定。而自从游学京畿以来,霆鸣已是阅“中文系人”无数,言谈间,偶和我聊起当年在华师中文系所受的本科教育,他同样也赞不绝口,觉得没有在桂子山白待四年。正是在华师打下的底子,才使他可以笑傲别的学校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当然,霆鸣和我一致认为,这主要得归功于当年中文系诸位老师的辛勤教育和耐心的引导。
我的感觉,好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比较好的了解,直接表现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或文化的修养都比较好。说到这一点,我就得感谢当初教我们《训诂学》的黄建中老师,正是他让我们抄写《说文解字》的几百个偏旁部首,才使我之后在与一些文人雅士游览古迹名胜之时,不至于看到众多的铭牌匾额而认不出来或因读错字而出丑。记得当年在黄老师的感染下,平时连瓶酸奶也不舍得请我喝,同时自己也舍不得喝的戴岳居然拨出巨额私房钱买了一本厚厚的精装的《说文通训定声》。作为武汉一名美女级的羽毛球国手的入室弟子,他每周去和教练练习完他最爱的羽毛球后,总是捧着那本书看来看去。我一度以为他将来会成为文字学大师或羽毛球老师。但荒谬的是,直到这次他来上海后我才知道,他后来一时冲动转了行去读了个教育学的博士,现在在贵阳的一所大学的教育系混饭吃。想想真是造化弄人。二是视野比较开阔。华师虽然号称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交通也的确是四通八达,但因地处中西部,文化风气和地位上并不占优,且因远离北京和上海、南京这样的文化发达的地方,很容易让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其学风闭塞。但我后来才发现,华师中文系不仅不闭塞,相反还很开放,甚至很“时尚”。我们在校时,不管是当时国内流行的各种思想文化的观点,还是“先进”的西方文艺理论,都有老师介绍和讲授。所以,当我离开华师到南大读研究生时,以前没有接触过华师中文系学生的南大的朋友都还很奇怪,他们没想到来自武汉的我居然会和他们一样,读过当时他们认为很“时髦”的书,并且思想似乎也很“前卫”。这当然也是拜华师中文系的老师所赐。比如最早向我介绍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的就是樊星老师。现在他已经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而他当时研究生毕业刚留校不久,尚属青年教师,故才会被派来当我们这组实习同学的指导教师。其时我们在汉口的六十五中实习,他也与我们一样住在一间大教室里,周末才回去一次,所以有很多时间与我们在一起。因为樊老师从小就在汉口长大,空闲时他常带着我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边散步边聊天,一次我们去逛武胜路新华书店,他向我隆重推荐了由重庆出版社推出的《兔子,跑吧》,我也因此知道了厄普代克这位在美国文坛影响卓著的作家。樊星老师浓眉大眼,长得很像八十年代的电影演员达式常,为人诚挚热情,真心的把我当成他的朋友。而为了表示我们的友谊,他还把一直不肯轻易示人的钱钟书的《围城》借给我看。因此,实习结束后我仍不时到他在华师东区的一幢筒子楼里的小屋去向他讨教。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去找他,他总是很高兴地放下手头的工作,不厌其烦地和我谈天说地。并且,正是由于樊星老师的指点和鼓励,我才决定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也因此才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正由于这个原因,后来我在上海听说樊星老师离开华师到武大任教的消息时,我还很是为华师中文系走了这么一位好老师而遗憾了一阵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勇强说自己毕业于华师“根正苗红”是并不为过的。但我想,如果不是学潮的影响,我们要是当年能够真的上满四年课程,可能我们各方面的知识养成会更好,说不定也因此在事业上会比现在走得更远一点。
而倏忽之间,在桂子山的生活已成为往事,想想都过去二十年了,还有什么事情不值得回忆呢?八十年代的大学时光在很多人的笔下也已渐渐变成一种“神话”,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没必要把那个时代“神化”成“神话”,而应该对其不足作出检讨,这样才会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大学,从而对今后有所增益。当然,对于华师中文系也同样应该如此。我觉得,相较其他高校,当年华师中文系在对学生专业知识的教导上是很好的,但在对学生未来的发展的导向上却做得不尽如人意。
我认为,这得归咎于其时华师中文系在教育我们时并没有处理好“职业”(oTtxOeJtB2pXawnsCDRcpeQ==ccupation)和“志业”(vocation)的关系问题。因为前者只是谋生的饭碗,后者却是需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的事业,它有一定的理想性,因此也可以激发一个人去完善自我并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前者亦可能成为后者。因为华师是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所以学校比较强调学生的师范性质,在当时我们毕业择业时,系里也多希望大家到教育系统,尤其是中等学校去任教。作为一种职业导向,现在看来,这当然并不为过。而且,因为当时我们都拿了国家的师范助学金,有责任和义务到中等教育部门去任教。但是,我以为中学教师只是一种职业,它当然可以成为我们同学的志业的一种,但不可能成为也不应该成为所有人的志业。况且当年我们的同学中有很多人并没有或并未把到中学当老师作为自己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大家到中学任教,且以当一名中学老师为终身之选,难免会造成很多同学才非所用,甚至大材小用的情况。
而事实上,因受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的影响,当年考上华师中文系的同学,有很多都是当地高考的佼佼者。外省的同学自不待说,即使当年人数占优的湖北同学,在高考中的表现也都很不错。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我们皆可算同代人中的“精英”,而在华师中文系所受的教育自然亦可称为“精英”式的教育。时至今日,我依然有个似乎有些“迂腐”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虽然不能把高考成绩当成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唯一标准,但它的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以此为据,我觉得我们那批到中学任教的同学理应做出更大的成绩。当然,我认为做一名中学老师是崇高的。但我想,这与我希望他们走得更远,作出比一个中学老师更大的贡献并不矛盾。
这二十年来,在我们的同学中,因我在校时和大家交往较少,毕业后只有很少的人和我一直保持联系到今天。像几可称为我在华师读书时最好的朋友的吴标,虽然和我不是一个宿舍,也不是一个班的,但只要我在华师,我们就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似乎有说不尽的话。他温文尔雅,对人对事皆有一颗难得的平常心。1990年夏天,我们和武大哲学系的两个好友从武汉一起骑自行车到杭州,一路上风餐露宿,他从未抱怨过一句。毕业后他到柳州的一家企业的报纸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去年他来上海,谈到这些年来的工作,他依然还是像过去那样平静和不温不火,似乎岁月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更多的同学自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面也没见过,有的面孔甚至姓名在我的记忆中也已模糊。可不管怎样,我们都曾在桂子山相遇,而无论在何时回忆这一切,都已成为我这些年来最为愉快的事。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