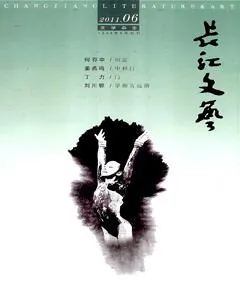学痴古远清
古远清教授长我整整20岁,是我的前辈。他大名鼎鼎,成就斐然,其学术贡献不用我多言。当代中国,学术之于学者,是职业、是产业、是事业。视学术为职业者,以饭碗的心态对待学问。早早把自己钉在某个专业领域,按通常的学术准则行事,从助教到教授,按部就班,干到退休。学术上小有贡献,生活上逐渐安逸,平实亦平淡。视学术为产业者,以经商之道经营学问。会联络、擅出镜、会跑课题、会报奖获奖,名利兼收、官学兼顾。这种学者最擅长做能“来菜”的学问,是时代学术的弄潮儿。如此能人,文理科教授兼有,做一辈子学问真有点大材小用,浪费了他自己的才华,但他们也浪费了学术。视学问为事业者,是把个人才华、志向、兴趣、生命与学问融为一体的人,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计好处但求真知,不擅经营只会苦做。这是书痴型学者、这是传统型或曰本色派学者。古远清即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见古老师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南财大老校区他的住宅。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写张爱玲,找他借书并请教。在没有呼机手机伊妹儿的时代,靠通信联络几个来回,才约定拜访时间、地点、接头方式。他的客厅兼书房全是书,即便是茶几上也摆放着书。他个人的专著,用一种可旋转的小书架竖插着。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很在意自己的事业的人。
张爱玲,或者放大些说港台文学,是我和古老师的第一个学术联结点。他多次主动告诉我海内外出了关于张爱玲的什么新书,他的文章怎么提到我的观点,他对张爱玲有什么新见,使我受益良多。我和古老师都参加了香港浸会大学的两次关于张爱玲的研讨会。2006年那次古老师约我同行。上午在深圳逛完书店他立马要求过关去香港,为的是利用下午的空闲时间在香港买书。学痴定是书痴,古老师是痴中之痴,于此可见一斑。2010年那次,他是在外地开会顺道去香港,特用电子邮件告知行程。开会期间亦给我一个纸条告知书店地址,我午休时跑去购书,大有收获。
当代文学评论是我和古老师的第二个学术联结点。古远清与余秋雨的笔墨官司众所周知,坦率地说,我是站在古老师这边的。一个专治当代文学的学者,对文革历史及相关人物作出评价,是他份内的工作。管你有名无名、任我自由评说,是文学史家古远清的权力,也是十年前学者刘川鄂批评池莉的权力,谁都不能剥夺,谁都不可胡乱猜度批评者的批评动机。尤其是被批评者。你只可就其批评的内容作辨析作反批评,但不可质疑其批评的权力和动机。在这一点上,池莉没风度,余秋雨也没风度。
也是因为古余事件,我第二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到了古老师家里,他的武昌街道口附近财大住宅区的新家。房子更大了,书更多了。在他的书房里,湖南卫视拍古余之争的专题片。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节目,余秋雨座在台上,古老师在台下第一排与他激辩。老实说,我对电视台这种安排很不满,亦对古老师表达过我的不满,但他却不在意。他知道,在这场论争中,圈内外人大都站在他这一边的。
古老师什么都不在意,唯独在意他的学问。不沾酒,不抽烟,不打牌,不用手机。他不喜跟人闲聊,但他并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相反,在人群中他的话特别多,这个人群当然是学术圈。他的话全是事关学术,文坛掌故、文艺动态、谁写了什么文章、出了什么书、发表了什么新见,他自己有何看法,等等,他可以不停歇地跟你聊,如果你有时间和兴趣。这么多年了,我跟古老师见过无数面,我几乎记不得他讲过什么与学问无关的生活趣事,跟我开过什么与学问无关的玩笑。有时我很纳闷:即使他的脑袋比常人大得多,但怎么装得下那么多文坛掌故、趣事、信息,总能如数家珍般脱口而出?而除了学问,其他什么都装不进去?纳闷之余是佩服,真正的佩服。他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实现了自己。所以有时你得原谅他不跟你客套、不跟你谈天气、不跟你搞交际应酬之术。
古老师有点痴,是个学痴,是可爱的痴。
我佩服古老师的还有一点,他做学问总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大学毕业即到中南财大教书,这是一个多年没有中文学科的院校,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即是他一个人的所。凭着他的勤勉努力,凭着他的过人学识,他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著名学者。文学圈知道中南财大,是因为中南财大有个古远清。在这个以学术团队、以学位点为评价体系的集体化学问时代,古老师以一己之力在学术界闯出一片天地,殊为不易。你可以不赞成他的某些学术观点,你可以对他篇幅浩繁的某些论著的含金量质疑,你也可以对他重文学事件轻审美评判的学术指向有所保留,但不得不服他的勤勉的个人化写作,不得不服他做学问的一片痴心。
古老师从大学毕业时,我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小毛孩。当我九十年代中期在他读过的大学读博士时,他已近退休之年。我和他是校友,但母校那种严谨沉稳的考据式、整合式学术传统,我个人认为,我和他也许都继承得不够好。我们总想在文字里有点个人化的印痕,哪怕是不够成熟也要尽心表新见,更不怕得罪所谓权威,因此有时免不了遭到误解和非议。私下里,我把我们算作母校的另类。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跟他有点特殊的亲近,尽管我从来没有跟他如此这般“套近乎”,因为他是一个没法套近乎的人。
约在他退休之年,中南财大有了中文系进而有了文学与传媒学院。在院长胡德才教授的带领下,一批后起之秀茁壮成长,在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已形成了学科特色,颇有声势,令国内外同行瞩目。作为特色学科的开创者,被返聘的古老师继续着他钟爱的事业。他依旧著书立说,依旧出席学术会议,依旧滔滔不绝,依旧精力旺盛。他是一驾不会停驶的马车,永远在学术的道路上冲锋陷阵。
你怎么会相信他已年过古稀?一个学痴,一辈子全身心扑在他钟爱的文学研究事业上,他超越了年龄,他战胜了时间。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