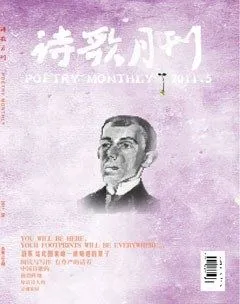老末的诗(7首)
孔子是个爱情故事
三十,他站起来了
却没有人能够和他相对
没有一双能和他对视的眼睛
四十,他对所有事物不再困惑
除了对那一个字
对那一个人
为什么他只能站在冰冷的车外
而她却在封闭的车里
五十,他自认为看透了命运
也把她看成一段空气——
一段曾朝思暮想去呼吸的空气
假如爱有天意
他觉得是没有
至少,在他的爱情里
只有天命,没有天意
六十,他听着所有的欢笑
也听着所有的流言
他也曾经有所想象
但终究觉得这一切与己无关
他自以为找到了内心的宁静
七十,他仿佛又回到了十七
终于敢去言爱
但死神已经悄悄逼近
他一生说了太多的话
对自己的弟子,以及世人
而那最想说出的话
却终于消散在永久的沉默里
只留下她一个人
孤单地读着《论语》
写着给后世的长信
然后又把这些缝在了织锦里
你会死很多很多年
因为你会死很多很多年
比二十四史还要长久
所以在世的每一天
都应该活得年轻
像一个刚册封的王子
时刻敢去追逐自己的公主
因为你会死很多很多年
比宇宙还要长久
所以在世的每一天
都应该活得年轻
像一枚刚爆发的超新星
把所有的俗务和定见
全炸个粉碎
白色明信片
白头发比黑头发轻
每当洗过头后
它就不知羞耻地浮在上面
像刺眼的月光
白头发比黑头发硬
扎根也扎得深
每当你想要拔掉它时
总是会首先殃及它的黑人兄弟
白头发是准时的不速之客
不受欢迎又无可奈何
它是时间老人寄给你的
白色明信片
而寄信人在云端看着你
你越发愁
他越微笑
蔬菜人生
我喜欢剥卷心菜
一片一片地剥开
一片比一片洁净
仿佛那个相声中说的
纸包里有一个小纸包
小纸包还有一个更小的纸包
如此渐渐地小了下去
最后的那张小纸片上
写着两个字:纯情
我害怕剥毛豆或者豌豆
当你剥开豆荚
一个完整的家庭出现在面前
那些大而饱满的肯定是父母
那些小而湿嫩的是它们的孩子
当一家人分开时
它们的心会痛
当你把它们放进清水里
大个的会浮在水面
把小个的藏在水底
仿佛在对你说:
先来吃我吧,先来吃我吧
此刻你会发现
沾在手上的绿色汁液
或许就是它们的眼泪
瓷
瓷——
当我们发出这个音节
就像被什么引力吸附过去
贴在某个长满青藤的墙上
有点冰凉但并不刺骨
有点坚硬但并不板滞
有点光泽但并不耀眼
那就是瓷——
用几千年的青
用几亿条缠枝
瓷实住你的手掌
瓷实住你的人生
一枚瓷器将如何死亡
它不会溶于水
如同泥塑那样
它不会毁于火
如同木雕那样
它会碎
但破碎只是一种失散
并不是一种死亡
每一片都等待着重逢
在那些生命并不永恒的人手上——
重逢
剑齿虎化石
就这样相互凝视
你用你
含着些许尘土的眼睛
它用它
已经彻底石化的眼眶
你在等待一个机会
纵身跳入远古
与它展开生命的竞赛
你或许将长出双翼
或许连根羽毛也没有
你的脑壳或许大于斗笠
或许只有鼹鼠般微小
它也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待你也硬化成石
只能各立一隅
无声地两两相望
再也没有真实的呼吸
只有风穿过空洞的眼眶
遥想当初瞳仁的温润
回忆
回忆有时是一只蜜蜂
专吮吸甜蜜的汁液
回忆有时又是残忍的牙齿
连根带血急遽拔起
回忆有时是沙哑的吸尘器
只吸起一地琐屑
回忆有时又是哈勃望远镜
只能看到天文尺寸
回忆有时是除草剂
让曾经丰茂的地方变得光秃
回忆有时又是生发水
让荒芜的花园长出茅草
回忆有时是己方证人
只呈递对你有利的部分
回忆有时又是对方律师
一直把你驳得体无完肤
人生像一架天平
生活在左边
回忆在右边
时光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缓缓地让右边上升
直到把生活弹进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