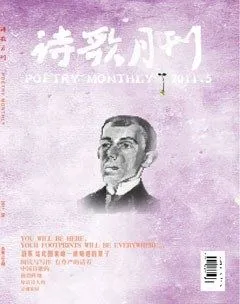《诗经》中的男女情趣(连载六)
从圣人到学者,在自古至今的《诗经》研究中,我们总看着的是一些板着的面孔,或紧皱着的眉头。他们要么将这些乡间男女歌诗断章取义为圣人教范,要么又斥其为淫佚下流的乡野俚语。由于他们的目光总是集中在史呀、政呀、德呀、化呀之上,对活跃在《诗经》里人性的欢乐以及男女之情趣,或视而不见,或予以曲解。
被称为国风之始的《关雎》,写的其实是失恋。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痛苦,还只能算是读懂了一半。因为,在最后两节,话锋一转,这位“君子”从痛苦不堪之中,突然醒悟过来,要对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是情感发展上的一个转折,是由悲变喜的一个戏剧性突变。这一转,很好地呼应了开篇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于是,全诗就显得完整,有跌宕、有起伏;也更多了爱情波澜变化中的情趣。
《关雎》结尾以“大团圆”收局,才使孔子看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不用彻底的失败展示绝望情绪的写作,自然也就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
同样的写作,在《汉广》里也有体现。虽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而且,汉水很宽,没人能游过去;江水又长,船也难以渡过。但是,想娶“游女”的男子却并不灰心,他说自己已经喂饱了马,“言秣其马”,“言秣其驹”;只要那女子肯嫁过来,他会立即用马去接她。
诗里设置的种种困难,看似无法解决,但对追求者来说,这些并非不能克服。既是决心、誓言的爱情表白;又是被爱激励着的一种顽强精神的张扬。
我们有过女娲补天的英雄,也有过夸父追日的勇士。虽然,这些品质展示的都是中华民族草创之初就具备了的矢志不移、追求不息的伟大民族性格,但毕竟是神话传说,是一种精神梦想。在《诗经》里洋溢和喷发着的追求精神,却是真真切切的人的品格;是积极的、热烈的人性体现。如果经师们一定要从这些远古的歌声里,寻找弦外之音,我以为正在这里。《诗经》里有爱情的欢乐,有失恋的痛苦,也有性爱的裸裎,但却没有精神的颓废和绝望,也没有性暴力的肆虐与宣扬。
《摽有梅》写一个女子看着梅子的成熟坠落,想着自己年龄日长,婚事的迫切。从梅子在树上还有“七分”、“三分”到全部落地,细致而真切地让我们洞悉了一位少女心理的变化。有趣的是歌者把变化无常的无形心理,与有形的梅子相依傍,让其似乎变得可以量化。少女对梅子的专注,急切而认真,让人觉得傻傻的可爱,不禁在心里溢出笑声。
《野有死麇》,共三章,前两章都说的是那位打猎的“吉士”,得到了一只獐子,想着怎么用圣洁的茅草裹上,送给那位他爱着的如玉一般“怀春”的女子。最后一章却是那女子的态度:“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那是说,你悄悄地过来,脚步轻轻地;而且悄声的叮咛,别拽掉我的围腰,别叫狗听见汪汪叫。女子的矜持、大胆又细心的警告与埋怨,让我们好像在看一出舞台剧:一对少男少女,蹑手蹑脚约会,轻声轻语提醒;那男子又急切地想动手动脚地拥抱,女子却嫌他毛手毛脚拽掉了围腰;又警告他别弄得狗叫,因为狗一叫也许她的父兄家人就会出来,这一场约会就要泡汤。
诗只三行,却极为简洁而丰富地传递给了我们如此多的信息让我们同样享受了一次爱情约会的甜蜜与欢快。
类似的情趣在《郑风·将仲子》里有很好的体现。《将仲子》通篇是一个女子对情人的心理告白。她像对天神祈祷一样,默默地对自己的情人说:你不要翻村里的圈墙来看我,压坏了我家的杞树,我担心父母会骂你;你不要翻我家的院墙来看我,压坏了我家的桑树,我害怕我的兄弟会骂你;你不要翻我家园子的围墙,压折了我家的檀树,我怕邻人嘴长,人言可畏败坏你。可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女孩子又在心里声明,不是怜惜那杞树、桑树、檀树,是怕你爱到伤害。而且一再表白:“仲可怀也”,我是爱你的,想你的。
把一个女子期待约会,又怕男子稍有差池,惹下祸患毁了爱情,表现得如此充分,细致;既想提醒男子不要鲁莽弄出麻烦,又怕男子误会她不爱他,一再声明“仲可怀也”;如此复杂、婉转的心理变化的清晰展示,让我们阅读时,甚至忘了是在读一首两千多年前古代男女的爱情。
在爱情生活里,并非总是严肃地、庄重的约会。现代生活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赖赖的那种男子,却特别招惹女子的喜欢。在古代的爱情里也不乏其例。
《齐风·鸡鸣》写一对夫妻在床上的对话。女子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鸡都叫了,赶集的人已闹闹哄哄的了,快起床吧。赖床的男子却说:“匪鸡之鸣,苍蝇之声”,那不是鸡叫,是苍蝇在嗡嗡。鸡鸣之声与苍蝇之声,何其远也!这怎么会听错呢?这是男子故意寻找的理由,他能以这种幽默的趣话,化解妻子的不满,以便在床上多赖一会。当然,我们可以将这视为春天,春梦一宵价千金,能多赖一会也舒坦;也可以视其为新婚夜短。不管怎么解,一个“苍蝇之声”,使男子对话增加了趣味。女子只好说:我也是想陪你多睡一会,只是怕人家说你贪床,笑话你。
在《诗经》的爱情表现里,往往是女子十分大胆、泼辣,男子常常显得拘谨与羞怯。
春日踏青,溱河边,洧河边,男女如云。可是在《溱洧》里,我们看到的是女子主动邀请男子到河滩去“相谑”。女曰:“观乎?”士曰:“既且。”看过了,女子还缠着不放,说:再去去吧,那里河滩宽阔,平整、舒坦。在女子的反复纠缠下,男子去了,然后落入爱河,以芍药相赠定情。
在历来争论最大的《褰裳》里,我们看到的女子更为大胆泼辣。她告诉男子,你要和我相爱,就挽起裤腿过河来,别以为你不想我,就没人想我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并用粗话斥之“狂童之狂也且”!
《丘中有麻》写了一个女子在麻地里等她心爱的人“留子国”。她的语言直白、裸露,说等那男子“将其来施施”,“将其来食”。那些斥其为“淫诗”的研究者,视之为直露的性的呼唤。
《蝃蝀》是一位妇女在向人议论一位不顾父母兄弟的阻拦,一心想要出嫁的女子。那种长舌绕绕,指天划地的形象,让人想起戏曲舞台上的媒旦。“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一句话,想结婚,不听父母话,女大不中留。但是,我们从这被戏曲化的指责声中却看到了一位热爱自由,追求爱情,不畏人言的泼辣女子的形象。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的男子的形象,却常嫌猥琐,或狐、或兔、或鼠、或氓。
《有狐》里,那女子眼里的情人只是一只在淇河桥上缓缓走动的狐狸。无裳、无带、无服,令人为之心忧。
在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强势;我们虽不能肯定这是母系社会女性强势性格的残留,但至少还看不出女性在的封建礼教束缚、压迫下所表现出的悲惨与无奈。到了更深远更成熟的封建社会之后如汉儒、宋儒们,已不能容忍这种女性的自由、泼辣和大胆。尤其是宋儒如朱熹一类,动辄斥之为“淫女”;以男性专制为屠手,以封建礼教为斧钺肆意斩割古代妇女自由的灵魂。
《诗经》特别是国风中,在歌颂男女爱情上,表现出的人性的善良、真诚与自由,以及爱情生活的乐趣与情致,才真正把一部《诗经》推上了文学经典的位置。如果真要“以诗证史”,我认为这才是最真实的民族生活史和心灵史。也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诗经》的生命力,看到了它对我们当代诗歌创作所能起到的启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