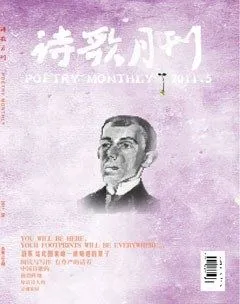一个异乡人的诗歌写作立场
作为一个在故乡安徽桐城生活了十九年,在异乡新疆生活了六年的诗歌写作者,对郁笛在随笔《望了一眼窗外》中所说的:“除了新疆广大的‘美景’,我还需要用我自己的跋涉来表达一个异乡人内心的苦难与喜悦。”我深以为然。
于是,2008年毕业的时候,我放弃了留在乌鲁木齐某报社上班的机会,在离校的当天晚上坐着夜班车风尘仆仆地赶往了伊犁。因为,我想在伊犁开始我的跋涉。
在新疆的前四年,我几乎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了解新疆也是从阅读开始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读到沈苇的诗歌《混血的城》、《两个故乡》时的激动心情。如同D·H·劳伦斯说的,有些人应该被我“诅咒”,因为他们已经把该说的话替我们说尽了。按照此观点,沈苇是要被我“诅咒”的人之一,另外两个就是郁笛和亚楠。事实上,他们也是在新疆对我的诗歌写作影响最大的三个人。
整整四年,在乌鲁木齐老满城那个校园里,除了其中2007年的两个月在库尔勒的毕业实习外,我几乎都蜷缩在安静的地下室宿舍里阅读属于周涛的新疆,董立勃的新疆,刘亮程的新疆,还有韩子勇笔下的新疆文学评论以及沈苇、郁笛的诗歌。这个时期,在2007年底以前,我深信“所谓诗人,就是要看谁是可以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并继而准确书写的人”,于是那个曾经诞生过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故乡文都桐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全部的抒写对象。我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思乡病患者,沉在自己真实与虚幻的故乡里,不能自拔。一草一木,甚至是一个词语,都激发着我,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在写着。一叠叠诗稿就这么放在了抽屉里,后来才知道那些不过都是一些没有新意的吟唱、向往和眷恋。
直到有一天,我在无意中读到了乔伊斯所说的“一个作家写头脑里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写血液里的东西”时,我才幡然醒悟。我一直抒写的故乡,甚至都不在我的头脑里。我应该把自己沉浸在故乡的血液里,而不是一直漂浮着。之后的那些日子,我开始思考,故乡的血液于我V/aDO5ftec2GWYEMKg0pBA==而言意义在哪里?我要怎么才能把自己沉进去,而又进出自如?在这期间,我反复阅读的是故乡桐城著名诗人陈所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阳光·土地·人》。在2008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沈苇的一篇名为《新疆我的天方夜谭》的访谈,其中说道:“多年前,我称浙江和新疆、江南和西域是‘两个故乡’,现在我感到它们是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我的意思是,空间不应构成诗人的囚笼和樊篱。文化的差异性、地域的大跨度往往会给一个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新的造就。”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似乎若有所悟,像是抓住了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有,脑子里空空如也。
但我知道,我必须要跋涉了,无论故乡在我心中有多么重要,我应该试着去了解新疆了。于是,几个月后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去伊犁。如今,两年过去了,对当初的选择我倍感欣慰。
或许是机缘巧合,到伊犁刚刚一个星期,我碰到了适逢在伊犁举行的全国第八届散文诗笔会。我作为接待方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碰到了笔会的代表、来自我家乡的诗人、桐城市文联主席洪放。虽然平时通过电话、网络有所交流,但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异域他乡的伊犁。在遥远的异乡,见到故乡人,自是十分亲切。笔会那几天,在洪放的点拨下,脑子里那些模糊的、分散的概念开始聚拢,至此我才明白我所抒写的血液里的东西在哪里。
作为一个来自异乡生活在新疆的诗歌写作者,面对脚下的土地,我应该有自己的诗歌写作立场和面貌。于是我在对故乡进行抒写的同时,尝试着深入到新疆的文化里,开始抒写新疆。尽管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年,但笔下的文字依然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水土不服和浅显。
而此时对故乡的抒写,我开始以一个“新疆人”的眼光去打量我所怀念和敬仰的桐城文化,我开始慢慢地走进它,希望随着自己的越走越远,对故乡文化的理解也能越来越接近真实。
在伊犁,由于工作的关系,与诗人亚楠接触得比较多。从他身上我学到的更多。他教会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面对自己脚下赖以生存的土地时,应该保持着必要的敬畏和尊重。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不至于荒芜。他在二十多年的写作中,对此身体力行。作为一个南方人,他对草原、对伊犁这片土地的理解,丝毫不比本地人差,甚至了解得更透彻。他说,这片博大精深的土地实在太悠远、太神秘、太让人无法真正读懂了。那些丰茂、绝美的花草,那些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那些银光闪闪的雪峰,那些哈萨克毡房,那些纯朴、善良的牧民兄弟,那些远古的神话和传说,一直在我心中萦绕着,久久不能淡去。不论走向哪里,也无论视线投向何方,伊犁之美留给我的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这就是故乡,这就是我生命的家园。在亚楠的指引下,我开始寻找走进人种博物馆——伊犁腹地的机会。
可以说,整个2009年我都保持着在路上的状态。这一年,利用工作之便,我一直处在寻找、发掘伊犁文化的路上,走遍了具有伊犁特色文化的各个角落。站在当年辉煌一时的伊犁九城的城址上,看着或残存残砖断瓦、一小截城墙(很多的城郭都被一片麦地代替者)时,我再次感到了时间的无情和永恒。当面对92岁的维吾尔老人赛来·吐尔迪悠扬的维吾尔民歌时,它的神秘和绚烂的风情我应该怎么去抒写?当我们驱车几百公里,只是为了寻找阿力麻里城、磨河古城残存的点滴痕迹时,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么博大的疆域和永久的历史?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沉浸在这种行走和书写的快乐中,一路走一路写,于是有了《一个地方》、《伊犁小镇》、《时间深处的故乡》、《一条河流的来龙去脉》等诗歌。当我想把两个故乡当作一个地方、当作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的时候,当我感觉自己已经接近真正的伊犁的时候,我再次发现自己错了。我的那些作品依然表现得水土不服、单调、浅薄,以及意象的单纯、重复……
作家盛慧在《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脉络》中说,只有在离开故乡之后,你才真正拥有故乡,只有离开故乡之后,你对故乡的爱才有深度,只有离开故乡之后,故乡才会成为创作的资源。对盛慧的这句话,我不愿用伊犁这个“故乡”去证实其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