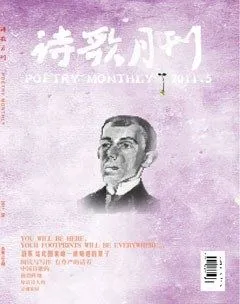章凯的诗(9首)
静止
我站在现在回望过去,
一切那么突兀而又坚固。
七月,当候鸟儿还在频频叫唤,
它们已是即将远去的风景。
每年都是这样。当酷夏
渐渐温柔,放行那些
老之将至的事物一一回归,
而显得可亲,
我们便要从大院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只剩下疏阔的几幢楼房。那又是什么,
还在那儿使我们思虑?是什么,
使我们这些空无一物的穷人儿,
在心底忽然发出思考的呼求?
“——是什么发出这巨大的声音
是身体吗?当身体刚刚老去。”
“——每当有乌鸦憩息时,那广袤的大地,
就从未因高楼大厦而丧失过分毫。”
“——杉木的果实从明亮的光线中坠下,
除了目光,还有什么能紧紧跟随?”
“——所有的现在,我用来安眠、读书,
用来满足于,同世上一切坏人儿诀别。”
“——过去就是静止。”
异乡人
清凉的天气:令人颤抖的云;
蛰伏的行人:一团团微小的火。
生活只能从抑郁中找到快乐。
仿佛只能从煤矿才找到的黑色金子,
流失的时光,让我们体会到片刻的快乐。
所有无名的我,立即从中赶来,
那些徒劳的陌生人难以抑制地流下,
非常孤独,又坚守秘密的泪水。
短暂的幸福
我正写下了什么?——
大海沸腾,是——
它捉住了每一个投海而死的人。
事实上,人们对身体的爱,
终将成为最高的爱。
但如果,它惊醒另一具身体对爱的渴求。
它使另一具身体发出爱的呼求,
它们就自由了——,短暂地,自在了。
椋鸟在东
选择分开了它们!椋鸟与椋鸟。
隆起的山岗,仿佛是自我的主人,
不断地复制着一年的树枝与花草。
但每天,它们都又重新回到土壤里。
落下的雨滴随时发出海洋的颤栗,
植被也随时发出土植的味道。
交缠在一起的枝蔓,我们,
都浸在其中。我们从黑夜而来,
我们整夜不去。而欢腾的椋鸟啊!
轻盈地落下在四面八方。
选择分开了它们:椋鸟与椋鸟,
那飞翔曾多么持久,那鸣叫
曾多么默契!我们即将吐出了沉默的秘密:
看伏起的最高处,椋鸟在东——
那清晨时巨大的彷徨,已被它骄傲地忘却了。
微风
怆然而至。
从水泊而起的风
对幸存者时时
造访,
这明晃晃的揭露,
使痛苦之中的快乐,
如同肥沃的稻田,忽然
发出哗哗的,不明不白的,响声。
那些高高在上的痛苦!
那些使之高高在上的,
更为创痛的,不可道明的甘辛
经过检讨,仍然高高在上。
如月,明晃晃、高远,时又
怆然而近。
愤怒
无论你的内心接入的是哪一种判断,
无论是什么支持你的判断,
快乐,抑或是,占有
造物都依旧存在,也时时死亡。
新来的生命,就是旧生命。
当他们判断造物死了,
旧生命正要求自己接受造物的安排。
他们正流着汗水。
他们发现只能对生死说,我们在。
他们痛哭失泣。像一千万朵黄花同时璀璨地开放,
用以表达入土时看不出来的愤怒。
爱
爱是一种是非判断。
很多时候,
在体内长廊里,
与你,同行。
有时走在你的前面,
有时落在你的后面——
在你休憩的时候。
但无论你,如何
努力呼唤爱,爱都
可能远离你,如同
无论冬夏如何
交替,鸟鸣
都不能,成为一种
苏醒。
悲伤
悲伤是怎样攫住我?
使我如长眠般安静。
又如初次发现自己,
像死海般,在心中升起我
周围的一切喑哑之物。
一切喑哑之物发出巨大的声音
它再次拨响我的痛苦之弦。
我的灵魂!怎样的风帆,
才能在已经消逝的大海中平稳地航行?
无论喑哑之物多么繁盛,
明亮的月光都按时升起,它知道
阳光在哪里,它知道如何借取仅有的光芒,
当翌日不能此时就来临。
水泊
我们跟随一座桥,跨向
对岸。
那宽广的水泊愈加平静。
顺着向下,倒映的
天空,
卷积云,各有流向。
我们被流亡的人潮裹挟,跨向
我们的对立面。
我们安静。但坚固的思想,并没有改变。
我们被他们欺辱,我们的沉默,
让所有人明白我们的内心那么清晰。
哦,不管那折磨人的时针如何
在原地转圜,我们只存在我们的欢乐之中。
如老船停滞港口,尚未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