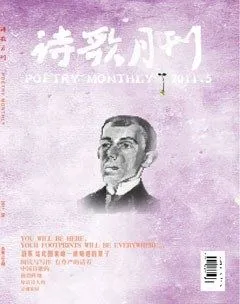洛夫访谈:台湾
胡亮按:2007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学李岱松先生陪同下,洛夫先生过访余卜居之地。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赴台,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外文系,1996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曾于1954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坚持至今,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座重镇。洛夫写诗、译诗、评诗、编诗近60年,迄今已出版诗集37部、散文集7部、评论集5部、译作8部,产生了重大影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洛夫提倡“修正超现实主义”,融中西诗美于一炉,思想渊深,风格奇诡,素有“诗魔”之称。著名诗人、学者简政珍指出,“以意象的经营来说,洛夫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诗人”(《洛夫作品的意象世界》);批评家沈奇称阅读洛夫,“既是一次新奇而独特的灵魂事件的震撼,也是一次新奇而独特的语言事件的震撼”,“是诗人洛夫,让现代中国人在现代诗中,真正领略到了现代汉语的诗性之光”(《重读洛夫》);诗人张默认为洛夫“是现代诗坛少数几位赢得国际声誉的杰出诗人之一”(《从〈灵河〉到〈魔歌〉》)。18日晚,蓬溪,别称赤城,四川诗人雨田、凸凹、吕历、胡应鹏、瘦西鸿、何弗、雪君等雅集,洛夫就我提交的15个问题作了选择性的应谈,返温哥华后复以书面方式一一作答。2008年1月30日,洛夫手稿20余页越洋而至,问与答合榫,对话录成矣。
胡亮(简称胡):大陆对台湾现代诗的研究,自流沙河先生筚路蓝缕以来,古继堂、李元洛、古远清、刘登翰、朱双一、龙彼德、陈仲义、沈奇诸先生均有著作问世,任洪渊、王光明、张同道、叶橹等也多有论述,大陆读者对台湾现代诗的了解日趋深入。就你目力所及,你认为大陆学者对台湾现代诗的研究还存在哪些误区,或者说,还存在哪些盲区?
洛夫(简称洛):就整个文化生态而言,两岸经过数十年的隔阂,不可能不存在一些分歧。大陆学者对台湾现代诗的研究,相对来说,比台湾学者对大陆现代诗的探索与了解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不过,我个人认为,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氛围之中,不论学者或诗人,对于现代诗都会有不同的观念,故大陆学者对台湾现代诗的认识,误区自是难免。据我的了解,你所列的这几位先生,大都拥有可靠的资料,且运用得宜,对诗的解读都有卓越的见识;但内地仍有不少诗人与评论家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史和现况不甚了解,对诗质的优劣缺乏分辨能力,往往第三流的台湾诗人会获得逾分的评价,他们来大陆访问,有时也会得到极为优渥的礼遇,因而使另一部分大陆诗人或学者对台湾整体诗坛会产生“素质如此低落”的误导作用。另一现象是因两岸诗歌语言风格的不同而导致种种误读。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台湾现代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验、辩证和整合,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种汉语诗歌特有的抒情风格,即透过具有象征含意的意象或隐喻来呈现的诗情诗意,这种风格俨然已成主流;而大陆诗人大部分都循叙事的诗路发展,故以叙事思维来评论以意象思维为主的台湾现代诗,误差是免不了的。我倒觉得,两岸诗坛有同有异,也是很正常的。
胡:我认为,五十年代以来台湾诗的发展和七十年代以来大陆诗的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诗歌政治时代——‘横的移植’的时代——‘纵的继承’的时代”这三个阶段,两岸诗歌发展具有一种“同构性”,你认为这种“同构性”是诗歌自身发展内在律动的结果,还是台湾诗发展历史对大陆诗发展进程有所暗示的结果?
洛:你说两岸诗坛都经历过三个相同的阶段,我同意这个说法,形成这种同构性最本质的东西,我认为就是同一的民族文化,但也有若干程度的差异性。由于这种同构性,也就产生了如你所说的“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律动”;但也由于差异性,也便衍生出“台湾诗歌发展历史对大陆诗歌的发展进程有所暗示的结果”。你所谓的“暗示”其实就是“影响”的委婉说法,不过我始终觉得,“异中求同”是我们共同的期待,而“同中见异”也是一种可贵的、可以相互参照的品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与成长要早大陆二十年,这是史实,我很难估量这种影响有多大,但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诗歌创作的先决条件是拥有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这种暗示很可能对朦胧诗的崛起有所启迪。根据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台湾诗人在白色统治下所承受的压力,远不如大陆诗人在六七十年代所承受的更为深重。政治时代的诗歌大都渗有磷的化学物,只有在黑暗时期才会发光。那时台湾所谓的“战斗文艺”,虽是一个历史阶段,但对现代诗的发展即便有所限制,并不严苛,像我在一九六三年开始写的长诗《石室之死亡》和同一时期痖弦写的《深渊》,都有很强烈的反战意识和反现实的情绪,却在白色统治时代顺利出版,未曾遭到任何困扰。到了九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基本上已在民主社会气氛中发展,政治神话已告破灭,诗歌已从“战斗文艺”的框框之中脱颖而出,而趋于正常化。换句话说,这时的台湾诗歌已完全摆脱了政治的干预,诗人再不关心写什么,什么都可写,百无禁忌,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写”,也就是说,如何把一首诗写好,一心追求诗艺的完善和深度,考虑的只是意象与形式技巧的变化;而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大陆诗人,最关心的是“写什么”,总要在诗中说些道理,他们的诗说得太多,他们从不曾想到,诗有时是沉默的,暗示的,意在言外的。叙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把话说明白,所以采取一种直接表达的散文手法,话说得太明,可诗趣诗意也就全不见了。早于六十年代,台湾诗人就已开始全面投入对西方现代主义前卫性的探索和创作上新风格的实验。既然是实验,语言晦涩的失败之作也在所难免,但传诵至今,仍为读者津津乐道,受评论家肯定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就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言,那时大陆诗人所能接触到的就只有苏联文学,对世界另一面的欧美文学所知甚微,世界眼光与见识都不免受到限制;一直到八十年代,朦胧诗群披荆斩棘,撞出那云笼雾罩的混沌时代,也开始了“横的移植”,给诗坛灌入了活水。日后以及今日,虽然纷扰不断,纠缠不休,却也形成了一个生机蓬勃的新格局。其次,台湾现代诗另一项优势,且对大陆诗歌的发展产生暗示作用的,是对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歌优质传统有着相当完整的传承。“反传统”这个词儿的确是台湾诗人早期喊的口号,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诗人们突然全面醒悟过来,总觉得流落异邦终非长久之计,便有了所谓“回归传统”之说;只是传统这个东西,若意味为一种成灰的历史,又何能回归?所以我从不说“回归传统”,而说“回眸传统”,也就是对古典诗歌美学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使某些具有永恒性的质素,借用现代的语言形式,创造出一种新的美来。经过数十年的追索与实验,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个人与时代,台湾现代诗终于找到了一个空前的,精神上和艺术上的平衡点。我觉得,台湾诗人在这方面的劳绩和成就是值得大陆诗人借鉴的。
胡:如果只推选四位诗人代表台湾现代诗的最高成就,我给出的名单是:洛夫、纪弦、痖弦和郑愁予。我的理由是:纪弦制定的《六大信条》对台湾现代诗所构成的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他本人将个性之狂傲与生命之悲凉熔铸为一种独特的“调侃”品质,从而赋予台湾诗歌“别具洞天”的美学际遇;痖弦借力于民谣句式、戏剧情境和小说笔法,成就了一个诗人中的契诃夫,他所“设计”的小人物的命运,在一种“过去时态”的意象缠绕中暗含着被淡化的、压抑而恍惚的悲剧性;郑愁予则将古典诗歌的血液注入现代生活的身躯,从字到词、从词到句、从节奏到意味,展现了非常中国化的“抒情天赋”,与痖弦的“叙事别才”,共同构成了台湾现代诗的双翼;至于你本人,在创办《创世纪》并引导形成一个辉煌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的同时,通过长期的写作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表现出了非凡智力和超人灵性,汉语最为精妙的特质、汉语文化最为精深的内核与西方现代诗最为精微的技术水乳交融,你的全部作品构成了关于人类存在的诗性思考和哲性回答。不知你对我给出的名单和理由认同否?如果不认同,你愿意推选哪四位诗人代表台湾现代诗的最高成就?理由何在?
洛:这个问题太沉重,尤其要我这当事人对你所作的评估表示意见,未免太敏感,的确使我为难。你列出的代表台湾诗坛最高成就的四人名单和推举的理由,除了对我自己不便表态之外,我不得不对你的惊人的历史眼光和洞见表示钦佩。你对这四位诗人的评语都非常允当而精辟,不过,我客观地说:你这个名单未必能邀得台湾诗人多数的认同。对这个名单我不会投反对票,但我得坦诚地说出我的意见:譬如以“二弦”来说,纪弦对台湾现代诗开创之功,无人能予以否定,他制定的《六大信条》虽不无争议之处,却也算得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但就个人的艺术成就而言,恐怕就难以给予最高的评价,尤其在他晚年,几乎乏善可陈。至于痖弦,他是我数十年的铁杆哥儿们,但他在四十多年前(一九六六)就已停笔写诗,他曾开玩笑说:“洛夫是高龄产妇,我是早年结扎。”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才华出众,诗艺成就颇高,只是在产量上远不如和他在质量上相等的诗人。他留名诗史应无疑议,但是否能代表台湾诗坛的最高成就,曾有台湾诗人表示过不同意见,因此我仍愿采用一种通俗的说法:让时间去证明吧!历史老人的话总是公平的。
胡:余光中先生也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但是我认为他以散文第一、评论第二、诗歌第三,他和席慕蓉在大陆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他们是一般意义上的大陆读者心目中的台湾文学“明星”。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洛:又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大陆我曾多次被问到我与余光中的问题,我的回答都很低调,而且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我和余光中一向被大陆诗坛说成代表台湾的双子星座。对这句话开始我有点困扰,因为我不了解我们究竟代表什么。正如你所说的,他是最富人气的“明星”,记得二○○五年成都在春节元宵节期间举办首届“海峡诗会”,应邀参加的两岸诗人有我、余光中,香港的犁青,大陆的舒婷、李元洛、林莽等。由于余光中早年曾在四川念过书,因此特别获得当地媒体的偏爱,余光中在大陆的红,主要是那首《乡愁四韵》,通俗的句法、民谣风的调子,很能吸引一般读者,但余光中还有比这更好的诗,却不为人所知,这对余光中并不公平。这次在成都的活动,连日都有整版的报道,而这些报道是极不平衡的,记者都是诗歌的外行,所以其他诗人在版面上只隐匿在“余光中等”的“等”字中而不名,我也几乎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影子。当时李元洛看出了我的尴尬处境,他安慰我说:“不必气馁,你有你的成就!”在世俗的眼光中,我是被余光中比下去了,没得话说;但余光中本人却不敢小看我。二○○六年十月,北京大学与首都师大两校的新诗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项“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与余光中都应邀参加。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我先离开北京,赶往石家庄参加河北文学馆为我举办的“诗书双艺展”开幕式,来不及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只采访了余光中,事后我才从报上看到这篇访谈,采访时记者很不客气地提到,说目前华文诗坛还没有出一个大诗人,余光中随即也毫不客气反驳说:“我不就是大诗人吗?还有洛夫。”看到这里我还真有些感动。大陆对我和余光中的评价,诗人与学者的一般舆论是,“两人不是同一个档次”,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语焉不详,我也从不去探究。有一个调侃诗人的笑话说,“诗人在历史中才会伟大,若住在隔壁,很可能是一个笑话”,对活着的人而言,历史是一个无法预见、茫茫然的未来,谁知道谁是伟大的,谁也说不准。至于席慕蓉,我与她根本不相识,甚至没有交谈过。据说她在大陆很红,与汪国真齐名,但我所到之处,从没有人提起她,我所认识的大陆诗人,也都不曾读过她的诗;倒是余光中在一篇文章中月旦台湾知名诗人时,竟然把我与席慕蓉毫不搭调地相提并论。该文大意说:席慕蓉的诗集销得好,读者不少,但评论家几乎不提她;而一向甚获评论家青睐的洛夫,读者则不如她多,云云。这能说明什么呢?以能不能卖钱来衡量诗的价值,岂不可笑。
胡:六十年代初期,余光中发表在《现代文学》第八期上的长诗《天狼星》引发了你们之间的论战。你们的根本分歧在哪里?事情已经过去了近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