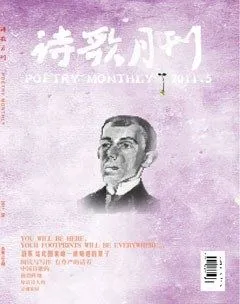胡弦的诗(17首)
天文台之夜
这样的夜晚是陌生的夜晚,
深涧里的鸟儿和遥远的天琴座
都在送来乐声。而一只蝙蝠说出
月亮的家,和它自己藏身已久的洞穴。
——对于人类,万物一直是友善的,虽然
昨天的股市中没有新星出现,只多了
几个吞光的黑洞。一场
来自天堂的雪,也不能把汇率和房市中的
尘埃压低。
但它们仍停在房顶、树梢上……
浮动的白仿佛厘清了
万家灯火和天上群星的关系。
因此我确信:那正在街市中闪光的车流
必然藏有陌生的星系,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都在其中。
——城市服从天象,岁月的真实
来自个体对庞大事物的
微小认识。而道德的珍贵恰恰在于
它最像流星:
在落向人间时,是发光的,
——以及那燃烧掉的绝大部分记忆。
讲古的人
讲古的人在炉火旁讲古,
椿树站在院子里,雪
落满了脖子。
到春天,椿树干枯,有人说,
那是偷听了太多的故事所致。
炉火通红,贯通了
故事中黑暗的关节,连刀子
也不再寒冷,进入人的心脏时,暖洋洋,
不像杀戮,倒像是在派送安乐。
少年们一夜就长大了,
春天,他们进城打工,饮酒,嫖妓,
染上花柳病,后来,
不知所踪。
要等上许多年,讲古的人才会说,
他的故事,一半来自聊斋,另一半
来自噩梦——每到冬天他就会
变成一个死者,唯有炉火
能把他拉回尘世。
“因为,人在世上的作为不过是
为了进入别人的梦。”他强调,
“那些杜撰的事,最后
都会有着落(我看到他眼里有一盆
炭火通红),比如你
现在活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死去过。
有个故事圈住你,你就
很难脱身。
但要把你讲没了,也容易。”
咖啡馆:忆旧
一
波纹在木柱里沉睡,
窗上的薄纱仿佛凉透的花枝。
你沉静,过于温柔。
一阵风在我们心中旅行。
你的手停在幽暗的桌面上:一阵初雪
在季节里旅行。
二
拐过逼仄的楼梯,上面
就是初夏了。空气中,
浮动着类似记忆的暗影。
糖在咖啡里融化:某种不明的变化
在摸索时间的结构。
玻璃花瓶已经替代过什么。
一个下午
正消失于它的寂静。
乌鸦
拢紧身体。
一个铸铁的小棺材。
它裂开:它的两只翅膀
伸了出来。
——当它飞,
死者驾驭自己的灵魂。
它鸣叫时,
另一个藏得更深的死者,
想要从深处挣脱出来。
——冷静,客观,
收藏我们认为死亡后
不复存在的东西。
依靠其中的秘密,
创造出结局之外的黑暗,
并维持其恒定。
随摄制组航拍一座古镇
码头上的旧机器有宁静的苦味,
江水无声的奔流,来自废铁的沉默。
一阵风俯身到江中饮水,堤上的人
像梦中人。
他们的倒影在水中晃动,群山的
也在那里晃动,带着歉意。
店铺的板门灰蒙蒙的,
猫在瓦片上屈身前行。
据说它久久蹲伏的某个脊头
连着我们的前世。
磨光的石板路,越来越接近穷人的耐心。
在高处,我曾想对生活作出概括,
而街巷、江水、屋顶……分行,交叉。
精致的结构间,忍受之物,
仍是难以拆解的实体。
林中
——回忆多么漫长。
椴树的意义被用得差不多时,剩下的
才适合制成音乐。
午后,树林贴着果肉,
言说者,追随提前出现的话语。
“要再慢些,才近似
肺叶间的朝圣者。”
太阳来到隐士的家而隐士
不在家。
树叶拍打手上的光线,
蓝鹊在叫,有人利用它的叫声
在叫;甲虫
一身黑衣,可以随时出席葬礼。
搬迁
——接近尾声。椅背上的线条
滑向另外的空间。
我坐下来,望着桌子上的光,那是
长久抚摸产生的意义。
书在纸箱里,字在黑暗里。
氧气有限,曾被反复谈到的启示
摇摆于窗帘和胶带之间。
挂钟用嘀和嗒
区分着时间的原声与回声。
“哪一声更重要?或者
是机械的区分带来了重叠的意义?”
换气扇嗡嗡响,把室内的寂静
抽往外面的空气中。
搬运工还没到,
楼梯无声地向下旋转。我知道,
过不了多久,脚步声就会从那里出现。
——脚步声总是从那里出现,从
永远消逝的人,和等候者之间。
空楼梯
静置太久,它迷失在
对自己的研究中。
……一块块
把自己从深渊中搭上来。在某个
台阶,遇到遗忘中未被理解的东西,以及
潜伏的冲动……
——它镇定地把自己放平。
吱嘎声——
隐蔽的空隙产生语言,但不
解释什么。在灰尘奢侈的宁静中
折转身。
——答案并没有出现,它只是
在困惑中稍作
停顿,试着用一段忘掉另一段,或者
把自己重新丢回过去。
“在它连绵的阴影中不可能
有所发现。一阶与另一阶那么相像,
根本无法用来叙述生活。而且
它那么喜欢转折,使它一直无法完整地
看见自己。”
后来它显然意识到
自己必将在某个阶梯
消失,但仍拒绝作出改变。固执的片段
延续,并不断抽出新的知觉。
“……沿着自己走下去,仍是
陌生的,包括往事背面的光,以及
从茫然中递来的扶手。”
下午四点
风捉的不是树枝而是它的颤动
(捉得树枝快要疯了)
风又用同样的手法
捉下午四点这个时刻。
玫瑰花和叶子都已落尽,
只剩下下午四点的刺。
矮小的刺,尖的刺,几乎就要刺到
关于玫瑰的定义。
下午四点,光线重新认识玻璃。
表格依旧严谨,有个公务员
在里面张开双臂。
酒摸到自己的声带并盘算
该在晚宴时说些什么。
下午四点,鸟飞过旧巢,
我也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反复降落在
自己左右。
有个孩子在纸上画下埃及,
有个老人在朗诵,声音很大,大过了
那些句子的需要。
两个人的死
一个叫建设,那年六岁,死于
胆道蛔虫病。我记得他抱着肚子,
俊俏的小脸因痛苦而扭曲,背
死死抵在绑着疙针的小杨树上。
他的父母都是哑巴,除了贫穷,
没有钱、药,甚至连语言也没有。
另一个叫王美娟,死于十三年前,
二十八岁,因为宅基地、丈夫酗酒……外遇……
她喝下半瓶农药,在大队卫生室
折腾了大半夜。没救活。
两个人的死,相距
二十年,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带走了
一部分病,让这个世界上的苦难
不至于过分拥挤。
他们都是我的小学同学,同龄,同班。
但在阴世,他们的年龄却相距悬殊。
如今我想起这些,因为
我正走过这片墓地。他们的坟包
相距不远,串个门,
也许用不到三分钟。在另一个世界,
哦,假如真的有另一个世界,
我愿他们相逢。
——死过的人,不会再有第二次死亡,
我愿他们辨认,并且拥有
在人间从未得到过的幸福;
或者,一个是儿子,另一个
做他善良的母亲。
山谷(组诗)
风
不可能有被风吹散的痛苦,
这是别人的山谷,现在,它把别人不知道的
给了我。
此地,没有永久的疑问,但有过永久的答案,
做过官和做过土匪的,名字都在家谱里安居。
而这些,对一个过客有何意义?
藏在心中的城市,一座山谷对它并不陌生,
——与世界一样,山谷,同样有它的反面。
就像风吹过,树在摇晃,
但在树的内心,风毫无意义。
不是因为愤恨或者反叛,它们只是以摇晃的方式,一次
又一次
完成了对自己站立的肯定。
承受
承受山谷如承受自身,此中
有模糊不安的欢乐。
如同身处世界的另一面,我找到了断裂链条的接环,
远方雷鸣的盲目威力,绵延群山对紧张感的厌倦。
而对于坐在黑暗中的人,有一颗星就够了。
神明的意图
是隐秘的,在最离谱的行动中,仍有象征,有需要忠于
的尺度。
这样的夜晚,我们能到哪里去?
我们在呼吸,星颗在慢慢燃烧,仿佛世界的秘密尽在其中。
一缕简单的光,正把松涛送进我们的心灵。
静
再次说到静,一种
类似幻觉的静,依附着山谷的永恒性。
它是要我承认,某些曾经被神承认过的东西?
它的坚定使我慢慢融化,丧失了边界,渐渐
变成了自己的脚步声。
如同窗台上放过的烛火,微弱光芒留下的苦味;
如同海棠树,在短暂的花期里,用叙述修改成的一声叹息;
身体里,蓄积着满含泪水的静。
——并不曾得到回答,
我只是明白了,自己一直携带的问题
是无用的。
村庄
村庄从前是山谷的产物,现在不是。
对命运的反抗,正好吻合了时代之恶。
一座山谷和一座城市,它们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
但山谷不会给出谜底,
犹如这小巷之上的天空,此刻,
含着忧郁的蔚蓝,并只为一段小巷而存在。
它与从这里出发的目光相遇时,才因为悲悯,而成为
这个世界看得见的边际。
山林
能拒绝一座村庄,却拒绝不了这片山林。
许多年,它发出的声音,与我们的需要契合。
有人曾离开这里,类似从自身的沉重中挣脱。
但许多年后,仍需要一座老院子,
——我们把它保留在记忆中,完成了对贫穷生活的依恋。
哦,岁月,它抛下一座山谷独自而去,又让它从过去
不断来到此刻,这长久的给予
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未成为弃儿,正因为曾被一点点
放进经历过的事物中。
不可能
我犯下了罪。
我没有否定神灵,但一直试图同神灵交谈。
而神,是用来沉默的。
不可能一边是人,一边是神,中间是山谷。
也许山谷并不曾昭示什么,是我们的希望产生了痛苦。
但要有痛苦来过,当它退去,浮现出来的石头,
才被沉浸在幸福中。
葱茏(小长诗)
1
曲折的穹顶下摆放着摇篮,
有些丢失的梦像手臂的晃动。
这是午后,谈话的声音小了,石头
陷入沉默,林木的倾听却愈加入神。恍惚间,
遥远的呼声像树杈上的幼芽;一凝视,
又变成了不堪攀援的枯枝。
——无名的探寻,借助风力不断缠绕过去,
将看不见的气袋和涡流编织在一起。
而在另外的日子里,榛莽和公园
交替穿过纸上的庭院。
——这是许多日子消逝后的日子,枝柯晃动,
乐趣稀薄,站在道路两旁的树,
如同需要想起的记忆。
有人躺在草地上,眼望浮云,
有人在黑暗中掘到从前的房屋,铁、骸骨。
而迟缓、疲惫的躯体,沉浸在
耐心一样晦暗的树阴中……
——太久远了,往事如同虚构。
……仿佛从未发生过什么。容纳了
所有瞬间的世界,唯此树林像是真实的,让人
猛然觉察:那些曾庇护过我们的天使,
已变成了走过瓦垄的猫,无声无息。
2
要在林木上方,太阳的光芒才饱含善意。
毛绒绒的嫩叶,恍如苦难岁月
留下的卵子。而在街衢、闹市,光滑的屋脊
像鱼,总想从时间的指缝间溜走。
它们,也许真的因此躲过了什么。
“任何可以重来的东西,都有低级的永恒性。”
在古老的郊外,有些树
已历千年,我们仍不知道它们想要什么。
“它在历史里走动,使用的
是它自身,还是它的影子?”
疑问一经形成,就和所有的事件同在,
……抵制、辨认、和解,严格的法则对应着
散漫的株距。
对转换的凝视使一切(废墟、拆掉的庙宇、线索……)
按照树的方式进入另外的思绪。
“树站着,一定是有种
需要不断强调、并表达清楚的东西。”
粗糙的黎明中,我们醒来;梦
和睡眠分开,从中变绿的树林,已在
绵延不绝的生长中分出了段落。
3
“节外生枝之物,都有棘手、固执的秉性。”
夏日潮湿,枯木上的耳朵
会再次伸进生活中来。
老透的树干里,波纹回旋,茫然而又坚定。
杂乱无章的枝条间产生过天籁,但还不够,还需要
称心如意的琴、鼓、琵琶、二胡、梆子……
——存在一直是简单的,当音器在手,才可以
在另外的声音里重回枝头;才可以
借助复杂的叙述敲定内心的剧目。
或者,析木为栋,为梁,为柱,为斗拱、桌椅……
或者,在木头上刻画山水。雕花。
(没骨。缠枝。也是令人目眩神摇的植物学。)
尺寸即自然。雕刀足够锋利,就有了天空。此中
有自明的痴情、野蛮的甜蜜……
而人,总是处在两者之间,拿不准
哪一个更好:枝间的长笛?还是屏风上的小兽?
或者哪一个更糟:大风吹折的树林,
还是镂花内无人察觉的深坑。
4
树与生活怎样相遇?
只要嗅一嗅花香,和汽油味,就知道,
它们没有交流,也不会相互抚慰。
这正是我们的悲剧:总把最重要的事
交给引擎来处理。“在对方的空虚中,才能意识到
自我的存在。”然而
树梢,塔吊,霓虹,又交织在了一起。
(我想起一头饲养在纸上的挖掘机,
正吃掉街道、水管、石块的呼吸。)
木柴杂乱,冬天强大,让人怀疑,
一直有一位冷漠的神,存在,并允许了这一切。
当错误变得完美,我们更需要
单独的考量;需要一棵从林中出走的树
在我们思想里的脚步声。
是的,不管世界有多大,围绕着一棵树的
一直是一小片冰凉的漩涡。
城市如同巨人在狂欢。一段树枝,
也曾有过钢筋一样强硬的追逐。——它是要分清
事物之庞大与伟大的区别。而对此
我们能知道些什么?蛀虫的痕迹,
还是藏在它预感中的金属种族?
也许,灵魂的安详正来自于此:
舵一样的墨绿山脉,以及坚硬、挤在一起的
树杈,与空间那无休止的刮磨。
5
一旦置身林中,仿佛就跨出了城市的边界。
(哪怕是一小片晨练者的树林。)
一两声鸟鸣,孤寂瞬间包围过来,足可使今天
不同于往日。
干净的石头,带来一些失败的联想。
相比于树,苔藓更懂得怎样获得宁静。
松树的鳞纹,仿佛往事游弋的幻影。
茑萝太柔软了,如果思索太多,是否会打扰它们?
小杨树走进刺槐的梦,它无所得,它回来,
在一阵风中摇摆不定。
(它还小。生活,尚是不需要意义的哗哗声。)
树各自独立,枝叶却交织在一起,
它们的影子也交集在一起(相比于它们,
影子,有过的交换也许更多)。
香樟光滑的横干上,还留有离去的手的抚摸。
蔷薇的刺,已构成了和虚无的尖锐对立。
一场蓝雾来过,所有隐藏的,呈现的,
都值得尊重:无名的手,依恋,泥土,莎草……
或者,叶面上的露水,那没有边界、
不可回收的感知。
——一切都无须证实。对林木的热爱,
最后,停留在对一根枝条的理解中。
6
而在更远的树林里,鸟儿如一颗颗受创的心。
飞翔的蝴蝶,像打开某种神秘存在的钥匙。
有种古老的活法,在榛叶,和梧桐中。
有种真诚,在乌桕的根,和它身体的斜度里。
如果智慧让人厌倦,荆棘会长出更多的刺,红枫
也会带来更单纯的热情。
虽是某种理想的代言,它们
并无受难的面孔,只有云杉高耸的树冠
略显严肃,须抬头仰望,并顺便望一望
树冠上方高远的天空。
(那里深邃、沉静,和我们像不在同一个时代。)
坚果如香炉。侧柏的皮,粗糙如砂,从空间中
提取的沉默结成它的身体。
不知名的小花儿有轻的发音,使气流中
交错着无声的节奏。
所有的细枝都仿佛在说,只要心有怡乐,就不妨自得。
在光阴坚固的实体和花瓣的柔软间,
它们只爱自己的幸福。
7
有时是一座夜的树林,披拂的枝条
探身在未知中。
太黑了!黑鸟的叫喊,被绑在黑暗的柱子上,
患白化病的云茫然地在天空里走动。
太黑了!影子早已抽身而去,每件事物都像是
黑色之源。偶有一两点
微弱的光,在其中追逐死亡。
——那是荧火一闪一闪,稍稍增多时,它们
聚集,像把灵魂扎成了花束。
而我们的灵魂
归于何处?是远方那恍如在沉没的巨舰般的城市?
还是眼前这回声般的黑暗?如果
生活已被转移到别处,那么,
树林是什么?拥有全部记忆的黑暗是什么?
正确的爱曾经像恋人的眼神,而现在,
是错与迷失,是罪与道德混合的小路。
一只莫名的手,像来自另外的星体,带着
另外的方式。被毁掉的街区、道路、村庄……
都已不见。它们在消失
和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轮廓,以及
树与它们、它们与它们之间的联系。
8
有时则是一座时间的树林,
饱食光阴,捕捉失踪的时辰。
譬如雷雨过后,棠梨会将一口气吸回肺腑。
又譬如椿树,当它的腰身长到足够粗硕,
便不再用来衡量什么,只把寂静挪动。
或者是瘦细、预言般的光线,在阴影中梳理声息。
时间,时间是一只小兽的滑行,
也是数百万棵树上,露水同时的滴答声。
是鸟巢,是落叶纷纷,是金龟子坚硬的
胸甲、指爪,木杪间再次卷来的银河的回声,
是蛛网、鸟鸣、雷电、蚂蚁的洞穴……
“你怕吗?”“不!”当时间呼啸而过,
对命运的指认,才具备了令人信服的准确性。
时间,时间是木已成舟守株待兔,是野火、木鱼、十字架,
记忆中的膝盖,灯晕的薄翼,木墩,
沉香积攒的黑而无声的风暴。
当许多事过去,时间是纪念品一样的老人。
当他踽踽走过,一面玻璃幕墙会突然以全部的痛苦
将一根新发的嫩枝紧紧咬住。
9
树怎样生长?一直是个秘密。
树的上方,宁静也在生长,这符合了
树对自身的要求,还是天空的需要?
也许这正是身体的本真:有空缺,又被呼应充满,
当它快乐,它就摇晃,以期
让快乐知道自己为何物。
当它身上的疤痕变得模糊,不再像眼睛,不再
有清晰的凝视。岁月的蹂躏,
才从中获得了更宽广的象征。
根在黑暗中连接,某种深刻的东西早已被确认。
未来像树枝在分叉——同过去一样,那里
仍会有南柯一梦,或束手无策。
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天性:像树那样
把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
只需一粒幼芽,就可指出时间的相似性,
又在抽发的新丝里,找到未知世界的线索。
叶片飞舞,朝向广大的时空,抛掷它的脸、脸部的
气流、光、不规则的花纹……
而星群焚烧,天空拧紧腰身,天地间
用力过猛的地方,仍是树喀咔作响的关节。
10
树林从不着急。没有比它更稳定的东西。
——风暴并不曾使它变得空虚。
手拿斧锯的人,得到过人世的幸福,
怀抱林木者,则能腾云驾雾,飞过噩运。
更多的时候,树被用作比喻:
一个开花的人,一个长刺的人,一个有曼妙枝条的人,
——我们,在从中寻找生活的等式。
而林木,似乎也对这比喻有所感应,因此,
香樟有蛊惑的香,核桃内心有隐秘的地图。
仰面槐与垂柳有无名的交换,
悬铃木充满音乐的肺腑,我们也能置身其中。
——转换,带来了对自身的静观。
这也像比喻:为短暂而生,事毕即脱离。
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仍是孤独者、可怜人、坏蛋、信
徒。仍有
林木在我们心中排列。我们也会
穿过幽冥与晦暗,重新来到明朗的枝头。
在那里,花朵正开,路径纷呈,精神的芬芳招展洋溢。
我们再次从自己的心灵出发,那些花瓣
是胞衣、子宫,神圣而秘密的往生之地。
11
在殿堂上,“粗大的廊柱有助于思索”。
在废墟里,美别有意义:把拯救与受难合为一体。
“破败的心灵使它们受了委屈”。而此刻
它们在我的房间里,分别被叫做
铁树、龟背竹、银叶兰……少女、思乡人、僧侣……
电话、书卷、文字里的白银和我想起的事
陪伴着它们。公园在外面。但一株石楠
也会把自己触及的空间
与更远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仿佛
尘世中有多少死结,它就会长出多少对应的枝条,一个
千手、公开而秘密的观音。
“对于具象的世界,也许还需要一张坚实的木桌
把花朵锲刻……”
“……更多的尤物也在那里。更多的
抄经人,皮条客,赌徒的指骨做成的骰子
同样会在木桌上滚动。”
曾经力透纸背的一笔,在叙述的应带中露出破绽。
是的,文字深处的树林,我们一直不知道那是谁的树林。
而时间,变成一片林木是可能的:在生活
和文字之间,它寄托自己,不希望沉入更遥远的过去。
明白了这些,吹过大地的风不再迟疑,忽然
跃过窗口,加快脚步,从一个时代
朝另一个时代赶去。
12
并不是林木在引领一切。有时候,
它也拿不定主意,需要听一听我们的说法。
我们周身遍布林木的影子,并在它的摇曳中
寻找自身,寻找那最精确的口吻。
“每个人都是辽阔、不可穷尽的。”也许是吧,但面对
娇艳的花朵或地上的落叶,我们该庆幸还是惭愧?
“到最后,我们都是吃往事的人。回忆,
却变成了与回忆相连的东西……”
据说树呼吸,用的正是我们的呼吸。
有个人去世了,殓入棺木;一棵树陪他前往他乡。
对于这棵树另外的生活,从此再无消息。
树多得像恒河的细沙,命运又何尝不是?但一棵树
不会玩味我们的命运,并自鸣得意于对它的感受。
当它吞食陌生的事件,自己,也会陷入挣扎中。
……另外的人在公园里晨练,树同样陪伴着他们。
而它们自身,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类似
一切存在与相遇的基础:
没有开始,因为你一选择,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也没有结局,因为能够移动的不过是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