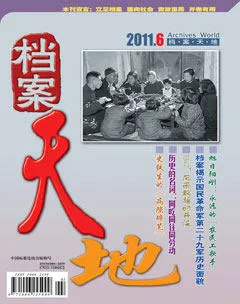毛泽东与秘书\\档案工作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开国元勋,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伟人。他在我国历史上绝对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在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中还躬身亲为了不少秘书、档案工作,成为了在档案的搜集、保管、整理、编研利用等方面独具卓见的导师。今天,回顾他老人家关于档案工作方面的论述及实践,对我们每一个档案工作者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三次直接担任秘书工作职务
第一次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大会秘书。据1936年陈潭秋同志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说,“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7月底开的。大会的组织是非常简单的。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周佛海”。为防止意外,大会将代表们的文件集中隐藏起来,大会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大会主席都是在和秘书共同组织下进行完成的。
第二次担任秘书工作是1923年,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代表建议中央局实行秘书制,即党的最高级领导机关设立秘书支持机关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代表们的意见,在中央执委会设立秘书,委任毛泽东为第一秘书。本次会议通过的《中共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的主要职责为:负责党内外文书通讯及开会记录之职责,并管理本党文件。毛泽东很重视保存文件资料工作,比如,1920年到1925年的档案资料3700多件原稿就是当时保存下来的,现在成了我们党和国家文献宝库中的宝中之宝。
第三次担任秘书工作是1924年上半年。这次担任的是中国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总务主任。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定。依照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兼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秘书处总务主任,负责帮助国民党建立秘书工作。1924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规定:秘书负责保管文件、印制文件、搜集文件、列席部务会议、“协助部长等整理部务,保管文件及图书,编制本部之部务报告书,起草一切公开函件”等。
对档案工作精心在意
毛泽东同志对档案材料的安全是极为关心的。他直接管理“本党的文件”时,兢兢业业,使数以千计文件的安全无恙;在指挥千军万马行军作战时,他肩挑马驮,边作战边阅办文件,对形成的档案叮嘱身边的人员说,遇到危险,不要管我,先抢救文件。这样的小故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胜枚举。
1936年8月潘汉年由南京来到陕北,通过友军防地时,友军一位副官热情招待,他离开时,不小心将随身携带的文件遗忘在了那里。潘汉年发觉后,随机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主席当即作出了相应的处理决定,他马上联系我方与友军联络的一位同志发去立即收回误交某某文件的电报,电报说:事关重要,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收回,一纸一字均不得散失,免误机要,切切。短短几行文字,表达了主席对机要档案工作的重视和关切。
1946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时,毛泽东对相关负责同志说,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文件材料的片纸只字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同年11月他还亲笔签署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其中做了如下规定:“一切机密文电,除最高负责同志及其所指定的读者外,其余任何人不准翻阅;不必留存的文件,用完后可以烧毁;一切密件可指定专人妥善携带;凡保存密件的地方,绝对禁止无关人员来往和接近”,表现了他极为重视文件材料的安全保管。
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中央机关的档案部门将档案撤离到陕北山区,一部分隐藏起来,一部分由档案工作人员随身携带过黄河转移到晋西北。同年4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签批了由刘少奇和朱德呈报的《对于处理文件之决定》,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具体执行。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护送档案的曾三、裴桐负责同志首先接收中央机要处、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和其它有关单位移交的档案;其次取回坚壁在陕北的档案,并依照情况进行处理;最后是对护送的档案进行分类,分为重要而不秘密者、秘密而不重要者、不重要和不秘密者、又重要又秘密者四类,并组织人力清理了几个月,终于按照上述要求分开,编制了目录。
1949年,为顺利接管国民党机关的各类文书档案,毛泽东同志于4月25日亲自起草并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布告数处提到接管文书档案问题,严肃要求在官僚政府和资本家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之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料、机器、图表、帐册、文件、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并警告,“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文件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从而使一部分重要历史文件材料免遭毁灭。据统计,仅接收南京国民党中央一级党政军机关文书资料就达130余万卷。这些文书材料成为党和政府的历史财富,并在建国后开展的很多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凭证与参考作用。同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来电,请示处理党的历史文件的办法。这里所说党的历史文件,是指党中央在原上海地下档案库保存的一万五千余份珍贵历史材料。中央办公厅于本月18日发出《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的电报,这份电报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刘少奇、朱德圈阅,周恩来同志批发。中央办公厅的一份电报,有四位伟大人物同时签发修改,真是不寻常啊。华东局按照这个文件精神,奖励了保存文件有功人员,并将全部档案派专人护送到北京。
重视档案的收集编研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对于文件材料的收集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他以马克思、列宁重视收集材料为榜样,强调收集文件材料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收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对党内,他曾严肃地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他还指出:“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为此,他号召全党重视对国内国际多方面材料的详细占有和研究,以利于工作,利于革命。1941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要调查研究,强调研究和解决革命工作中的难题就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收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毛泽东同志收集文书材料的范围与内容是十分广泛和丰富的,既包括我党我军直接形成的各种文件原件,也包括敌方的各类资料和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各种资料。
从1941年9月开始,毛泽东开始着手《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为此,主席对档案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工作。起初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只是为了给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并没有汇编成书的打算。这项工作于1940年下半年开始,最初由任弼时等人负责,后来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和裴桐两位同志,协助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们每收集到一份文献,就送给毛泽东审核,审核完后直接送印刷厂排印。《六大以来》这本书共收入1928年6月至1941年11月的五百余份文件和电报,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多万字,大部分是中央秘书处材料科提供的,也就是当时的档案部门。《六大以来》产生的积极影响,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许多同志向中央建议,要求像编《六大以来》一样,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于是从1942年初,毛泽东在陶铸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开始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在文献取材上,《六大以来》汇集的主要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党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六大以前》则主要汇集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刊物上登载过的。由于时隔更为久远,《六大以前》收集到的文献比《六大以来》要少许多,共收文献184篇,按时间顺序,分上、下两册,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紧接着,毛泽东着手准备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选编一本关于党的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即《两条路线》。《两条路线》在取材上,只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有了前期编辑《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又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活动的开展,对党的历史上代表两条路线的文献可以比较明确地加以认定,因此《两条路线》的选目和编辑相对都比较容易。它所收录的137篇文献中,有106篇都选自《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按照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分期顺序进行编排。《两条路线》于1943年10月出版后,取代《六大以来》选集本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在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身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这三部历史文献集,对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当时,对这三部署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文献集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党书”。
解放后对档案工作的支持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更加关怀档案工作,本文就简单介绍几个中央档案馆老同志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1961年1月,中央档案馆征集组收到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写的《调查工作》原版本。裴桐同志派人送印刷厂铅印,并将铅印件送田家英转呈毛主席。毛泽东见到这个文件很高兴,立即把这个文件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印发时,毛泽东在文件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字,我们叫它‘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后来,把《调查工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重新出版,公开发行了。1962年5月,郭沫若同志写《喜读毛泽东的〈词六首〉》来中央档案馆使用了一些材料。郭沫若同志将写成的文章送请毛泽东审定,同时写了一段话:“我费了几天工夫,并且还靠着好几位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算把这六首词写作当时的情况弄出了一个初步的眉目。”毛泽东看了此文以后,将郭老这段话最后一句改成“是中央档案馆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1964年中央档案馆同志找到一篇毛泽东写的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毛泽东同志这种认真严肃考证文件的精神,热情赞扬中央档案馆的话语,不仅使当时的档案工作者很受鼓舞,也使我们新一代档案者备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