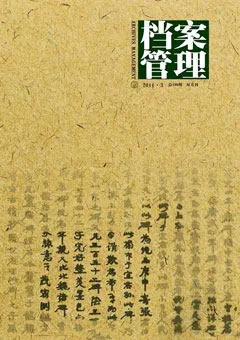低调的职业
说实话,我对日本电影向来不带有任何的好感,可能是民族观念在作祟,但还是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一部2008年出品的日本影片《入殓师》。关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知道这部电影以“黑马”的姿态获得了当年的“最佳外语片奖”,但始终提不起兴趣去看。昨天,终于在网上将这部影片完整地看了一遍。剧情不复杂,讲的是一位日本的大提琴手小林大悟由于乐团解散,与妻子回到家乡谋生,并误打误撞进入一家“为旅行者提供贴心服务”的“殡葬服务公司”,公司服务的项目就是为已亡人提供化妆和礼仪服务。故事以小林大悟参与的为社会不同角色入殓服务所发生的故事为主线,向观众交代了男主角对入殓师这项职业由胆怯到荣耀的心理变化历程,并折射出每个人对于死亡意义的不同理解。虽然,全片大部分都是用马友友的大提琴作为背景音乐,却丝毫没有带来悲伤和阴暗的感受,反而会对男主角的诙谐表演忍俊不禁。“人不论在世时犯过多大的罪过,我们都有责任让他体面地离开。”就是秉承着这样一种信念,小林大悟逐渐获得了妻子的理解、师傅的支持和家乡父老的尊重。这部温情而又不失幽默的写实电影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可以说,入殓师由于其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始终是一项低调的职业,但是,在这低调的背后却是对人性即将泯灭之前的一种追求,是一种对逝去之人的一种高调的尊重。正是秉着这种精神,小林和师傅的低调付出换来了小镇公众对他们默默的尊敬,在这份尊敬之中,体会到人类生活的真谛和对生命逝去的理解。不知编剧在构思“小林大悟”这个人物时,是否刻意用“小××大××”给主人公命名,而将“小人物大作为”这种理念传递给观影者。
观罢良久,不知不觉,回想起2008年在某档案论坛中发生的一起“写”案,其根由就是对档案职业与档案从业者的高调定位与低调认知之间的冲突。就观点论观点,我始终是支持“低调”一派的,因为,从我接触到档案学专业,到去专业实习基地实习,再到攻读档案学博士学位期间的兼职工作,档案职业和档案从业者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低调,我既没有看到某“中央级”媒体大书特书档案职业的崇高感,也没有看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追捧与宣传,档案职业和从业者给我的印象就是低调。但我们不能认定档案从业者所从事的工作是低调的,毕竟,流转于他们手上的物件都是社会机构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原始性记录,它们承载着社会发展的记忆、人类赖以维持的文化精神。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与之相反,虽然,我们手中握着社会的发展轨迹、人类文明的记忆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利器,但是,“门可罗雀”的门槛与“似于鸡肋”的职业环境始终难以支撑起档案职业“形而上”的定位,究其原因:“公众不买账”。档案学界研究再多的先进技术,科研部门搞出再多的应用软件,我想结果都是徒劳,因为,这只能从面子上为档案职业“涂脂抹粉”,提升档案职业的技术含量,但在实质上,特别是在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方面,只是“小动作”罢了。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贬低档案应用研究,更不是对当下档案学术研究和档案事业发展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我认为,社会公众对档案职业或档案从业者的认知不是通过对某人、某份档案的利用中得出的,反而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潜移默化不断积累起来的。正如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小林大悟并不是通过入殓师这个职业而被乡亲认可的,反而是因其在平常入殓服务中所一贯坚持的准则与对职业的尊重感油然而生的。因此,我觉得档案从业者的身份象征与社会角色分配不是用嘴说出来,也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在公众对档案职业的满足与认可之中。
我们需要“刘义权”式的英雄人物,因为,他的事迹使档案事业首次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被放大,但我们并不能把他当做神一样崇拜,进而把档案职业的社会认同无限地放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把他对档案职业的追求感融入每一位档案管理从业者的工作中,做好自己的基础工作、本职工作。人不是活在理想中,理想主义的“肥皂泡”终究会被现实之风所吹灭,对于档案职业的定位与档案从业者社会角色分配的认知,作为身在“此山”中的我们,要更理性、更切合实际,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档案事业的“真面目”。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