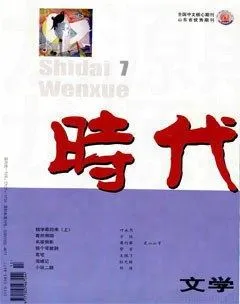我侧耳倾听土地胎音(组诗)
我侧耳倾听土地胎音
春天温馨的鼻息,轻轻亲吻山村门环和蜜蜂嘴唇。
大地僵硬的胸脯悄悄萌动。
我闭上眼睛,把耳朵贴上大地的胸膛。侧耳细听:
有一棵草,在冒芽的声音。
有一株树,在拔节的声音。
有一朵花,在绽放的声音。
有一条虫,在低吟的声音……
轻轻的,细细的,柔柔的,暖暖的,纯纯的。
来自天籁,来自土地与灵魂深处。
二十四节气,庄稼与野草一个生死轮回。
大地积蓄一冬水分、营养、心血与梦想。
翘首期待春天那一刻幸福的胎动。
那是春雷的种子,暴雨的激情,秋收的命令。
每一棵草,每一株树,每一朵花,每一条虫,
都是大地至亲至爱的圣婴。
或红或绿,或高或矮,或美或丑,或长寿或短命。
同宗同胞的兄弟姐妹,根与母亲的血脉攀结在一起。
乳香未散的蝴蝶,像久别的恋人栖落我的掌心,
预报春天降生的消息。
村庄味道
那是山石、溪水、阳光、泥土、树木、青草交融的味道,
那是报春花、桅子花、荞麦花、鸡冠花、苦菜花交杂的味道。
那是汗水的味道,牛马粪的味道。
那是在旱天祈雨、在雨中浇灌庄稼的味道。
那是在大雪天、用洁白的雪团搓揉冻疮的味道。
那是收获大豆、高粱、苞米、地瓜、花生、柴草的味道。
那是用新小麦摊的煎饼、蒸的白馒头的味道。
那是盖房娶亲、逢年过节,点燃鞭炮、开怀喝酒的味道。
乡村坑坑洼洼、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生生死死,
说不清、道不明其中的味道。
走进山石古老、土质薄瘠的偏僻乡村,
酸与甜,淡与咸,香与臭,苦与乐,美与丑,纯正地道。
还是那条故乡的山路
乡村独有的血脉,生命的藤蔓。
拴系一嘟噜一嘟噜山里人的梦。
脚步匆匆,走出山门,走回山寨。
那赶牛调,那叹息,那汗珠,那泪水,
甩进薄薄的土层,无影也无息。
庄稼越来越黄、越来越稀
路旁的野草、野花却越来越旺。
青蛙和其它动物早已远走他乡。
只有家雀留恋故土,依然在山路上觅食。
山路,游子思乡的一把琴,
轻轻一拨,就跌落一幕幕生死别离。
有时竟然变成祖辈缠在身上的粗重绳索,
挣脱竞需要花上几辈子。
山路依旧不动声色地蠕动在大山脊背上,
不知伸延到哪里,也不知伸展到何时!
那把已经睡着的老木犁
那副古老干瘦的身架,
翻耕粗糙原始的中国农业。
站成展览馆的一幅老照片,
依然弓着腰,
吱哟吱哟地响着。
这刺骨铭心的姿势。
一段岁月,一声喘息,一手老茧,
沿着柞木的犁耙,
真实地传来,
传遍我的手臂和沉重的记忆。
一垄薄地,一路汗水,一片庄稼,
养活农家清苦日子,
穿着褪色衣裳的山庄。
木犁依旧活在偏远的山乡,
庄稼不知收获多少年多少粒。
山民扔掉那把老木犁,
眉间依旧锁着一团愁。
山地与农民
不挪窝不改姓的薄山地,
养育这一族,
埋葬这一族。
从茅屋发出第一声啼哭,
就随父辈亲近土地。
云彩被一片片撕碎,
擦干脊背上的血渍与汗珠。
土地因汗水浸泡而松软,
农民因土地慷慨而生存。
双脚踏上这片山地,
鞋印重叠沉睡的辛酸。
双手插进潮湿的土壤,
触痛一声久远的长叹。
土地渐渐在农民的视野中模糊,
村庄在颂歌声中逐渐消失。
不知许若干年后,
有土地还是有农民,
只见父辈那满头白发,
依然粗壮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