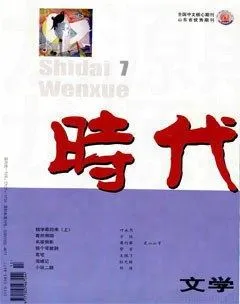文学经典的当代处境
摘要:在商品化的今天,昔日的文学经典陷入被不断异化的困境,以三种姿态(戏仿文本、花哨图像、学者的评书)呈现在大众面前。经典的创作者再不是固定的个体而是鱼龙混杂的大众,权威的经典开始放下架子,接受大众手术刀随心所欲的剪裁,成为迎合大众趣味的文化。这一切主宰了经典在当代的命运:它映照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为文化提供养分,为时代所需,同时遭受后现代文化的颠覆与拆解。为新的语境产生新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经典;消费文化;解构;权力;价值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阅读变为一种金钱和精神上的奢侈品,文学经典失去往日的魅力,逐渐改头换面,以一种被异化的姿态挤入读者的视野。
文学经典“妖魔化”的生存形态大体分为三种:一是古典作品幻化成当代戏仿文本,沿用原有叙事框架,消解其精神内涵,实现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和功利主义的创作心理。这些作品多属畅销书:《水煮三国》将三国故事与管理学策略相融合,变成一本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管理学教材。江南的《此间的少年》,维持了金庸小说里的基本人物关系。将人物移植到当代的大学校园,上演了爆笑的大学闹剧。
二是文学经典文本转化成眼花缭乱的视觉图像。集中体现为古典名著的翻拍。如新版《红楼梦》的拍摄,制作方利用受众的娱乐心理着意炒作。从选角到拍摄,文学失去其原有的精神内涵,变成市场化运作的商品和一场作秀所获得的商业利润。而大众关注的是文化事件而不是作品本身。《赤壁》似乎试图体现个人化的历史,然而特技,明星和外表的花哨并不能遮掩文化内涵的空虚和乏力,最终变作三国故事包装下的好莱坞“视听盛宴”。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热播的浙版《西游记》,现代流行语植入古典文本语境,令人啼笑皆非,孙悟空与妖精的床戏更是惹来非议。古典名著的原始魅力已丧失殆尽。
三是文学经典在“说书人的伎俩”中成就了学术的民俗话和大众化。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代表。学院派学者拥有对经典名著独特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体系,他们将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口述。传达给大众。从而实现了学术的通俗化。对受众而言,这是实现其知识填充的一种浅阅读。经典中的原义也许被曲解,但听众信以为真。经典通过“翻译”被大众理解。但学术界却不买账,认为同行歪曲原典,亵渎学术,实属商业行为。
在大众的视野里,经典已沦为一件商品。写作者利用它翻新花样,移入现代元素,妙用桥段,创作出博读者一笑的畅销书。出版商挖空心思,以“义务教育必读书目”的名头贩卖经典,满足了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功利之心。电影工作者更是巧立名目,力争将经典改编的面目全非,不惜一切代价混入色情,血腥,特技等桥段,构织成华丽的票房神话。矜持的经典被大众拆解地淋漓酣畅。甚嚣尘上掩盖了它的失语。学者陶东风将处于尴尬境地的文学经典命名为“大话文学”:“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有人不禁问,经典以如此的姿态存在,它究竟还有无价值?
也许该换一种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人们在质疑经典价值的同时也发现了另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当代文学与影像反反复复。毫无厌倦地与经典缠绕,纠结。从八十年代四大名著原汁原味的影像呈现,到九十年代末戏仿文本的大量畅销,再到当前影视剧、动画片的不断翻拍,经典读物的一版再版,当代文学与文化从经典中攫取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得以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经典的不衰也许意味着当前文化创新能力的衰竭,同时也意味着,时代需要经典。在这个喧嚣浮华的时代。经典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必然性,
经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饱经淘漉,已经凝固为一种传统的价值,内蕴着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文学对经典改头换面的纠缠,不仅为了利用其百看不厌的故事套路与情节原型,也暗含着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以国学经典为例,在这个快餐式阅读盛行的当下,能够潜心专注阅读国学原典的人越来越少。于是,艰深枯燥的老庄孔孟换了一种姿态,以白话形式展现给少儿读者,以拉家常讲故事的方式呈现于电视荧屏,甚至。有导演挖空心思拍了一部《孔子》,生硬编了一套并不好听的故事,来宣传儒学教化。学者们哀叹传统的断裂。但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以浅学术的形式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儒家的仁爱礼仪,温柔敦厚的人格修养,道家自由而无功利的处世态度。纷纷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精华与思想宝藏,它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品质,也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养分。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便是要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中探究民族发展与人类生存之谜。
既然我们的民族需要经典来维系断裂的传统,追溯集体的文化记忆。而当代文学又不断地从经典中汲取文化营养,弥补疲软的创造力,缘何经典难以维持原貌,尊严扫地,被迫变身?这种文化现象与后现代语境紧密相关。自古以来,经典与权威同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经典”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我们面对的经典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的文学,历经时间筛洗,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而当代是一个充满解构与反讽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去传统。去中心,去权威,颠覆和拆解掉最后的神圣与价值。网络上对经典影片的恶搞,凸显了草根网民的戏谑心理。在身份隐匿人人平等且自由进出的网络之上,一切正统文化都可以被嘲笑玩弄,一切权威都失去话语权力,经典文学也变成一场七嘴八舌任意消解的无比喧腾的狂欢节目。经典在被确定的过程中经历了起起伏伏的筛选,它最终成为一种严肃而不可撼动的权力话语,对经典的消解乃是对权力的消解,从而达到另一种权力的建构。从文学经典本身存在的悖论来讲,它“一旦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西游记》的变身花样最多。在《西游记》中,唐僧处于师徒四人中的至尊,徒弟对他言听计从,就算是反叛自由无法无天的孙悟空也需对他毕恭毕敬。这是传统的尊师重教思想。而在八十年代周星驰改编的电影《大话西游》中,唐僧变得如妇人般唠唠叨叨惹人讨厌,孙悟空形容其“像个苍蝇嗡嗡嗡”,出场便要杀了他。对师父的挪榆不仅是对自古师道的反叛,也是对佛家思想的解构。《西游记》中的神灵佛祖都高高在上,一本正经,道貌岸然,而在电影中,菩提老祖变成一个滑稽软弱遭人戏弄的狼狈神仙。等级观念遭到消解,万物生灵皆平等。在原著中,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后跟随唐僧西天取经,算是走上正路,斩妖除虎。最终修成正果,皈依佛门,自由反叛的天性被驯服,达成时秩序与正统的认同。而在电影的“大话”叙事中,主人公的命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悟空拒绝西天取经,欲杀了唐僧。观音赐他五百年后重新做人,却早已规划好他的人生,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亦不敢相信自己的前世真相。他成为一个遭命运捉弄陷入困境的生命个体,在命中注定不能成真的姻缘中痛苦挣扎。这样的叙事自然有了一种现代性的追求。在兮何在的小说《悟空传》里,孙悟空更是陷入历史与现实混淆。过去与虚构真假难辨的窘境,神终究是掌握了话语权,人是话语的追随者,再神勇的齐天大圣也躲不过命运的捉弄。那最经典的一句“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是被命运围困的个人对自由与主体性的终极追求。
如此经典变身并非恶搞与戏谑,其精神性也大于纯商业性,它凸显了一种对现代性的自觉追求。经典应时代而生。而产生经典的时代已久远,经典所阐释的传统意义已无法满足新的语境与时代,新的意义亟待产生。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对待经典的态度不免偏激,但他们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背叛是出于启蒙救亡的现代性追求。在消费语境到来的新时期,尘封的经典必须接受流动的读者和现代性的阐释。经典被扒下旧棉袄,套上新外表。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上演了贾府的兴衰与女儿国的悲欢离合。在原著流传的一百多年,对其解读与改写层出不穷。五四时期,蔡元培以“反清复明”的思想解读它暗藏的谜语,胡适以“自传”考证曹家的兴衰。四十年代以后。《红楼梦》被罩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把它引申为一种封建家庭的权力之争。八十年代后思想解放,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对《红楼梦》的解读多从人性人情的角度,红学遍地开花,各成一家。二〇〇七年的舞台剧《红楼梦》从构思,剧情,舞台设计都颇具现代意味。在人物安排上,改变了原著中宝黛为主角的格局,王夫人和薛姨妈一跃成为中心人物。这一创意来自于对经典新的阐释。在剧中,王夫人实际掌控着贾府的权力,成为一切悲剧的根源。全剧采取倒叙手法,从贾宝玉的灵魂回到残破败落的大观园开始叙述,三个宝玉穿插其中(精神世界的宝玉,现实世界的Xu26OtjI1nMGwufFCUcvT6biLZCK9TQ/KjT+tWxTWHU=宝玉,老年宝玉),舞台设计成一个坍塌的大观园屋顶,所有演员在上面表演。这些后现代意味的元素呈现出文本的开放性,意向性与阐释空间的无穷尽,颇具时代感。经典文本封闭的叙事空间被打通,意义得以重新阐释。
在消费时代,经典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不得已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而经典的创作者再不是固定的个体而是鱼龙混杂的大众,权威的经典开始放下架子,接受大众手术刀随心所欲的剪裁,成为迎合大众趣味的文化。大众审美的畸形也拉扯着经典的体态:对色情、肉欲、暴力的沉迷,拒绝思想与深度,热衷于时尚美与装饰美。寻求感官刺激与廉价幽默……这一切主宰了经典在当代的命运:它映照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为文化提供养分,为时代所需,同时遭受后现代文化的颠覆与拆解。为新的语境产生新的意义。经典的意义不停流动,无限开放,出入自由随意建构意义的读者将其串成一串串移动的能指。经典必将存在,并永无停歇地被异化,成为一个参照传统与现代文化景观的哈哈镜。
参考文献:
[1]陶东风,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90页。
[2]季广茂,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0卷第6期,第8页。
[3][4]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第206~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