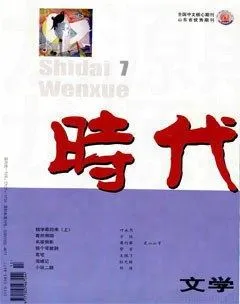向黎与我
要把朋友落实在纸上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等到你真的要去写一个朋友,而且是一位很好的异性朋友时,似乎就更难了。潘向黎之对于我,似乎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太熟了,往往就成了空气,无处不在,但你却无从下“手”,不是要写这篇文章,也就根本想不到“下手”——好朋友根本不是用来写的。
报刊、网络上写向黎的文章不少,说她这个人,漂亮、优雅、时尚……甚至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牌子的首饰。等等——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些都很重要;说她的作品,由散文而小说,叙写世事,如何如何洞察人性,怎么怎么理解女性的身心,文字智性而优美、洒脱而又蕴藉——对于一个作家。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想想也是啊,说的都对啊。可作为她的朋友,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么理性地去概括她。朋友相处时间长了,甚至根本就想不到去评价他(她)。
向黎来了南京,或者我去了上海。很自然的就开开心心地见面了,有时还是两个家庭混在一起。吃喝聊天,张家事李家事、张三事李四事,没什么顾忌,不留心眼。这么多年。好像就没有正经地聊过我们从事的行当。聚散都极自然、坦然,然后就是下一次见面,从不厌烦。
我觉得,这已经是很高的友谊的境界了。不是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吗。这就是投机。
所谓默契,所谓原则,所谓人品,甚至人世间的大是大非,其实都在日常里,往往没什么。道理。好讲的。
我和向黎的交往倒是始于文字。大概是九十年代末,我出了一本随笔集《红颜挽歌》。不久,我偶然读到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一副长者的口吻。因她用的是笔名,我后来才从编辑那儿知道,作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潘向黎。真是受宠若惊!据说潘大作家在那以前是从不给人写书评的。此次破例,记忆中后来见面时向黎说了两条理由:一是我在该书的作者简介中。大大方方地写明了自己“乡下人”的出身与经历。没像有些人那样绝口不提或者遮遮掩掩,对生活的挫折也没多少抱怨;二是我在书中或隐或现的对女性的态度,好像是说还比较端正。因了这本书,向黎判我为“新好男人”,实有“妄断”之嫌;后来有朋友说。这篇书评向黎无意间帮我做了一次艺术的征婚广告。说是“无意”,因为那时我们还尚未谋面,她也不知道那时的我尚未婚配。
何时何地首次“会见”,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后来是见得越来越多。我自然就很认真地去找她的作品读,并且尽职尽守地向她约稿。人、文互证,哪个敢说我对她不了解?我们相处得很好,谁能说没它的道理?过去,人们谈到友谊时,必说“世界观”、“人生观”为基础,如今听不到这样的说道了。但它们无疑还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是我们不用“世界观”、“人生观”这些名词称呼它们罢了。所谓人生,说白了,就是处理各种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人生也不过是在努力摆正这些关系。所谓人生的“清贞”,就是不管如何背运,不管遇到多少挫折、不公、甚至磨难,都不糟踏这些关系。向黎的最新长篇《穿心莲》里的女主人公在热恋的情人不辞而别,在无望的等待中忍受巨大的身心痛苦的同时。仍然能在行动上、在心理情感上既不“糟踏”别人也不“糟踏”自己,就是这份“清贞”。上帝仅造了男女两个性别,无论男人女人,我们根本就没有互相作践的资本。
人到中年,我们每个人都难免经历许多的人和事。因此,有的愤世嫉俗,有的自甘沉沦,有些人清醒地把人和事做最商业化的处理。向黎都不是。我是欣赏向黎言行之间流露出的那种对人对事的温暖态度,不会太热也不会由温而冷,而且,以我的感觉和判断,向黎的这种态度已不会改变。我们见了太多的改变——由“单纯”而变为不“纯洁”。有些词我们常常用错,主要还不是语法错误,比如“纯洁”与“单纯”。儿童天真无邪、不晓世事、没有城府、两小无猜。那是“单纯”,还不是“纯洁”。阅尽人世沧桑,历尽繁华和苦难,返璞归真,铅华洗尽,尘埃落定,爱依然溢满胸襟,那才是“纯洁”。单纯到底,必是纯洁。由单纯而纯洁,才是“美”,才是“帅”!
记得向黎有次开玩笑,说她的这几个男性死党。根本就不把她当女人看!
其实……
有一次我到文汇新民楼下等她,她一袭长裙,略施粉黛,款款从楼上下来,我当时真有“惊艳”之感。我倒是没什么“私”心。作为一个男人,我感到欣慰。为这世界上的男女关系感到庆幸:这世界上还有好女人j哪怕仅仅是做普通的朋友,至少我们这些老爷们就不会像有些女性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那样反骂女人,男人的心理世界因此也就不那么荒凉。
去年,向黎考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丁帆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跟包括我在内的丁门弟子成了一个师门的兄弟姐妹。自自然然地就觉得亲,是自家人的感觉,我就免不了常常想着怎么去维护她——这就有点私心了。再公开发表地说她的好话,我还真有点不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