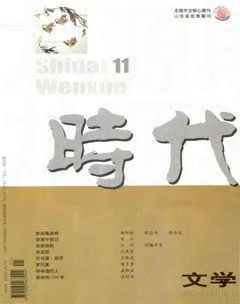在烟雾中埋首前行
读凸凹的文字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也惭愧了差不多二十年。
可能是出身相类,骨子里有一脉相承的因袭吧,第一次见凸凹的文字便毫无理由地喜欢,感觉中,他独特的文字给我的影响要甚于很多名家。便自然而然地要引为知己加以膜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通过信,他给我寄过书。1993年7月,我的散文《夫妻作坊》和他的一组散文同在《青年文学》散文专号上发表,便私以为和凸凹是有些个小小缘分的。
凸凹风光无限,文场得意,仕途顺遂。他的官越做越大,文集也接连出版。他每出一本集子,我都到处寻找,找不到就打电话朝他要。直到他第一本长篇《慢慢呻吟》出版,我致电索要,不可得。后来再没联系。那些年,自己虽然还在写,但文字越写越少,格局也越来越小,自尊心却出奇地膨胀了。再加之那几年谋生的任务日重,生存的艰难凸显,文场上鱼龙混杂,明枪暗箭亦让人气短,便意气用事,想躲文学这个圈子远点,从此不读,不想,不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差不多十年后我才重新拿起笔。我用十年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学不是用来意气用事的,文学对于自己是呼吸之于生命般的自然需要。对照凸凹,反观自己,更觉得凸凹步伐坚定的可贵。在我们左右徘徊之际,凸凹已早早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他自成一格的小说和随笔已成了文坛一道炫目的风景,让人只有气馁和远观的份儿了。
去年金秋,北京作家协会组织部分作家去天津开研讨会,在作协楼下等车时,我看到一个背双肩背包,拉大拉杆箱的中年汉子立在花树边歇脚抽烟,觉得他很像凸凹,一问,果然是。
乍见凸凹,心下未免遗憾。觉得他不是想象中的样子。想象中的凸凹该是个性情中的汉子,敢说敢闹,敢喝敢醉,有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勇,也有谈吐狂放,挥洒不羁的个性。可面前的凸凹,沉默,寡语,淡漠,你和他认真说话,他却在认真地吃他的纸烟,是个嗜烟如命家伙。交谈中的凸凹出语短促,声带傲慢,言谈间有几分官场熏染的习气,他谈兴不浓,我也兴味寡然。所以和凸凹的第一面就这样失之交臂了。
后来是去冬的一个中午,我正昏天黑地地写小说,突接一个电话,竟是凸凹。说要和祝勇先生来平谷找我聊聊。再后来,已是今年的初春,他来电向我问付秀莹的电话。那天,外面大风呼啸,手机信号不好,加之他独特的粗短口音,我听得时有恍惚。但他突然的一句话,我却听得明明白白。凸凹说,“小兄弟对文学的虔诚真让我敬重!”初始没觉得这话怎样,过后咀嚼,竟差点落下泪来。我是个从来不愿喊苦和说累的人,他的这话让我顿感为文和办刊的苦楚和艰辛。就像孤独远行者于茫茫夜路听到的一句轻声问候,陌生,却是长长久久的温暖。
之后不久,凸凹如约写来了他给杂志的“寄语”。寄语里,他把《天天》说成是“我们的园地”,这就让我们除温暖之外,还收获了一份真实的感动和力量,觉得凸凹是把文学爱到了骨子里的人。这样的人,时风之下已是稀缺得紧了,因而更值得我们敬重。
杂志要配照片发一篇作家印象记。我知道给他写印象的人不少,又多是在文坛享有盛名的人物,便打电话给他,让他找一篇现成的给我。他却坚持让我来写。踌躇半天,还是答应了,只是不知见了一面的凸凹,我该怎么来下笔?细想,印象中的凸凹,最深的居然是他贪婪抽烟的表情,在花树旁,在走廊里,还有他故意选择和刘晓川先生一个房间,目的也是为了抽烟方便……除了烟,还有他趁开会前给大家签名送书的情景,他俯下身子认真给每一个作家签名的样子……粗壮魁梧的凸凹,两鬓竟有白发森森然亮着,触目惊心……后来我曾向他感慨,说你可显老多了。凸凹说快五十的人了,也该老了。不知为什么,听他说这话我心里会不好受,会想到小他几岁的自己,头上芜杂丛生的白发不也如野草般不可自拔吗?就不免悲从心来。知道文学是个极易催人老的行当,为这个,我们老了自己,值当吗?
也许在我停笔自问的时候,凸凹又已经在路上了,他埋首前行的样子,分明有些奋不顾身,我一点都不奇怪,凸凹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只是奇怪,他偶尔停下来时会不会还有吸食鸦片般抽烟陶醉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