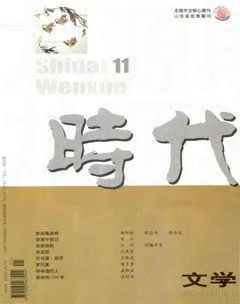学者散文中的个人体验
摘要:作者的个人体验及其表达、真切的内容、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和审美诉求是学者散文成功的主要原因。学者散文的论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的经验教训,批评者要尊重学者的个人体验及其表达,更多地在学理层面上开展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学者应该在创作上避免这三个方面的价值缺失,共同促进学者散文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学者散文;个人体验;真切;形而上;审美
学者散文不同于文人散文,它融入了学者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独特的个人感性表达。学者散文长盛不衰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作者本人这种独特的个人体验表达。某一个重要历史时段中的事件、人物,某一个重要命题符号,从学者们异彩纷呈的笔端流露出来,渗透着各不相同的观察、思考的思想内涵,从不同程度上引起读者的思考共鸣。同时,又以其严谨的笔法,多样的表达手法——或隐晦,或直露,或嘲讽,或首肯,给读者以艺术美感享受。可以说,学者散文作为众声喧哗中的一个强音,作者个人体验及其表达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存在很多的争论,焦点集中于作者个人体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如何把握这两个方面,关系到学者散文的成败和对其进行批评和争论的意义。
一
作家的学者身份以及他们独特的理性思考和个人情感表达方式,是学者散文区别于其它类型散文的最独特之处。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陈平原、周国平等学者的散文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近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学者散文领域仍笔耕不辍,同时,一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如金开诚、张颐武等又恰逢文化热潮,得天独厚地驰骋于此,赢来了阵阵喝彩。究其原因,学者散文中个人体验的内容和各不相同的表达方式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迷失自我、缺乏个人体验的写作所造成的千人一面的雷同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而就在那专制阴云密布、意识形态戕害个性的艰难环境中,仍有“潜在写作”的灵光隐现。作者们“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 [1]这其中,从事美术创作的丰子恺的超脱随笔,改行于服饰研究的沈从文的殷殷家书,都传达出他们深刻的个人体验,这也是他们的作品直至今日生命力犹存的个中之因。待到文学观念得以修正,文学重新回到文学本身,文艺作品重新重视个人体验的呼声得到了广泛地回应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风潮骤起,学者们深厚的文化功底,对天、地、人的独特深刻的思考,无不使学者散文长风破浪、硕果累累。
综观这些散文作品,真实——建立在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上的真实经历、真实感受、真实思考,是这些作品的灵魂,也是击中读者眼球的那束最耀眼的强光。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造作,有的只是灵魂的告白。就拿季羡林先生的散文而言,乐黛云先生用“真情、真思、真美” [2]来评价,可谓切中肯綮。有两篇文章对照来读十分有趣:《我和北大》和《我看北大》。在《我看北大》里,先生表达的是一个“老北大”对北大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的殷切期望,很符合北大百年校庆的气氛。但老先生笔锋一转:“我希望国家教委和北大党政领导在待遇方面多向这三个系(中文、历史、哲学)倾斜一些”,不惜冒败兴之嫌,发出自己内心的真心呼吁。而在《我和北大》里,痛切地指出自己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则是和北大剪不断的复杂情感的真实表露。这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和对象明显不同,但不管是“要我写”,还是“我要写”,对北大的真情却是一以贯之的。
雷达很佩服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特意写下《我喜欢徐光耀》一文,声称“我喜欢的其实是他的人格和人品”——“捍卫真理的刚毅” [3]。徐光耀对“反右”引蛇出洞的条分缕析的揭露和自己血泪斑斑的心路历程的描绘,是感动雷达先生的最主要原因。作为学者的雷达对文人散文的强烈共鸣,也从另一方面透射出一个真谛:真实不仅是文人散文的生命,更是学者散文的灵魂。
二
正如梁凤仪的财经小说,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一样,学者散文说到底也是学者的一种“行业写作”。取得成功的作者们大多在文化或与此相关的领域积累了相当厚实的人生体验。对他们来说,对文化与人的关系进行透彻地思考分析就成为他们散文创作的基础。诚然,写出行业内幕能满足读者了解和窥视这些行业的欲望,但仅仅满足“写出行业内幕的东西,有好的素材和好看的故事” [4]就可以取得读者的拈花一笑,这是对读者的多层面阅读和多层面的读者的有意漠视。所以,停留在个人体验直露的表白上,还只是形而下的自然复述,学者散文在表达这些个人体验的时候采用了形而上的方式并注意避免审美上的欠缺,达到了既叫座又叫好。
曹文轩先生在这方面有精彩的论述,他说:“对形而下的关注,却往往出自政治的、伦理的或各种各样现实功利的动机,它并无探索本质从而走入本质的意识,拘住注意力的是一时一地、一家一国的‘当前的’、‘具体的’问题。由此种关注而获得的认识,往往只能供一时一地、一家一国的特定的人或人群所理解,而不能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当我们将‘走向形而上’一说用于概括文学的一个现象时我们会毫不受阻碍、心领神会地感觉到它意味着什么:文学在背弃实用主义哲学,在摆脱功利主义的注视,在越过实在时空而去超时空领域捕捉所谓永恒,在抛却充塞于我们视野的社会景象与日常生活景象,而努力在它们深远的背后发现目光初不能达、力初不能及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景象” [5]。周国平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专业是哲学,所写的散文被称为“哲理散文”,一入手便由“器”入“道”,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精鹜八极,贯穿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他坦言:“在我的价值表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我切身的经历和体验,第二是我对它们的理性思考,第三才是我在学术上或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6]。再看余秋雨的名篇《风雨天一阁》、《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交融了“人、历史、自然混沌”,以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典雅的行文风格感动读者。读他的散文,如同聆听杨洪基的歌咏一样厚重、悠扬而饱含激情,达到了周国平所谓的三种价值的统一和契合,就连余秋雨个人也不无得意地说过:“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韵致” [7]。
但学者散文在表达个人体验上很容易自然而然地陷入一个误区——沉溺于专业知识的阐述,以至把散文写成学术论文。常常看到,浩淼二十四史中的一个用语(绝非一般读者所知)、一个掌故,往往成为立论的酵母。史料的勾陈本无可厚非,但考虑到散文的特点、接受的范围,即使是圈内人士也有学术方向的差异,何况于面对大量的圈外读者,行文中作简明的介绍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把酵母当作面粉,作者洋洋洒洒、滔滔不绝、高屋建瓴,读者如坠云端、雾水蒙蒙,即使立论如何高妙,行文如何优美,也定是酸得不能下咽。所以有论者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学者散文里。学者、学者品格、学者风范,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种‘潜在’和‘隐在’,只是一种‘内功’,都不应该直接地、毫无遮挡地出现在散文作品之表” [8]。
三
近年来,学者散文在风行一时的同时,也遭到了一系列的诘难,关于学者散文的论争可谓此消彼长。撇开一些技术上的不辩之症(错字,错语等硬伤)和文坛意气之争外,论争在本质上集中于文章作者个人体验的真实度以及表达方式上。
孟子的“知人论世”,完全可以用于学者散文的接受上。一方面,读者可以通过学者的“论世”,了解学者其人;另一方面,通过了解学者本人,了解其“论世”的深度。沸沸扬扬的“余秋雨忏悔”事件,除了某些媒体的炒作,也不是“凉风起天末”,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如前所述,余秋雨的散文达到了学者散文的上品层面。但是,读得多了,文章的瑕疵也就暴露出来,如篇章的雷同等等,进而人们自然想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于是,对于这些瑕疵也就谅解起来——毕竟余秋雨侵淫戏剧多年,戏剧的因子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文风。另一批有心人却大哗,对于余秋雨没有披露自己“文革”的真实表现大为不满。先是要求余秋雨忏悔,又是质疑他当歌手大奖赛的评委妥当与否,以至对簿公堂。其实,这样的“论世”未免偏颇,对余秋雨本人也不公平。诚然,余秋雨的那段历史是真实的,但即使是有过失当的表现,人无完人,谁又能保证自己,包括那些批余者本人是否也能做到刀枪不入,成为一个完人呢?余秋雨的文章是有缺陷,但迄今为止,横看成岭侧成峰,一家之言,大家评说,完美无瑕的至文还未见一篇,何况余秋雨还在行走,在发展。余秋雨评说歌手,是有己所欲施于人的尴尬。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大奖赛)中普通的一员,处其位而谋其政,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已。况且这样的尴尬其他评委(包括尹鸿)也都遭遇过,何止余秋雨一人!
从学理上讲,要求学者散文具有真实、形而上和审美的诉求,同样也要求读者,特别是批评者尊重作者的个人体验及其表达。要有理性的接受,而不是专拣名人批、逮谁宰谁的感性膨胀。我们已经习惯于尊重作者们——“每一颗露珠都在太阳下闪耀着不同的光芒”,还要习惯于尊重作者们的个人体验--已成文本的或未成文本的。对于学者们来说,已经取得的成就是百尺竿头的坚实基础,真切、美感的个人体验表达是时代的财富,读者惟有期待更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1]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