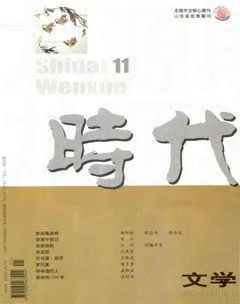情义凸凹
一
结识凸凹先生,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走进了凸凹方正的院落。落座后,没有多余的寒暄,他便展开了我随身携带的稿件。审读之际,表情不是我预见的那样,眉头紧锁或者微微含笑,有的只是全身心的投入。很快读罢,他说:“这些题材要是我写,可以减去一半文字。”这一点评,切中要害。正如高明的中医,上手就号准了脉象。
我感到,凸凹是一个可以信服的先生。
因为有了基本的信任,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试探着说了出来。说到稿子的质量,求教先生也还顺畅;想到请求先生荐稿,就先自惭愧,话语也在吞吐之间。事到如今,也不清楚是否表明了我的那层用意。尽管如此,先生还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不做躲闪,直截了当地说:“我通常不替人推荐稿子,也只能掏给你一些干货。”所谓干货,就是指实在的文学引领。先生的意思明白不过:荐稿,没门儿。我这样认为,求人和求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求教是学问层面的行为,虚心、好学、上进,值得敬重与褒奖。求人有太多的功利意味,有弄巧的成分存在。参与之人,难为情也难免。所以,先生的愿与不愿便在情在理了。于是,我掘弃了荐稿的想法,踏踏实实地随先生学习写作。
这以后,总有或长或短的稿件请教先生。从先生会心的微笑中,我感到自己的文章有些上路了。
意外的是,先生竟然做出一个另我瞠目的决定。他突然打电话来,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说是他的一本散文集《无言的爱情》(1998年8月,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得喝上两杯。那天的阳光金灿灿的,透着暖意与温情,很配我俩的心境。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坐上了良乡西街一处临街的酒馆。我兴奋地翻阅他的新版文集《无言的爱情》,他则很入境地审看我的文稿《不再喝彩》。读罢,他“叭”地一拍酒桌。好,这篇稿子我替你发了,再配以一篇评论。很快,散文《不再喝彩》就在京城颇有影响的《京郊日报》上刊发了,同版发表的还有凸凹的一篇点化金石的短篇评论《为〈不再喝彩〉喝彩》。这一天是1998年9月10日,是先生给予我的最好礼物。
至此,我终于明白凸凹先生荐稿的用心。他的荐与不荐,绝谈不上“朝令夕改”的善变,更与“说了不算”的偏执毫不搭界。如果你只是这样想想,都是对他的不够敬重。他之不荐,是文章本身尚未达到发表水准,唐突举荐会降低文学的格调,玷污创作的神圣。他之所荐,是稿子本身已然达到刊发标准,甭说不荐,即便拖延,他都会觉得是对于文学的不够尊重。
所以,对于文学的情感态度,凸凹先生是清醒的。
凸凹敬重文学。
我敬重凸凹。
二
孝敬若是由着心性就不委屈,就心甘情愿。
曾经读过凸凹先生的两篇散文:一篇是《对酌》,另一篇是《难忘父亲两支烟》。前者,是垭里人父子情深的感性呈现——
喝到这一刻,父子遂失了辈分之囿:面对那满坛的醇酒,就只有两条汉子,就要喝出个高低——父亲不让儿子,小的也不服老的。就我喝你喝,你喝我喝,喝成个昏天黑地。这叫豪饮。
当老的喝得眼皮已紧紧地阖上,还准确地端起桌上的酒杯:“这杯是俺的。”
老的摆了摆手:“咱哥俩谁跟谁哩?”少的一饮而尽:“不,你是俺爹!”即便是醉得要趴下了,但他心里明白。……(凸凹《对酌》)
这样一对酒父子,岂是一句真情了得。这份“没大没小”的至深情谊,成为凸凹先生日后孝敬老人的内在情感动力。后者,是面对人生命运的困厄,父子一起做无为而绝决的抵御。先生经过求学走出垭里的柔弱理想,被冷硬的现实无情地击打。受伤的不仅是凸凹,还有木讷温厚的父亲。然而,父亲温暖的指掌,却先抚慰在儿子的伤处——
“孩子,抽口烟吗?”父亲突然说。
我登时一惊,抬头看时,手里果然就擎着一支纸烟。我怔怔地望着父亲,在瞬间,他变得极陌生。
……
“就抽口吧。”父亲执拗地将烟递过来……(凸凹《难忘父亲两支烟》)
所以,旁人的孝敬,多的是一份责任与道义 ,是做给别人看的,多少有点做秀味道;凸凹先生的孝敬,受内心的驱使,是做给自己的,与旁人无关。
于是凸凹的孝敬,就实在,就细微。
数年前,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在良乡医院与凸凹先生偶然相遇。
当时的天气状况,前去的目的,皆已记忆模糊。我却清晰记得,凸凹用一辆双轮车推着一位重病的老人。老人我是认识的,在先生的家里见过,是他一向敬重的父亲。只是被病情折磨得脱了相,显得陌生。凸凹疲惫地推着老人,凝重地一步一步走来。一辆双轮车,将这对相知的父子牢牢地联系着。说它牢固,是因为这种联系有着金属般的质地。坚固中蕴含着刻骨的亲情,暖透心肺。我为之动容,不禁想到“父子对酌”,想到“父亲的两支烟”。我分明看到,凸凹半旧的军用棉衣是敞开的。或许是急走热了身子,或许根本没顾得上扣紧。双轮车是三面围挡的那种。虽然如此,老人的身前身后还是让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上面一顶棉帽暖暖地罩着整个头部。
我和先生轻手轻脚地把老人家料理妥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想到,病床上的老人突然粗重地喘息起来。我们本就悬着的心,又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我不知所措之际,凸凹已经将老人的上身托起,顺手把一床棉被垫在老人的身后。之后,轻轻地拍抚着老人的后背。在缓慢拍抚中,老人的喘息渐渐平稳。整个过程,先生动作轻柔得像个女儿。父子连心,这话真是。
终日卧床,老人的胡须零乱,缺乏打理。面容不洁,是凸凹不能忍受的。他将水温调到适中,用毛巾敷热老人的面颊,再涂满泡沫,用剃须刀一下一下小心刮拭。久病的老人,气息自然污浊难耐,却是老爸此刻的真实味道。凸凹不躲不闪,安然地承受。意念中,那是老酒、纸烟的气味。刮洗干净,老人的精气神儿徒然增加许多。在先生的心里,敬着的还有父亲的尊严。
凸凹的孝敬,本分、情义。
三
印象中,凸凹的朋友众多。
赵日升——
赵日升,是凸凹景仰的老人。
最早认识赵日升,是在房山区文联成立的大会上。就是这次大会,凸凹先生始任房山区文联主席。以后,房山的文学活动很多。每有活动,他都在特别邀请之列。据说,他从不需要车子接送,只是自己坐公交车或者打的来去。每次集会,都被请上贵宾席位,他不做过多推辞,便安然就坐。需要发言,凸凹等文化界领导必要恳请。他也会作一段简短、质朴的讲话,内容总能一语中的。会上会下,杯盏之间,凸凹先生都称他赵老师。感觉中,一声“赵老师”有着特别的分量。先生,对赵老师有着父亲般的敬重。
我很是不解:一个身量不算高,花白头发的质朴老人而已,何以至此?
这一疑惑,到2004年7月方才得解。可惜,这时赵老(赵日升)已经辞世。凸凹一篇涕泪文章《心碑青苍》,使我深刻认识了赵老。两册《房山文艺》,催生了少年凸凹的文学梦想;一份《青年文学》,丰满了凸凹的文学羽翼;一趟编辑部之行,凸凹享受到父爱的关照、宽容与鼓励;一句“凸凹,我敬重你”,成为凸凹长篇小说创作的起点;一次春节聚首,却道出了赵老对房山、对文学的无尽眷恋。
是对赵老的景仰,更是对文学的景仰。
凸凹是对的。
真心景仰,无愧于心。
张振乾——
1991年10月至1992年4月间,有两部文学作品问世。一部是小说集《两个人的故事》,一部是散文集《两个人的风景》。两部合集的作者,史长义(凸凹)、张振乾。这期间,正是两个人的文学起步时期,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难想像,史长义、张振乾有过一段共患难的日子。
我曾与张振乾有过一面之缘,有幸目睹了他们的交往。
一个夏日的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当时,我和凸凹先生几个人正在他西北关的院子里闲聊。突然,墙外一声呼唤:“长义。”院内立即一声回应:“老张”。没有任何悬念,果然是张振乾。没有心理准备,呼应竟然及时准确,不是多年的交往,便不能想像。也算是心灵感应,常有类似的情景:楼下一旦传来或疾或缓、或轻或重的脚步声,必有一家的楼门为其洞开。换句话说,是不是家里人,听脚步声音没错儿。由此可见,对于凸凹来说,老张不是外人。张振乾也不外道,走进院来没等让座,自己找凳先坐下了。不是自家兄弟,如此不见外做得到吗?
难怪凸凹先生说,我和张姓、马姓、阎姓有缘。张姓之中,就有张振乾。
2010年端午节,在良乡功德福饭庄和凸凹先生小聚。很准时,外面传来凸凹爽朗的说笑声。我正要迎出门去,一前一后推让着进来两位陌生人。显见得,是先生尊重的朋友。
我来介绍,凸凹爽快地说。这位是骆总,这位是杨总。搞建筑的,他还找补了一句。我趁机打量一番:骆总,四十多岁年龄。面色黑红且粗糙,一件普通的白色短袖衫敞着怀。杨总,五十上下年纪。花白短发,一件准军用短袖衫同样敞开着。两位老总,真不讲究。哪有老总派头,真人不露相吧。我心里直犯嘀咕。
两瓶烧酒下肚,彼此熟络许多,便将一些家务琐事与之求教。其时,正想在老家的宅基之上置些房产。建筑诸事,对我来说极不在行。材料、工期、质量,弄得两位老总有些慌乱。慌乱中,骆总竟把这件事情推给了凸凹先生。一个内行把事儿推给一个外行,凭什么?除非,他也不是行家。
第三瓶烧酒启开,酒继续喝。话题转移到扑克上面,评价的是打牌的技艺。骆总面对凸凹,你的牌出得也不怎么的,瘾还不小。杨总回敬说,还不是你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先生好玩两把扑克这我知道,他离不开那些牌友我也知道。
牌友偏称老总,真有意思。
凸凹先生曾经调侃:我的朋友,不是艺术家就是老总。哈哈!
静心体察,凸凹是有道理的——
现代人热衷于功名、利禄,多凭此权衡人之价值所在,据此施以“青眼”和“白眼”。从这种意义上说,凸凹先生“封”其朋友为艺术家,为老总,迎合的是世俗心态,是入世的。从入世的指归上讲,凸凹先生迎合世俗心态,是为朋友争取一个“青眼”,是对朋友尊严的基本维护,又是出世的。
所以,凸凹之交友,是入世更是出世。
凸凹说,交朋友,便是交生活,交善性的悟道。
先生的朋友,岂能不多。
四
几年前,文化圈内一位熟识的朋友结婚,我被邀去喝喜酒。
酒席设置在酒店的雅间,敬酒就得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分敬。新人一轮酒敬过之后,朋友间自然也需敬一敬,这是酒桌上的规矩。这样昭示着朋友之间的尊重,也能作些相应的情感沟通,大家乐此不疲。
一对新人敬酒过罢,凸凹先生就适时地出现了。近旁的董华老师幽默地说,你亲师傅来了。先生逐一敬过之后,我迅即端起酒杯。来,跟我亲师傅喝一杯。酒桌上一下热闹起来。大伙你敬我喝,你喝我敬。亲近许多,也温馨许多。不成想,我的意识之中居然出现了亲情幻觉。年长的置换成为叔叔、大伯,年少的变换成为堂兄、堂弟。这份亲情,令我迷醉得飘飘然。
先生有这样的习惯:在相对熟悉的圈内,与我陌生的朋友他必要“师叔”“师伯”地一一介绍。我也必然端起酒杯,“师伯”“师叔”地一路敬过去。其中的真诚自不必说,因为我享受的是亲情待遇。
慢慢地,我们这对师徒的亲情味道愈加丰厚。
在散文《赠书小记》中,先生真实地记录了他的赠书经历。赠给我的,一册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一册是朱湘的《中书集》。这次赠与,有图书上的递承,也有文化中的启迪。便是精神,便是读书,便是艺术——
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绅士腰间的佩剑。凡常时刻并未有几多实用的意义,但它都是身份的标牌,象征着高贵、自由与尊严;待到关键时刻,便可依仗它去捍卫,作最后的抵御。
什么是读书?读书正是开刃的砺石,随时除去佩剑上的锈迹,使它永远放射出不钝的光芒。
什么是艺术?艺术全是对生活取一种赏玩的视角。比如用山木挖烟斗。山木是固有的质材,用来挖烟斗,而非别的器物,这便是对生活的个人取向;烟斗可以吸烟,表现出生活之实用性;但却并不满足,还要用砂纸把烟斗打磨出美丽的花纹,便可以清供于案头,作文物的珍赏,便可以享受到一种超乎生活实用之上的不可言说的趣味。如是,生活不仅可以过,而且可以玩味。
——(凸凹《赠书小记》)
精神、读书、艺术,对于一个嗜学的后生很要紧。天启一般:精神的干柴,霎时爆燃;读书的要义,豁然明确;艺术的细胞,于瞬间激活。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美中不足的是,先生的话语会随时间流逝,渐淡渐远,缺少细细品味的可能。没有办法,这是语言的自在规律。于是,就遗憾。不期然,先生竟然用文字将语言记录下来。散文《赠书小记》承载的精神、读书、艺术的特有光芒,沉潜在时间深处,耐心等待着值得等待的后生。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朱湘的《中书集》是凸凹先生最珍爱的两部书。多年以来,一直在我书架的显要位置珍藏着,不敢示人。两部书自上架之日起,便以两张雪白的纸张包裹。一是防止有人贸然索取;二是便于接受大师的文化熏染;三是随时承接来自先生的温暖关注。此后某年,我从良乡西街的文雅书屋以很便宜的价格购得一套《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版本是一样的,只是原版日期要滞后十几年。其中,就包括这两部书。果然朋友中也有相同的雅号,我便将整套书中的《湘行散记》(沈从文)和《中书集》(朱湘)送他。不过,我没有先生那样的“悔意”。无悔不说明我不在意,因为有先生赠我的两部书垫底。
感谢凸凹:教我独享,也教我分享。懂得独享、知道分享,才是珍爱的本来意义。
这一次赠书的数量很大,是凸凹先生用车给我拖来的。明显感觉,他对于我的文学创作寄予了厚望。安顿好这些图书,就到了晚饭时间。于是,我们就近来到良乡东关的“九头鸟”饭庄。
酒桌上没有外人,只有我和凸凹先生一家。酒,不算多。几瓶普通啤酒,对于我们的酒量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儿。可是,几杯酒下去先生却说出“醉话”。“啸思(凸凹之子),将来我没了,把我的书籍全部转送给你阎叔儿吧。”先生对他的孩子说。我一愣,师母脸一沉,啸思没有作声。一片沉寂,都预感到这话不够吉祥。我急忙打破这种沉郁:“不说这些,那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冒昧揣度,先生是借助酒话,表达一番真实的思想——
第一、是亲情的表示。先生将我列入凸凹家族序列,确认书籍的承继。需要师母,啸思作个明证,也是可能。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家庭,继承是不得了的大事,是不能轻易出口的。然而,熟稔中国传统思想的凸凹先生却有举重若轻的一锤。这正印证了先生的一句话:心比天大。
第二、是本能的袒露。一个优秀的文人,追求生前的文化辉煌;一个卓越的文人,还需寻求身后的文化传承。辉煌和传承,对于文人来说,是责任也是本能。从这一层面上讲,凸凹算得上中国的卓越文人。
第三、是向学的激励。一份浓郁的亲情,一副传承的重担,无疑是先生向学的鞭策。无论我身在何处,总能感受到他关注的目光。这束目光,使我不敢懈怠。想象中,是先生关爱的声音。小子,你就干吧!没有进步,看我不抽你。
今生今世,能够师从凸凹先生是我的福气。
我如是想。
《文化长阳·散文卷》出版发行的当天晚上,我和凸凹先生再次聚到一起。
电话是先生主动打来的:朝来,晚上请我喝酒,你的散文集《文化长阳·散文卷》出版了。感受得到,他有一股掩饰不住的自豪情怀。《文化长阳·散文卷》是我的第一部散文作品,它的出版让我有一种初为人夫、初为人父的体验。似脱胎换骨,更似再生再造。
按照常理,第一杯酒本该我敬先生、师母,没有想到先生、师母竟然破例抢先敬我。我惊惶地起身,端杯。先生说,你且坐正坐稳。我们不是敬你,我们是敬你的文章,敬咱的文化。我着实地感动了,一口将酒喝干。第二杯酒,该我敬先生、母师,我端起酒杯:“敬先生、师母再造之恩。”“不敢当。”师母惶惑地说。“敬,应该。”先生端稳地坐着,安心地承受着。
再造之恩,用意准确。你想啊,先生从“小”把我拉扯“大”。我如今有了自己的散文集子,有了再造的感觉。不把这样的词汇敬给先生,咱就亏心。
再造之恩,是血缘之上的亲情。
温暖、向学是这种亲情的原本特质。
五
与严谨的治学态度相反,凸凹先生的治学方略宽容。 这种宽容,颇有老庄风骨——无为而治。
一篇文章到先生手上,通常会有三种评判:不错,还成,路数不对。其余,也会适度说上几句。这很像当下教育界风行的等级评价: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其中,绝少有百分制的苛责成色,更多是宽松的激进氛围。
奇妙的是,我却不肯松懈。
究其原因,倒是不很复杂。其一、我恋念那份成功的享受。先生是个直爽的人,他的评判不会掺假。正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的审美标准很高,说是不错,一准儿是篇好文章。这种时候,我就有按捺不住的快乐。当然,如此快乐也无需压制。既然到来,就尽情享受。说不定,还要在孩子面前扭上几下自己伴奏的即兴舞步,或是在妻子眼下很蹩脚地唱出几句——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愿你有一个好身体,健康又美丽。在孩子含笑的注视下,在妻子一句“疯子”的嗔怪中,一家人享有融融的快乐 。兴之所致,我还要情不自禁地嚎上几嗓儿《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这番情境之下,一种超然的自信便潜滋暗长了。其二、我恐惧自卑带来的那种痛苦。如同一句“不错”,先生的一句“路数不对”一样会使我情绪发生波动。是下落的感觉,就这样一直坠落下去。失重的感觉,提吊心肺。如果用失魂落魄形容显得夸张,那么用不思茶饭概括就很恰切了。这种痛楚,以至让妻子心生怜悯。妻子是一个矜持的人,悲喜交加的情绪与她无缘。每到这时,她总要心疼地劝慰。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写不好也没有办法。我感激她的抚慰,可是仍然不能饶恕自己。尽心尽力倒是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是“出水就看两脚泥”。这样思忖,并非旁人不肯谅解,而是自己不想宽恕。
现而今,凸凹先生对我失败的评价日渐稀少。越是这样,我愈想把文章做到极致。
俗话说: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种情况,托付一方最难容忍的就是一拖再拖。对此凸凹先生却能以宽厚之心容之。
前不久,先生嘱我写篇文章。内容、字数、期限都很宽泛。
8月15日是交付稿件的期限。这期间,我迟迟不能成文。思路乱得一塌糊涂,语言烂得不像样子。意图一改再改,稿纸一废再废。8月14日,我硬着头皮打电话。先生很痛快,8月20日交吧。
8月20日是交付稿件的期限。这期间,写作状态依旧。我这样形容当时的创作状态。灵感“失忆“,语言“便秘”。混沌中,草草成就一篇。自己,亦不知所云也。电子邮件发出不足一小时,先生就打来电话。这篇文章路子不对,应该如此这般入手。说话听音,锣鼓听声。很显然,先生没有放弃的意思。还有时间吗?我内心惭愧地问。今天是8月20日,再给你五天。五天后,是8月25日。
8月25日是交付稿件的期限。几天下来,仍是没有成文。我思忖再三,再三思忖。忐忑而沮丧地给先生发出一则短信——
先生,我是朝来。我都没脸给您打电话,更甭说见面了。您要的稿子我没有写出来。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多天,灵感就像失忆一样,语言也烂得一塌糊涂。勉强写些文字,连自己都自卑。也许太想写好的缘故,过于拘谨,反而弄糟了。只好请求您的谅解。说是谅解,实际是我在向您谢罪!先生,实在对不起。
这则短信,虽然有些矫情的成分,但却是我的真实表达。在惴惴不安中,我终于在当天下午盼来了先生的消息。明明白白,先生又给我五天时间。
8月30日是交付稿件的期限。稿件发送后,立即得到先生的回应。不错,这样写就挺好。天呀,我长长呼出一口气,紧缩的心慢慢地舒展。与此同时,快乐潮水涌动。
宽容治学亦能创造“奇迹”。
事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