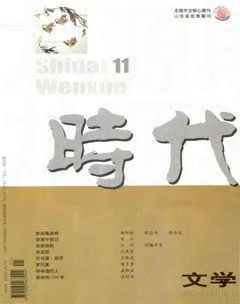那“别样的生活”
认识凸凹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虽然也不过是十来年的事,但居然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的事情。文学一点地想,总归难免生发出多多少少的感慨。
那年,我们的副刊做一个征文活动,从寄来参加活动的稿子中,看到了他的散文《四爷》。《四爷》的篇幅不长,写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故事,点睛地选取了老人一生的几个片断,凸显了一个有着朴素的人生理念与达观的生活态度的智慧老人的形象。文章的语言简洁利落,表达恰切而传神,读罢,让人确有眼前一亮的兴奋。与我们通常处理的投稿相比,《四爷》有着不同一般的文学素质,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在那次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了最高的奖项。随后,在当年的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的评选中,《四爷》又获得了一等奖。
凸凹来领奖的时候,我们认识了。这时我得知,他的本名叫史长义,京西房山人,当时任职于房山区政协文史办。
那个时候,电脑写作还没有现在般普及,大家都还是用笔来写作。长义的字很有特点,不大,确总是不甘心被局限在格子中的样子,且棱角鲜明,有些让人联想起漫山遍野的山石。那几年,有着这样字体的稿子,每年都会出现中我的面前。即使是后来,长义文名愈显,向他约稿的报刊越来越多,完全没有必要总在我们的“地盘”露面了,他也还是时常会给我们稿子,并时常参加我们组织的活动,这足以见出他为人的忠厚。
认识他不久,就看到了他和文友张振乾合出的作品集《两个人的风景》、《两个人的故事》等。至今我仍记得那两本装帧朴素的小书,那书中的文字质朴而充满蕴蓄,常能使我深深感动。
后来,读凸凹的文字多了,渐渐地对于他那一时段的生活有了些许的了解:由于夫人户口的关系,他们很长时间里都无法享受公房分配的待遇,他们的家是他们自己一砖一瓦地建设起来的。这些他曾经写在了自己的作品中,其中的琐碎艰辛则大多是阅读文字的人,从字里行间品读出来的,他的笔下展现的却大多是安天知命的坦然。这样的人生态度一直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从第一次读到的他的文字《四爷》,到不久前读的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神医》中的很多篇什。可见,这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底色。
“我向往纯净的生活,却总是被琐屑打扰。”这是我自己随口诌的两句话,曾用于给一个朋友写的一篇小文中。此刻,当我回忆着我认识的凸凹即史长义时,却发现,需要颠倒下次序,才能描述我感受到的他那一时段的生活:“我总是被琐屑打扰,却向往着纯净的生活。”是的,生活的琐屑并没有令他消磨于其中。或许是来自祖辈血液中的坚忍与执着,或许是对于文字的深刻迷恋,使他在艰窘的生活常态中,依旧怀抱着对于文学初恋般的热望。
曾有人形容时下的时代是“读物ojP0uXSVzs43+bETybJ5N6muO1niRaOnDjJdama0lPc=泛滥而文学衰微”,对于文学存在的末日之叹在今天更是时有耳闻。文学为何?文学何为?这个问题,在现在这个时刻又一次油然而出。对于那个年代的凸凹即史长义来说,除了微薄的稿费之外,他钟情文学的理由何在呢?不由想到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中接受“耶路撒冷奖”时所作的受奖演说《文字的良心》。以下的两段话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长义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在琐屑的生活中依旧痴迷文字的人,提供一个途径:
“……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可以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如果文学本身,如果这项进行了(在我们视野范围内)近三千年的伟大事业体现一种智慧——而我认为它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文学重要性的原因——那么这种智慧就是通过揭示我们私人和集体命运的多元本质来体现的。它将提醒我们,在我们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互相矛盾,有时可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冲突(这就是‘悲剧’的意思)。它会提醒我们‘还有’和‘别的事情’。”
或许,正是这“别的事情”、“别的生活”才是文学存在的意义所在,它使文学具有了令人超越当下、既有的力量,它令人们在琐屑的生活中拥有了梦想,拥有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一种打量既有一切的不一样的眼光。
或者在下班后人去屋空的办公室,或者在自己一手建起的,简陋却温暖的家中,待妻儿熟睡之后,或者秉烛夜读,或者奋笔疾书,或者掩卷沉思……这是文字中的凸凹或史长义,这样的印象来自于我对于长义文字的阅读,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描写过当年的生活。
长义的勤奋与刻苦是无可置疑的。这不是来自他自己的描述,有多年来他的作品为证。若干年前,我亲眼目睹了整理出的截止到当时为止的他的大约还不是全部的作品,厚厚的四大叠,但还只是他写作的散文、随笔、书话等小体量的作品。而几年来,他写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玉碎》、《玄武》等近十部,还有今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神医》。这几年,他几乎每年都有长篇作品或作品集出版,其创作的活力,实在令我惊诧。有的时候,看着摆在面前的他的作品,我常常会想象着他写作这些作品时的情景,于是,不免感慨。
自我认识长义以来,十几年过去,他的岗位从文史办到基层的乡政府担任乡长,再到现今,落在北京市房山区文联主席的位置上,说得上是经历丰富了。而在到文史办工作之前,据我所知,他还在基层乡镇担任过一般干部。丰富的生活阅历奠基了他的文学写作,而大量涉猎领域广泛的阅读,又使他从他生活的土地上超越出来,具有了广博的学养与开阔的视野。这一切的努力最终结果于他的文学写作,于是硕果累累,便也不足为奇了。
从认识他到现在,十几番寒暑春秋,除却头发略见稀疏,并有白发现于两鬓,他的样貌以至谈吐都无太大的变化,也算是难得了。他说话,略带京西口音,直爽外多多少少夹杂着些文人的狡黠,听着倒也有趣。最喜欢听他讲家乡的故事,就如最爱读他乡间生活的文字。那些文字和人物故事都那么率直,并不一定美好得让人向往,但结实得让人觉得踏实。或许,正是这踏实的早期记忆,让凸凹或史长义的文学之路走得很安定与执着。这是一种人生底气的涵养,其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写作还只是它的收获之一。
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就我涉及长义文字的记忆来说,他写父亲的篇什不止一二。就在前不久,又从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神医》中,读到了《无为》。这是我读到的长义的文字中对父亲写作最深入的一次,也最令我慨叹。
长义也写过祖母、母亲,但或许是自身性别的缘故,在亲人中他对于父亲的写作是最多的,由此也见出父亲对于他人格的形成具有着怎样的影响。在他的《无为》中,我依稀读到了今日长义的某些影子,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由对于父亲的审视而渐渐地开始来对于父亲的贴近。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也是生命的馈赠。
那就不得不提到2009年长义发表于《北京日报》副刊的散文《最后的凝视》。这是又一篇关于父亲的文字,它讲述了父亲与“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特定地方的擦肩而过的因缘。而父亲病重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最终留下的目光,凝结了一个人的一生的慨叹,实在让人无法不感慨万千。恰巧的是,这篇文章又一次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评奖散文类的金奖。评委中一位资深编辑曾这样评价它:“它让我落泪了。”这样的评价也许在旁人看来并不出色,但对于一个终日浸淫在文字中的人来说,其中的分量不言而喻。
长义刚届中年,他的创作必然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着。对于他的读者我们来说,该做的、能做的,也许就是送上自己诚心的祝愿,并认真地读着。
这样很好了,能拥有着那“别样的生活”是一种福气,无论对于写作者的凸凹或者史长义,还是对于作为阅读者的我们,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