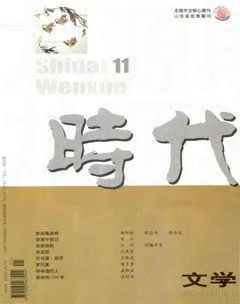凸凹编年史
——二十多年前的凸凹,二十多岁,刚刚从农学院毕业,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手里拿着一块小黑板,架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讲科学种田。
——十五年前的凸凹,三十多岁,我们刚刚相识,那时他是乡长,在北京房山区南召乡。他的办公场所,是砖彻的平房小院,一派乡土气息,有一天,小院里来了一群年轻的写作者,有邱华栋、伍立杨、彭程、从深圳赶来的姜威,还有我,主人就是凸乡长。
那时我刚刚主编一套《新锐文丛》,包括伍立杨、王开林等在内的新锐们悉数亮相。大概就从那时开始,九十年代中期,那一批写作者——李师东先生曾命名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渐渐聚拢到一起。很多年后,我与《天涯》主编李少君兄回忆这一群体的时候总结道:这批写作者的相识相遇,缘起于八十年代校园文化时期,那时各所大学都有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彼此交流甚多,我与少君、华栋、桑克、杜丽等的往来,就缘于那段时期,但那还只是早期写作,形成相对成熟的写作阵容,是九十年代,包括伍立杨、彭程、王开林、苇岸、周晓枫、宁肯、张锐锋、李敬泽、李冯,以及凸凹,都是在九十年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勾结到一起的。不知为何,我们这批写作者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体意识,自觉地合并同类项,不像如今“八零后”、“九零后”,个人主义色彩很浓。这并非因为我们喜欢拉帮结派,而是因为相互间的敬重,尤其在九二年全民下海热之后,奋战在祖国的文艺战线的,就更加难能可贵,直至今日,这批人大都步入中年,每个人的生活都经历了一连串好的或者不好的变故,世俗地位也早已别如天壤——官升副部、正局者有之,贵为军长者有之,像我这样的无业下岗人员亦有之,但那种彼此的爱惜敬重,却有增无减。
在认识凸凹之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在《光明日报》、《青年文学》等报刊,都读过他的散文,所以,当伍立杨引见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内心早已与他熟稔。那天凸凹拿出地方酒招待我们,所有人都喝得有点高,晕晕乎乎地,得到凸凹兄赠送的礼品——乡镇企业生产的衬衫,军绿色的,凸凹的憨朴可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
以后和凸凹的交往就渐渐多起来,至少,房山有了一个可以喝酒、谈文学的朋友,对房山的想念便多起来,以至于很多年后,凸凹成为我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我生命中许多重要时刻,凸凹都是和我在一起的。
——十来年前,凸凹到我办公室,从挎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稿子,说他写了一部小说,让我看看。应当说,我当时没有对这部小说寄予太大期望,只是觉得是朋友的作品,就得看看,不想读了以后,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我后来常常提起来的《慢慢呻吟》。这部小说,笔调平淡,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实际上写得荡气回肠,大开大合,远胜于当时世面上走红的某些名家名作,凸凹的底层经验和他对叙事的高超把握,在这部作品表现无遗,体现出一个作家对历史的洞察力的悲悯情怀,如同我为《慢慢呻吟》所作序言中写道的,“作家以一种纯粹个人化的视角透视他们,作家自己在试图摆脱任何‘摧眠’……他具有了鲜明的个体意识。这使他的作品显得高深莫测。当然他把他的个人意识隐含在背后,从不暴露,并不去破坏时间的连续性,小说便很好读,故事起落转合,让人拿得起,放不下。他的目光落在了千万个村庄中的一个。九州之内不知能找出多少个翁太元、翁息元、翁上元、翁七妹、南明阳、谢亭云……但他们一旦被作家选定,他们便同作家——还有我们——一道歌哭着上路。所谓的‘共鸣’,实际上是时代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的焕发。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设置的深刻的隐喻。这种隐喻,不仅是唤起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思索,更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仍处于‘历史’之中,不要忘了保持清醒的神经。”
我至今觉得,这是一部应当在二十世纪小说史上占有席位的作品,只是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那段时间,我几乎全部的生活都被这部小说控制了——我上班读,下班回家还读,读到紧要处,时时潸然泪下,以至于在家人和同事面前不断丢人现眼。出于出版人的本能,我为此书出版竭尽全力,但没有在全国一流的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我至今引为一大憾事。
《慢慢呻吟》出版之后,我对凸凹戏言:“你可以死了。”意思是死而无憾。
凸凹却从此在小说领域一发不可收,一部部长篇,如《永无宁日》、《大猫》(原名《乡长手记》)、《玉碎》、《玄武》等接踵而至,内容涵盖房山自抗日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北京城西南郊的房山,这片中国文学版图上的空白之地,一如福克纳笔下神秘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成为凸凹写作的永久题材。
然而,凸凹也是在这段时期,显示出他与一般小说作者的不同。他的视野更宽,阅读范围极广,同时创作了大量学术含量极高的思想随笔和读书随笔,这在他的《游思无轨》、《书卷的灵光》、《风声在耳》、《以经典的名义》等随笔集中有集中体现,在谈到安妮·勃朗特《阿·格雷》、川端康成《山之音》、怀特《人树》、卡赞扎基《自由或死亡》、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诺里斯《小麦三部曲》、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等作品时,都颇具真知灼见。
——十年前,正是我和凸凹喝酒的黄金时代。那日我到房山,照例喝了不少酒,先醉的是凸凹,我把他扶回家,他醉眼蒙眬地说,先在卧室里睡会儿,叫我在他的书房里稍候。这使我有机会对凸凹的读书有细致的观察,因为了解一个作家的书房,便会了解他的知识结构和心路历程。那天,我按照凸凹的指示,在他的书房里“稍候”了整整一个下午,下午的阳光从窗子照进来,使那间不大的书房显得空旷和温暖。他呼呼大睡,我并不急躁,是因为他的藏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我第一次认真地打量他的书房,那是一幢普通居民楼里一套十分普通的三居室,凸凹用了一间作他的书房,书房里四壁书架,从底到顶,开放式的,很有气势,靠窗横放着一张书桌,书桌也堆了很多书。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拥有这样一间书房,堪称奢侈。那时的我,书柜和书桌都是放在卧室里的,很多年中,拥有一间专门的书房,都是我的梦想。因为那个书房,所以等待并不显得漫长,甚至成为对我的某种犒赏。除了隔壁传来的凸凹隐约的鼾声,周围十分安静,我仔细地翻弄着凸凹的藏书,对凸凹的敬佩油然而生。许多书,是八十年代的旧书,许多书我至今不曾读过,而他很早就开始自觉地遍览好书,而且对好书,有着独到的判断,许多书,他都密密麻麻地作了旁注,连我那时刚出版不久的三卷本《祝勇作品集》也不例外。那个下午,我看到了凸凹的强大,他必将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作家。
《慢慢呻吟》出版之后,凸凹没有大红大紫,这丝毫不防碍他对写作的热情。与那些精于炒作的人相比,文学给他带来的回报少得可怜。但他是一个温厚的人,对命运也显露出温厚的态度。不苛求,不放弃。
——五年前,我离婚,躲开人群,独居房山乡下,后来踢球受伤,瘸腿半年,凸凹自是时而来看我,给我带来诸多安慰。我也试图像他那样,对命运表现出温厚的态度。我们一起去门口小店,喝小米粥,吃葱花饼,喝二锅头,在无比尴尬的处境中,依然探讨红旗还能打多久这样严肃的问题——后来我去美国啃洋面包,心里还怀念中国乡村的小米粥。当年有两个场景不能忘:一是,那年“五一节”,他到房山乡下看望老母,先把我接上,我就这样与他一个母亲两个弟弟一个老婆一个儿子还有一条大黄狗一起过了个节,我腿上打着石膏,拄着拐杖,第一次出门,坐在凸凹故园的小院里,让温煦的阳光穿越发霉的身体一路把心底照亮,另外,那天的炒鸡蛋好吃;二是,一日黄昏他开车来看我,那时我腿上依旧打着石膏,不能动,我就说,在门口小店订了几道小菜,去野餐吧,他开车带着我,一路开到麦子结穗的田里,四周无人,只有风吹麦穗,哗哗作响,我们坐在干净的麦田里,谈人生和文学,我从小画麦穗,直到那天,麦穗才真正开放成我心中最美的植物。
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一部自认为重要的思想学术专著——《反阅读》。那是我文革学研究长久积聚后的一次喷发,尽管腿上打着石膏,而且腿不能竖起来,只能横放,以免手术刀口出血,写作十分不便,伤口的疼痛也时时袭来,但我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定要写好这部渴望已久的书。作为精神盟友,凸凹,自是这部书写作的见证者和支持者。《反阅读》后来在美国完成,经台湾著名作家林文月老师举荐,由台北的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美国的电视台和报纸都作了采访报导,得到包括哈佛的麦克法夸尔、耶鲁的史景迁、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在内的著名汉学家的支持和鼓励。我回国,把《反阅读》样书交到凸凹手上时,他回敬我:“行了。你可以死了。”
我们就这样给对方判了死刑,并且像两个贱人一样对这样的鼓励全然笑纳。我们有如瞎子背瘸子,在困顿中互相支持。有人议论,凸凹和祝勇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我庆幸世上还有这样的裤子,能把两个热衷于文字的人结合到一起。我把那句话当作对我和凸凹友情的最佳赞扬。
——四年前,我和凸凹在周晓枫家看影碟,放的是一部以色列电影,英文名字“Walk on water”,意思是“在水上行走”,很诗意,影碟上印的中文译名却庸俗不堪,叫《男人的心中只有男人》,好像同性恋的片子,实际上不是,是讲男人之间的情感,而且是两个特别的男人——一个是德国男人,另一个犹太男人,情节很淡,沉下去,才能看出导演的功力。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作品,通过两个年轻人的现实关系反思历史,表面上轻飘飘,实际上沉甸甸。我和凸凹的共同感受是:这样的作品是真正的好作品,于平凡素材中见深度,杯水中有波澜,四两拨千斤,胜似重大主题的写作,我们都希望自己写出这样的作品。尽管凸凹说我有了《旧宫殿》、《反阅读》 这样的书,这辈子的写作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但至少在我看来,我以往所有的写作,都是在为写出“Walk on water”这样的作品做准备,凸凹的小说,如《慢慢呻吟》,已有这样的迹象,但对我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两年前,我在康定的一家小书店里看到凸凹一部五十万字长篇小说《玄武》。这部小说的电子版我看过,但此次是江苏文艺出版社作为改革开放30年献礼巨作隆重推出的,紧接着看到报刊上的各种评论,虽远在藏区,心里仍为他叫好。这部作品后来获了北京市纪念建国六十周年优秀作品奖。
——半年前,凸凹给我打电话,说他中篇小说集《神医》出版,邀我参加研讨会。当时我仍在藏区,被稻城的雪山围困,插翅难飞,所以无法参加,只能在电话中表达祝福,回来后看各大报,好评如潮。我知道自《玄武》写成后数年中,他一直在磨砺中篇,在《十月》、《当代》、《长城》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这本书,也算厚积薄发。
张仃说,大器晚成,这是艺术的规律,谁也逾越不了。金庸说,有人给他看十四岁少年写的武侠小说,他不看,因为他不相信少年会写好,他可能有才华,但他没有阅历,不知道夫妻之爱、父子之情,不了解人生的各种喜悦和伤痛。
凸凹人到中年,两鬓已白,但凸凹不怕老,也不怕没有轰动效应,他有他的自信,他的自信不受他人的态度左右。他的文学路,成熟、稳健、有力。
——一天前,我写下这篇《凸凹编年史》,试图对凸凹的文学历程进行彻底揭发。今天——公元2010年8月18日,我对这一编年史加上最后一句话:
写好的作品就是在水上行走,看上去不可能,却有人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