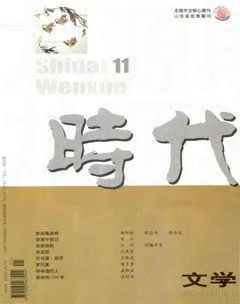风沙眯眼 我自清明
时近岁末,本期本栏推出一辑关于京西的实力派作家凸凹的文字,以飨读者。
凸凹本名史长义,生于京西,长于京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步上文坛,由散文而小说,已出版五百多万字、二十多种作品,成为一位进入全国读者视野、颇有影响的乡土作家。他不仅创作颇丰,而且传承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创作路数,提出“温暖书写”的创作理念,写出了一批具有更突出的艺术个性的作品,引起强烈的反响。
凸凹还喜爱读书,善于读书。他遍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写作、出版了一批读书笔记。他对茨威格、博尔赫斯、怀特、诺里斯、缪塞、川端康成等世界名家情有独钟,尤其喜欢怀特的《人树》和诺里斯的《小麦三部曲》,决心写出这样的作品。
凸凹正当盛年,他在写作上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对其寄以厚望焉!
本栏开栏已整整十四个年头,从明年起将略加革新。本期本栏增添了作家简历及作品目录、作家作品评论、作品选载等内容,就是革新的尝试,望读者诸君予以关注。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那里能够给心灵找到位置,让人感觉到生命的纯粹、高贵和慰安。也就是说,文学能够给人入定的力量,能找到“自我”,便不会为身外的世界所左右,就不会患得患失徒然悲苦,生命就壮大了。正可谓“风沙眯眼,我自清明”,卑微的自我,获得了本质上的尊严。
关于文字
文章写了二十余年,已形成了“文字思维”——所经历的人事与物象,即便是没有明显的意义,也想用文字的编织,勾画出意义。这是一种本能,在它的推动下,居然就有文章源源不断地写出来,令人惊奇不已。
文字真的是一种性灵,而不是工具,它默默地独处着,等待着“意义”。
文字的等待与作者的等待是相向而行的寻找,一经“路遇”,就结伴而行了,共同地完成了“意义”的过程。
路遇,因为不是预先的邀约,便具有宿命色彩,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料的。
二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吱吱响的日光灯下枯坐,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媒婆”这两个字,自己便感到很诧异,因为此时的我,已经有了很优雅的生活,所处的语境是与如此俚俗的字眼不相干的,便想把它们驱赶出去。但是,愈是驱赶,愈是呈现,弄得你心情烦躁。便只好抻过几张白纸,把这两个字写下来。奇怪的是,一旦落笔,相关的字词就接踵而来,直至写得筋疲力尽。掷笔回眸,竟是一篇很完整的关于媒婆的文章,且有不可遮掩的“意义”透出纸背。
便不敢再儿戏了,定了一个《中国媒婆》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抄录在稿纸上,寄给一家叫《散文》的杂志。一月有余,竟被登在重要的位置上,不久,竟又被著名的选家、著名的选本(选刊)接连地选载与收录。二十一世纪的开元之年,居然被一本叫《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的书树为“经典”了。真是始料不及。
有论者说,这篇文章文字典雅老到,非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长期的文字修养而不能为。这个评语把我吓坏了,因为那一年我才25岁,弄文字也不过三五年的工夫。真正的原因,是“媒婆”这样的字眼显得老旧,老旧到最后,就“老到”了——是文字驱动的结果,与作者的阅历和修养无关。
还是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低档的烧酒喝多了,神魂颠倒,愤世疾俗,不平之气盈满胸臆,便口出悖语,且喋喋不休。酒友被吓坏了,把我推进房间,叮嘱道:“有不平事写在纸上,莫在大庭广众之下胡言乱语。”便把那些放纵的字眼涂鸦在纸上,不期就涂成了一篇《悖语人生》。文章在《青年文学》发表之后,竟得到一片喝彩,还被选家选进一部“先锋散文”,意外地捞了一个先锋散文家的名号。
这真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素日的我,是循规蹈矩的一个人,笔底的文字也是很本分的成色,与“放浪”是无缘的。是被酒液烧灼了的文字推动着我往前走,稀里糊涂地呈现了“先锋”的意义。那样的文字,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是命运之赐。
这种情状给了我一个启示:所谓内容决定形式,是偏颇的,文字(语言)本身的存在方式,往往就是内容,就是“意义”。
孙犁早期的文章为何有湖光水泽?因为他使用了与水气有关的字眼。晚年之后,他怕动荡,怕水,躲进书斋里,整理旧书,对古色古香的文字有感情,下笔为文,便是“芸斋笔记”和“书衣文录”那样冷峭、简朴的文本。俞平伯和废名的散文为何有“涩”味?是因为他们欢喜于用涩味的字词书写。是文字之“涩”,而非内容只“涩”。如果把他们的文字特色解构掉,文章的内容其实是很平白的,甚至是很平庸的。
换个角度看,说到“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料的”,这是对不成熟的作者而言。对于那些成熟的写作者,他们深知文字对作者的推动作用,为了从“宿命”中挣脱出来,他们自觉地采取了“反抗”的姿态,有意识地选定了一种与自己的身份、影响和年龄、阅历相适应的文字样式,就写那样的文章,就发那样的格致,于是,“风格”就形成了。
所以,所谓“风格”,标志着写作者已进入了一个与文字和谐相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写作境界。
从本质上,这体现了对文字的敬畏。
关于散文
之于散文写作,已经足够二十年;累积下来,有二百多万字之余。无聊时翻检,多少还有些成就感,感到人生未尝虚度,心底看得起自己。这一点很重要,人而为人,说到底,还是活给自己的。
反省一下,少时就有写作欲望,崇拜作家并心向往之,对金钱和地位反而看得淡。这影响了自己在“实生活”中的发达与发迹,虽然满肚子诗书,除了一个饱满的面相,被人高看的地方很少。常孤独寂寞得失眠,甚至悄然垂泪。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活在词语中”,业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有不可剥夺的自足自适,能时常感到自我。人间冷暖,均转化成内心的温暖,悲悯着小我,也悲悯着这个世道。
我是个沉得住气的写作者,写作活动少功名、功利的成分,多是为了表达内心所思所得,娓娓地道出对身外世界的看法。外界的评价不很重要,快意于文字本身。这一点,与孙犁和汪曾祺仿佛。
也是这个原因,我的写作,主观色彩很强,不太愿意作纯客观的叙事,也耻于渲染式的抒情,与流行文字远些。所以,写了这么多年,门前依旧冷清。我常劝慰自己,香火繁盛的庙宇,多是小徒在弄机巧;寂寥深山中,才有彻悟人拈花而笑的静虚守护。这种守护,才真正属于精神。
这不是在标榜自我文字的品位,而是说,甘于寂寞,不做欺世文章,不说欺人之语,是真正的“门徒”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品格。
我追求文字的“复合”品质,学识、思想和体验,不露声色,自然而然地融会在一起。我觉得,只有学识,流于卖弄;只有思想,失于枯槁;只有体验,败于单薄。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丰厚了——前人的经验,主观的思辨,生命的阅历——知性、感性和理性均在,这样的境地才是妙的。其实,天地间的大美,就在于此“三性”的融合与消长,使不同的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文章若此,适应了自然的律动,生机就盎然了,对人心的作用——换言之,与心灵遭遇的机会就多了。
此种意识,是我创作的遵循与动力;虽笔力不逮,但从不敢懈怠——苦心经营多年,所得甚少,惭愧不已。
关于小说
现在的评论界,有一个倾向,好像希望创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他们特别地注重关于文字的“感觉”,只要合了他们的感觉,就是一部好作品了。他们是“感觉派”。
但是,你怀着十分的虔敬,去读他们“感觉”好的文字时,发现那些作品,要么是在文字上处处散发着暧昧不清的小情调、文字上的小精致,比如把心情不好,喻作“我的心情像一盆脏水”,把节制的欢娱喻作“我隐忍地呕出一声快感”;要么是在叙述上人为地扮酷、人为地点染,比如一部以农作物命名的小说,乡土上的人物就很不乡土,带着城里人的想象和好恶,夸张,乖戾,毫无节制地行而上着,把乡土女子的自然欲求凝聚到城里人的快感地带,满足了书斋里的畸形趣味。所以,那些论者即便感觉良好,亦有吓人的权威态,却让人看出他们的破绽和可怜,他们一切都从趸来的观念出发,不知道“发生”的原生态,他们仅仅,也只有仅仅,是在个人的畸形趣味上毫不羞愧地把玩着,并且理直气壮地评判着,说:“因为你‘俗’,因为你不‘文体’,你便不可能有理。”
但是,他们忘了,被他们最最迷信的博尔赫斯却说过这样的话:文字的精致是脆弱的,原有的韵味往往会在传译中消失得荡然无存;然而,再拙劣的译笔也不能丝毫减弱《唐吉诃德》的魅力,是它勃郁的灵魂使然。
所以,他们评判的管道里,喷出的是酸性的小资的苏打水,而不是艺术的精液,更遑论灵魂之血。
记得鲁迅说过,民间的相貌即便有些“俗”,但是,是“实生活”,是属于人的。那么,“实生活”便是小说艺术的依据;那么,健康的叙事,便不能离开其中的人物,其中的事件。那种光见文字,不见人事的小说,可能很雅,可能很酷,可能很有感觉,但是,它假,它苍白,会误导人们轻视生活,把有闲的娱乐,当作日子。
问题在于,牛虱虽然瘪,吸血的功夫却是大的,它紧紧地地叮在行进的牛身上,让善良的牛痛痒不堪。但是,牛的体魄毕竟是大的,烦躁一会儿,驻足一会儿之后,渐渐把牛虱忘记了,依然若无其事地前行,毫不挂碍地耕耘。为什么呢?前行,耕耘,而已。
牛是有担当的,它没有做文体家,或听文体家设坛讲座的余暇。
所以,一个严肃的创作家,应该有牛的品性,看着路,看着土地,看着“实生活”的人物和事件,质朴地传达出其中的消息,不歪曲,不做作,不张望,不自矜,更不摆阔,让人感到人性的真实和温暖,增一点抵御浮火和虚寒的自信,足矣。
这不是悲观之论,因为很有些未被评家读出“感觉”的作品,不可遏制地在民间流布着,那些想生活得庄肃一点的读者,从中品出了醉人的妩媚,少了一些自扰的怨尤,多了一份处世的旷达。这些读者,当然不是追逐流行读物的小市民;因为小市民的阅读趣味,与那些自命不凡的评家的趣味几近相同。
因此,我真心地想创作一些,能在民间默默地流布,能被民间的有识之士情愿地翻一翻,并不时地会心笑一笑的小说文本。
其实做个民间的写家也没什么不好,虽不能大红,但也不会太可笑,可笑到羞于文字、没脸见人的地步。
安心于作民间的写家,便以民间的立场、民间的视角写了几部关于小人物的长篇小说。计有:“乡土中国三部曲”——《慢慢呻吟》、《玉碎》、《玄武》和《永无宁日》、《大猫》、《欢喜佛》、《正经人家》、《双簧》,共八部。此外还有中短篇小说三十余篇(部)。
翻检一下自己的创作,发现自己并没有预定的题材,只是视素材对我的打动程度而定。感动我的,让我心神不安的,我便着手写下来,不然,我怕得了“癔症”。我是农民的儿子,生来就迷信的,那些让你不得安生的物事,你与其跟它作对,不如安抚它。所以,我很理解贾平凹先生,为什么把《废都》说成是“安妥灵魂之作”。
我还发现,我的长篇小说是做“减法”的,大体都是远离“宏大叙事”;社会的波澜只是背景,小人物的命运,或者说民间的生存状态,才是我心之所系。并且,连小人物的悲欢故事我都懒得记述,更多的是关心他们在“悲欢”迫压下的心灵感受。非要归类的话,我的小说,决不是“史诗”(虽然《玄武》被评论界戴上了一个“史诗”的花冠),倒可以说是“心史”。茨威格的“精神分析小说”,上个世纪施蛰存们的“新感觉派小说”对我是有影响的——我记述和挖掘的是民间的心态。
硬要定位的话,我作的是“民间心态小说”。
比如《慢慢呻吟》,是记述的“文革”、大炼钢铁和三年自然灾害那个特殊时期的民间心态。因为是“民间心态”,政治的“催眠”作用便被疏离了,便处处可见“惨烈”之下的温厚,左“右”离间下的守恒,虽不热闹,但绝不欺世。比如《大猫》,便是把基层“乡长”这一角色放在“小人物”的层面,记述其在“潜规则”的钳制下,义也忧心,不义也忧心的血泪感受,直让人在唏嘘之中,生出一种悲悯。悲悯何物?心之温柔也。再比如《欢喜佛》,写的是“婚外恋”这种“俗烂”的题材。但正因为“俗”,才真实,才有真货色。“艳史”往往是“哀史”——与人上床,决不简单是一个本性和欲望实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灵魂的或“陷落”,或安妥的过程。追求净化、“纯粹”与接受现实,甘于沉沦,都是需要超拔的“心力”的。所以,《欢喜佛》是一部严肃的“心灵史”,它试图对同类题材作品的表面化、感官化进行有深度的反拨。平心而论,它是完成了这个使命的,许多个中之人告诉笔者,他们是饮泣而读的,心灵是大为震撼的。可惜的是,评论界是“洁癖”和腰斩术并行不悖的一群雅士,他们不屑于看完全书,只凭着对这种题材的偏见,便认准它是一部“通俗文学”,甚至是一部“感官文学”。这种无因由的“血脉贲张”,让人感到,我们的评论家是如此的可爱,他们有着“儿童般的天真”。然而,鲁迅、蒙田和梁遇春却也说过的,儿童的天真虽可爱,但不可贵,因为它出自感官和本能,而不是出自经验和理性,如若挂账的话,是隶属“生物史”的,离“心灵史”还差得遥远。
说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多余的,既然是“民间心态小说”,有民间的反映也就足够了,偏偏还要往“坛上”瞭望,也正说明作者的“天真”。静心一想,不免惭愧。俗话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系“面子”和“不朽”的痼疾作怪也。
关于温暖的书写
在中国当代文坛,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是镶嵌到我的生命中去的,他的著作,是我的枕边书,每日耽读与揣摩,从无中辍。“人间送小温”是他的写作之道,也是他的人生品格,他的人与文是一致的。所以,我把他当作父执人物,虽无缘谋面,但一直是敬的,并把他的创作理念当作自己的人生信念。
因此,我的写作姿态就放低了:写小人物,关注民间情感,把能贡献温暖当作自己的创作伦理。
小人物与人间的本质近些,他们的生态往往就是写作者的生态,因为写作者从来都是卑微的一类人。所以,写小人物就是写自己,能让人在写中,自然而然地看清自己,心花怒放,创作的过程,也是受用的过程。
积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小人物在现实中是“小”的,但在人性层面却大得无边。首先,小人物有草木品格:兀自生长,不计冷暖。他们坚韧、隐忍、沉静、皮实、忘我,活得本分、自适、自足。这就了不得,如草木虽被磐石挤压,也能钻隙而出,向上生长。其次,小人物有天地性情:被人轻鄙,被人污损,却绝不仓惶失据,他们从容地应对,以失为得,正如天地——人一不如意就骂天,但老天从不怪罪,阳光依旧照进那家的庭院,雨露依旧滋润那家的田园;人一乱性就咒地,但大地从不计较,即便瘠瘦与旱涝加身,只要你播下种子,也没心没肺地生长,贡奉出果实。海子曾说,收获过的大地一片苍凉。他说的是真相,也道出了土地道德的核心所在,即:苍凉背后是孕育和再生,是不熄的生命力。其三,小人物有光明本性:因为他们不被人照耀,所以他们自己发光,正如萤火虫在暗夜里行走,自身就带着一盏小灯笼。也就是说,良心、悲悯、喜生与善,这些温暖的东西,足可以让他们不迷失自我,也不加害于他人。己心妩媚,而世间妩媚;己心温暖,而世间温暖——这是汪曾祺老先生文章与人生的底色, 以前我认为是他的个人修为,能冷眼看风物之后,才知道,那是来自民间,是他替小民说的。
这个认识可不得了,我因此而获得新生。
我原来的书写,追求阴冷、残酷、坚硬、放纵、激烈,以为这样才有叙事力量。现在我再这样写,就感到惭愧、自私和欺世。背阴处的积雪,可谓坚冷,最终也是被柔弱的阳光所融化;慈母轻轻的一声怨叹,会陡地在逆子心中生出一大片波澜,且久久不息,以至于决然逆转,痛改前非。我愈来愈清醒了,真正有力量的,是柔弱、温暖而绵长的东西,因为它是人间性的存在,与实际人生接近,能作用于人心。
真实的人生状况是这样的:对具体的死,人往往不怕,惧怕的是死的概念;对现世的贫穷,人往往能够应对,不能承受的,倒是贫穷的意识。正因为此,温暖的书写多么重要,它对世道人心有益。
所以就有了这组小说。它虽然弘扬了汪曾祺的叙事传统,但绝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出于相知,更出于内心的驱动。
几句后话
在我们房山,上世纪学大寨的年代出了一个叫吴春山的全国劳模,在别人都跟风效仿的时候,他有自己的理解——
学大寨的意义在哪儿?我认为不是比着葫芦画瓢,照抄照搬人家的具体做法——人家大战虎头山,把荒山变梯田——你有虎头山吗?学的是人家的精神。大寨的精神是啥?我琢磨着不外乎这三点:热爱集体,艰苦奋斗,虎口夺粮。
咋热爱集体?出勤出力是热爱集体,爱护队里的牲口是不是热爱集体?在我们平原,大面积耕作需要充足的畜力,那么大力发展牲畜饲养,就是我们应该做好的文章。科学饲养,科学使役,死亡率就低,繁殖率就高,畜力就充足,生产水平提高的就快,集体的家业就壮大。
他循着自己的思路,不仅做了,而且还总结出了一套被上边科学家都认可、并被各大报刊发表的“骡马经”——
喂牲口,要细心;如绣花,似穿针。
牲口回,要看真;有毛病,追原因。
卸下套,滚滚身;先上槽,歇歇神。
急吃草,结症根;猛饮水,肚疼因。
清明后,天气暖;湿拌草,料面炒。
立冬后,大肠阴;煮玉米,换干草。
前半夜,先喂草;后半夜,再加料。
中午喂,料要少;上套前,先饮好。
大把草,小把料;添多了,吃不好。
料瓣草,喂到老;饲养员,要记牢。
使牲口,量力好;劳累伤,不得了。
打着跑,牲口倒;慢拉套,先吃饱。
多歇息,饮要巧;车超重,要检讨。
自繁殖,贯彻好;靠公社,靠领导。
我之所以,把吴春山的“骡马经”抄在这里,是想说,我们乡下人搞文学,也不能只低头卖笨力气,也要抬头看路,善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