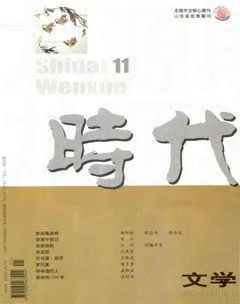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闯城记》:一个文明的寓言
摘要:杜光辉由生态小说转向平民小说创作,保留了一贯的人文关怀,在小说闯城记中,围绕三个人物,展开三个层次,演绎了城乡之间,人与制度之间的文明冲突的寓言。
关键词:闯城记;城市;农村;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作家杜光辉曾经以生态小说创作驰名文坛,“他属于国内为数极少的,专注于写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富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意识的作家。”[2]他的描写人与生态关系的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浪滩的男人女人》、《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可可西里狼》引发了文坛的震动,获得巨大声誉。但他的创作视域非常宽广,他并未局限于一种题材一个主题,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杜光辉的近作暂且放下了他一贯的生态小说写作,写了一个平民世界,写出了这个世界特有的伦理,写出了辛酸,也写出了温馨、正义、友爱、奋争,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2]。《闯城记》就是题材转向后其中的一篇力作,发表于2010年7月的《时代文学》。
小说讲述了三个农村女孩在都市创业的故事。夏雨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大专毕业生,她和小同乡冬梅共同经营着一家掏耳店,为都市人提供保健服务,寻求着自己的理想。一天早上,她在菜市场偶遇同村的卖菜姑娘春花,并巧妙地化解了工商人员对春花的刁难。随后,夏雨邀请春花和她与冬梅共同经营小店。夏雨还设法在店门口卖掉了春花的生态鸡蛋和蔬菜,城里人对春花的绿色生态食品异常青睐,使得三位姑娘在经营掏耳店外又出售生态蔬菜,并与绿色食品的购买者——普通市民,形成了一种互相信任的和谐关系。当生意红火之际,街头无赖骚扰捣乱,春花挺身而出,痛揍小混混,剔除了创业的第一个障碍。之后夏雨三人共同努力,通过高质量的保健服务赢得了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傅德兴的赞许,并介绍来了傅局长,获得官员顾客的同时,也为掏耳店带来又一次小危机。傅主任提出雇佣三人专职为领导服务时,夏雨以不卑不亢的巧妙谈判,保住了店面,又兜揽了生意。她们的掏耳店不仅为健康人群提供保健服务,并且轻易地治愈了面临高额医药费的患耳病的幼儿。姑娘们坚持着自己美好的理想,并固守着真纯的情操与高尚的的人格,毫不为商人的金钱财富所诱惑。在小说的结尾,当事业平稳前行时,冬梅与夏雨的父母的重病使她们的理想夭折,店面转让,积蓄花光,冬梅为昂贵的医疗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委身于好色的商人,失掉了了美好的青春。小说在姑娘们的痛哭声中结束,整篇小说贯穿作家一贯的基本创作精神,“依我看,不管杜光辉写什么,都渗透着辛酸而温暖的人文关怀,闪烁着朴厚的人性光辉”(雷达),“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灵魂的演绎,关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1],这些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却非小说的主旨所在。小说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人物心灵的挖掘都是次要的,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简单,夏雨、春花、冬梅为一方代表善良、纯真、理想、健康,同时也是弱者;工商人员、傅主任、街头无赖、好色的商人为另一方,代表贪婪、庸俗、丑恶、病态同时也是强势群体。人物的关系都是单线,没有交叉复叠。小说情节没有对人物内心展开细腻的探索与追寻,仿佛只有简单的是非善恶,形成了雷达教授所说的一种模式,他的写平民的作品“大都存在正与反的对立,双方的人物又大都推向极端,人物也似乎随之也缺乏了多面性;另一方面,精神性的内涵也需要深挖,不能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人性的善恶,而应努力触及生死、永恒、人与自然等根本问题。”事实上,对于《闯城记》而言,还不能简单地套用雷达的评判。《闯城记》主要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不是道德上人性上的善恶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效应,也不在于刻画立体的富于深度的典型形象,而是对一种制度进行含蓄有力的批判反思。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情节,都非自身所表现的表层意义所能局限,而是都在为主题的最后实现做着重重地准备。人性的善良美好、丑恶庸俗,在阅读中并没有产生通常道德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心灵冲击,故事情节也少有精心构筑的形式之美。小说的整体叙述在轻松的理想化氛围中进行,围绕着城乡文明的冲突展开,直到小说的结尾才发生逆转,从高峰跌落,理想碎灭。接受者也在最后一刻进入主题,悲剧的情绪覆盖了前期所有的阅读体验,对制度的批判成为小说真正的最具价值的社会性主题。与前期的另一篇小说《洗车场》相比较,《闯城记》的以上特点就更为明显。两篇小说都是底层小人物创业,都是三个主人公,都在小说的结尾发生逆转。但两篇小说的的差别很大。《洗车场》 由困境向顺境逆转,小说的文本效果就在整个叙事过程中;而《闯城记》由顺境转为困境,小说的主题在最后,感动力也在最后。它的整个顺境的每一个情节都似乎太容易了,就现实生活的残酷性复杂性而言,主人公们摆脱困境的过程显得太简单,并不像前者充斥着屈辱辛酸的描写。所以,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般意义来解读这部小说是不够的,虽然小说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方方面面的批评嘲讽,而深层只能是一个寓言,农村和城市文明关系的寓言;也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所要揭示的是人与制度之间被控制与控制的关系。
《闯城记》以三个人物、三个层次深刻地寓示着农村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尴尬关系。由低到高依次为生态文明、人的文明、制度文明,实际上小说情节也是基本沿着这样的顺序进行。以下依三个层次逐次剖析。
第一个层次,生态文明的层次
在小说主题的第一个层次,作者表现出生态作家的本色。作家自己曾说,城市依赖农村的食物供应,农村的生态关系着城市的健康。在春花卖蔬菜鸡蛋的一系列事件中这个层次得到了体现。小说一开始,即以春花卖菜的故事引出三位主人公。在春花与女工商人员矛盾冲突事件的前后,作者不失时机地表达农村绿色生态食品对都市的诱惑。农村的绿色食品吸引着市民的眼球,工商人员对蔬菜鸡蛋的垂涎及市民的疯狂抢购,都表现出了绿色的土地对于物化扭曲都市的巨大优势。那些女工商看着羊肉和店主说闲话,“这年头啥东西都不能吃。猪肉喂瘦肉精,鸡鱼喂激素,鸡蛋喂苏丹红,只有牛羊是吃草的,吃起来还放心。”这里既是贪婪的暗示,也是真实的表达。春花对女工商推销鸡蛋蔬菜又引起了工商的贪婪欲,“我的鸡蛋是家里的土鸡生的,土鸡吃的全是树林的虫子,没有喂一点饲料和激素。我的黄瓜和豆角上的全是农家肥,没有用化肥和农药,绝对生态……”很显然,作者的表达欲望盖过了小说人物的声音,作家的生态情结使他不由自主地借人物之口向读者传达更多的信息。之后春花两次以特殊的方式证明着绿色生态的优异性,第一次对女工商把鸡蛋砸在马路上,“春花猛地抓起一个鸡蛋,对着工商脚前的水泥路面狠劲一摔,啪的一声,蛋清蛋黄四下飞溅,溅得工商的皮鞋裤子上都是,黄灿灿的像婴儿拉的屎巴巴,清兮兮的像感冒人流的鼻涕。春花指着地上的蛋黄蛋清,有理气壮地对工商说:你看看我的鸡蛋里到底有没有苏丹红?说完,又从筐子里取出一根黄瓜,喀嚓一掰两半,咬了一口说:我把这根黄瓜吃了,你看超标农药能不能把我毒死?”描写清脆极了,痛快有力。第二次又在普通市民面前与饲料鸡蛋作对比,以农村真正的绿色生态折服了都市人。作家在这一层次的叙事中,目的并非要解决生态问题,只是为了表现农村生态文明对于都市的巨大优势。表面上是少女们征服了都市群体,实际上是绿色生态。然而,少女们在客观生态的层次取得的成功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土地的绿色生态永远是物化扭曲都市的生命之源。作者要表达的是,农村绿色生态文明对于都市的胜利是与农村少女的卑微身份交织在一起的。为了求得生存,他们还需要在复杂的都市环境中与人周旋。
第二个层次:人的文明的层次
在这一层次,城乡文明的种种对立差异融合是在三个农村女孩与一系列都市人的纠葛中间展开的。小说篇名为《闯城记》,显豁地表达着农村人向城市的突进姿态,她们要征服城市,要在都市中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必然要在面对普通市民、地痞、官僚、商人这些城市人群时,采取种种方式,依托传统的乡村价值理念实现着各自的理想。
性格的不同决定着行为方式的差异,三位主人公正是如此。她们身份的确认,就细微之处而言,是有区别的。夏雨与春花、冬梅有着一点很大的不同即在于,她是接受过都市文明熏染的农村女孩,所以在面对城市官僚阶层人物时,就表现出了非农村的智慧与世故,无论是面对工商人员时的急中生智、以对春花的贬低来获取对方的原谅,还是面对傅主任时的不卑不亢、多谋善断,都显示出弱者在强者面前的生存之道,也是都市中的生存法则;春花与冬梅皆为农村女孩,文化水平相对低,但也有不同。春花是那种倔强粗放的农村姑娘,代表着农村的一种原始野性和反抗意识,所以在对付官僚时就略逊一筹,而在对付城市小流氓时却游刃有余,她以胜利者的姿态征服了都市的一群;冬梅却是青春与纯洁的化身,年龄最小,也最柔弱,作者有意安排让她成为了城市制度的殉道者,批判极为有力(第三层次详论)。三人在对待普通小市民方面,都散发出了农村质朴人性的光辉。在卖菜事件中,三位姑娘以农村文明特有的朴实简单洗涤着都市人的灵魂,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性的复归;但在面对好色商人的金钱诱惑时,他们共同采取了拒斥的态度。
武力与智力,接纳与拒绝,农村文明在向都市文明的进发中采取着多样策略。在面对都市人的时候,农村姑娘们是自信的、自足的、自洁的、自爱的,心灵的健全与充盈,人性的朴实与真挚,智慧的圆熟与力量,仿佛一切尽在她们的掌控之中。但进一步探求,他们在人的层次上的征服充满无奈和悲哀。对不同人物采取了不同态度,如下所示:
对工商人员——自我贬损
对普通市民——以心换心
对城市流氓——以暴制暴
对政府官僚——不卑不亢
对好色商人——婉言拒绝
由此看来,在人的文明的层次上的胜利,除与市民的买卖关系中存在精神的熏染和同化,与其他都市人的关系完全是处在被动的屈辱的位置,她们与他们是异质的两类,无法融合。在这一点上,女孩们的成功与胜利的价值又有多少?
第三个层次:制度的层次
此一层次无疑是作者的重心所在,放在小说结尾,呈现了现实人生深刻的悲剧性。当姑娘们的母亲生病住院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掏耳店转让了,积蓄花光,冬梅也失去了美好的青春;这些都源于钱,更是制度,这里作者的批判是大胆的有力的,却非突然出现。关于制度的叙写在小说的前面都有或明或暗的提示,小说开始,掏耳店“体健身康”的横联对小说的主旨形成某种先在的暗示作用,这是农村姑娘们为城市人提供的保健服务,而在小说最后,农民自身的健康却无法保证,形成强烈的反讽意味。另外在她们掏耳店经营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一名患耳病的幼儿,他的母亲因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而放弃了在医院的治疗,在夏雨们的店里却很轻易地治疗了,有点神,却表达了对医疗体系的无情嘲讽。无论如何,姑娘们终于不能避免不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这只无形之手撕碎她们的理想。小说指向的只是医疗制度,然而城乡的不平等体现在许多方面,于此,朴忠焕《乡村与都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一文有详尽的论述。城市领导农村,城市群体在社会制度方面占尽了优势。[5]对此,农民无语。所以农村在向城市的进发中必然要牺牲掉许多。卡夫卡在《城堡》中寓言了国家制度对人性的无法言说的荒谬束缚[4],而在这里,无情的制度扼杀着富于生命力的健康文明形态。姑娘们此前的一系列成功如此不堪一击,她们可以抵挡住城市商人的无耻诱惑,但面对现行制度却只有举手投降。
沈从文一生中顽强地表达着一种对都市伪善虚饰文明的痛恨和对农村原始人性的热烈赞美,他却很少致力于改造扭曲文明的思索;高晓声在农民小说中表达着特定时代农民对于城市的态度与感情,欣羡与鄙夷,自大与自足;路遥充满深情的执着表达着农村知识青年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追求,迷失与反思;杜光辉在这里却演绎了一个寓言,农村文明在与城市文明的较量中,被现行制度无情摧毁的悲剧,极具现实意义。
《闯城记》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制度的嘲讽,对农民工的同情,在杜光辉的小说创作中不是孤立的。近年以来,杜光辉的许多小说都关注着中国在转轨时期的制度设置,比如中篇小说《杜泓伯的友谊》对官员道德品质和选拔制度的思考;《抢救莉莉和弟弟的运动》对当代收入分配制度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的思考;《内分泌紊乱》对基层权力机关廉洁制度建设的思考;《无名街的男人女人》对新读书无用论与权富袭乘的思考;《洗车场》对制度设置如何帮助贫穷阶层的思考等等。可以说,杜光辉对当代各类制度的关注和思考,在当代作家中是不多的。究其原因,杜光辉曾在专门研究中国转轨经济的单位工作了10年,并担任一家以“反映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变化、重大社会问题、重大社会事件”为办刊宗旨的综合性新闻期刊的总编,对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类矛盾比较熟悉,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们在他的小说中读到了不同于其它小说的东西。
当代文坛,许多作家都和杜光辉一样,强烈关注着这个领域,表达着他们的人文关怀。如尤凤伟的《泥鳅》,孙惠芬的《民工》,项小米的《二的》,荆永鸣的《北京候鸟》,贾平凹的《高兴》,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败坏的都市道德,对于乡土文化格格不入的都市文明深恶痛绝。特别是尤凤伟的《泥鳅》,也叙写了三位在都市中求生存的农村女性,陶凤、寇兰、小齐三个纯朴善良的农村姑娘,经过一番挣扎,最后都陷落在都市里。寇兰为了给丈夫治病被迫走上卖身之路,陶凤在不断的性骚扰中精神失常,小齐也沦为了按摩女,以出卖肉体谋生存。《泥鳅》的故事触目惊心,在人物的蜕变中痛斥着病态无情的都市制度;相对而言,《闯城记》表现得相对含蓄,悲剧刚一产生小说就结束,没有一个令人压抑痛苦的叙事绵延。但他们的精神指向并无不同,其中深厚的人道主义品质令人感动。张语和评论杜光辉小说时,引用了哈金的一段话也许正可以同时用在这些作家身上,“伟大的作家应该用自己的作品预警人类的苦难,洞察和怜悯人类已经发生的苦难,拒绝对人类苦难的遗忘,昭示人类认识自己的苦难并走出苦难,避免未来的苦难,改善人类的未来。”[6]
参考文献:
[1]陈忠实,《文化艺术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雷达,《人性的光辉——读杜光辉》,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22436_75963.html.
[3]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
[4]卡夫卡,《城堡》,王印宝、张小川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
[5]朴忠焕,《乡村与都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2期。
[6]张语和《生态文明的捍卫者》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 BlogID=2570133&PostID=21745552.
(作者单位:琼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注:《闯城记》,中篇小说,原载《时代文学》2010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