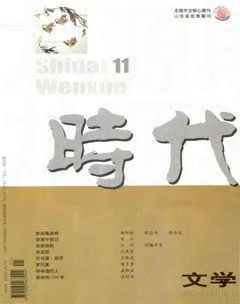《一坛猪油》:迟子健的温情叙事立场
摘要:作家迟子健的《一坛猪油》,是近年来备受好评的短篇叙事佳作。其叙事立场在于恰如其分地运用物的形态,让人物与之接触,演绎人物命运,在叙述中,始终保持着温暧色调,抒写了人性的光芒。
关键词:一坛猪油;迟子健;叙事;审美;人性
迟子健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如果说在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叙事体能的话,迟子健无疑将进入中国当代小说最为出色的行列。无论长、中短各项,她都从容应对,始终保持着叙事的活力。”①爱情和人性是作家作品中的最动人的叙事,本文试从迟子健新创作的一个短篇——《一坛猪油》(原载《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5月号),来审视作家的叙事立场,阐述其文学美学意义。
一、叙事:以“一坛猪油”之物作为作为叙事载体,对生活样态重新审视
近年的小说创作,乡土叙事仍然备受读者关注。一些作家的叙事作品,表现出更开阔的视野,呈现生活的本原状态。小说就是叙事,叙事就要有“事”的生活样态。如何把握新的生活样态,进行有魅力地叙事,迟子健在《一坛猪油》中给我们带来一种清新的叙事味道。在《一坛猪油》中,迟子健以自然、娴熟、轻巧的叙事能力,充满灵性地营造一个具有地域风情特色、温情朴实的乡村世界,其“叙事朴素自然如天籁,感人至深亦如天籁,如有神助般获得了文学感动心灵的巨大能量”②。
作家很巧妙地把“一坛猪油”作为叙事的载体,表现人和物、人和人的关系,自觉而完美地表达了不同时代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人性主题。小说叙述的是在物质匮乏年代关于财富与人性的传奇。在那个年代,农村体力劳动强度高,生活十分清苦。作家把握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即一坛猪油,让它承载以“爱”为主体的真实的农村生活样态,表达对乡村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体察和关注。《一坛猪油》最巧妙之处在于,不仅是写猪油,而是从坛子由外到内,一层一层地写:雪青色的坛子、雪白白的猪油、猪油里埋藏的一枚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让人物与这三样东西相碰撞,演绎人物的命运。
小说一开始,“我”,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以林业工人家属身份,要到丈夫老潘身边。临行前,村里的屠夫霍大眼,用一坛猪油换“我”家的两间泥屋,于是,“我”带着仨孩子、怀里抱着一坛猪油艰难地赶路,由此,与三样宝物相关联的故事就一一发生了。
坛子——成了旅店店主的相思物。“我抱着坛子走进客栈时,店主一眼就相中它了。他问我,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古董啊?我说这不过是只猪油坛子。他嘴里啧啧叫着,在坛子上摸了一把又一把。”店主宁愿以几匹马的代价换下坛子,他说,“好物件和好女人一样,看了让人忘不了!咱没福分娶好女人,身边有个好坛子,也算心里有个惦记的!”
猪油——是“我”对丈夫老潘爱的生命力表达。屠夫霍大眼怕“我”不用泥屋换他的猪油,只说丈夫老潘那地方一年有多半年是冬天,“除了盐水煮黄豆就没别的吃的,难见荤腥。他这一说,我活心了,跟着他去看那坛猪油。”“我”到了丈夫老潘那,用猪油炒野菜,“老潘夹着蚂蚁时,也不挑出,说是蚂蚁浸了一身的油,扔了可惜,连同它一起吃了。到了小岔河没两个月,我怀上了。”后来生下了胖男娃“蚂蚁”。
金戒指——测试爱情纯度的试金石。猪油里藏着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载着三个爱情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崔大林。崔大林私藏了猪油里里金戒指,一个女教师看中了这宝物嫁给他,他得到的失真的爱情,夫妻生活不顺,妻子在江边洗衣时丢失了戒指走上了绝路。一时的贪念,竟给他带来一生的折磨。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儿子“蚂蚁”。蚂蚁”长大后,在江上放排,和江对面的苏联姑娘一见钟情,并且接受了姑娘的信物。因为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他只能隔江遥望,在江这边洗澡摸鱼,结果在摸到一条大鱼肚里发现了崔大林老婆的那枚戒指,就将它还给崔大林,崔大林反而不敢要。“蚂蚁”就揣着它越界到苏联,去兑现那个美好爱情的诺言。第三个故事是屠夫霍大眼对“我”一生的暗恋。当“我”得最终得知是他把金戒指藏在猪油里,无不感到心酸和感动。
《一坛猪油》的叙事,就是这样对坛子由表及里,让每一样美好的东西,与人物的婚姻、爱情、家庭产生撞击,并“将传统的道德伦理埋藏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借助漫长的时光一步步地淘洗出来”让我们从中近距离地看到人物心性状态,并使我们对人物的命运产生关注和对生活原状的美好想像。
二、技巧:暗示、悬念、叙事语态,给作品增添了传奇性和文学魅力
暗示是中国传统小说婉曲的修辞手法,说话人用一些含混、隐约、闪烁的话来暗示本来的意思。婉曲的好处在于婉转曲折,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在《一坛猪油》的叙述过程中,作家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给人物性格发展以众多的暗示,给读者以一种含蓄的叙事美感,回味无穷。小说是有两种类型的暗示非常精彩,一种人物的行为暗示,例如:“我抱着坛子走进客栈时,店主一眼就相中它了。他问我,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古董啊?”,这个暗示,店主明着欣赏坛子,实际上是含蓄地欣赏这坛子的主人,包括店主为了买下坛子所作的努力。另一种暗示,是借助地方风俗,将人的命运赋予的必然性色彩。迟子健相信生命是有去处的,人的命运是有事物的暗示的,这完全符合原生状态下的人们期望的现实。作家在叙述崔大林结婚后的命运时,先以地方风俗“压床”作为暗示。“所谓‘压床’,就是找一个童子,陪新郎倌睡上一夜。据说这样婚床才是干净的。”“蚂蚁没压好床,崔大林说,这孩子突然肚子疼,哼唷了一宿。”这个暗示正由崔大林贪得金戒指而来,有一种神秘性效果。
悬念是指作家为了激活读者的急切期待的心情在叙述方式上采取技巧。它包括“设悬”和“释悬”两个方面。通俗地说,它是故事发展中间只亮开谜面,藏起谜底,在适当的时候再予点破,使读者的期待心理得到满足。《一坛猪油》里的悬念设置众多,有时与暗示交织重叠。小说中最大的悬念是霍大眼在猪油坛子里藏了金戒指,早在用猪油换房子时,“霍大眼他嘱咐我,不能把猪油送给别人吃,谁想舀个一勺两勺也不行,一定要自己留着,因为这坛猪油他是专为我准备的。”即霍大眼对“我”的用心。作家在叙述完一坛猪油及里面的宝物和多个人物接触之后,才通过崔大林说出那个让自己备受折磨的金戒指的秘密,那枚金戒指本不是他,是那坛猪油里藏着的,是霍大眼送给“我”的,这个出人意料之处的秘密,经历漫长的时间,使霍大眼对“我”暗恋行为有最充分的解释,也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作家选择自叙式的叙事语态,即我“讲述我”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正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及魅力所在,容易把一些散落的故事连缀起来,增强主人公故事的整体感。此外,以女性第一人称叙事,呈现了女性特有的从容不迫的叙事性格和温存软语的叙述风格,使叙述语言更有温馨妩媚的质感。
三、审美:在特定生存状态下观察人的本源道德,演绎着人物最自然、最朴实的美感
迟子健善于在特定生存状态下观察人的本源道德,也的小说“信奉着小说的最原始、最本源的道德与伦理,始终演绎着小说最自然、最朴实的美感。③”小人物和平民生活永远是她叙述的主角。她既写了人生存的艰难,也写人性的善与真。《一坛猪油》是放在物质贫乏的时代背景下的农村寻常百姓生活叙事,叙述了数个人物在《一坛猪油》物质刺激下的内心挣扎和超脱。作家借此表达世俗关怀和人性的呵护,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审美趣味。
人物理想和道德的二重结构。例如小说中所叙述和刻画的旅店店主的性格形象,是含蓄和耐人寻味的。在旅店店主看来,那雪青色的坛子,是妩媚、风韵佼好的农村好女人的化身。在他的意识中,好物件就和好女人一样,所以要不惜代价连坛子和猪油全部买下来,在“我”不肯卖坛子的情况下,店主内心经历痛苦的煎熬,以至于他老婆自伤不想活。但是,传统道德给了店主以理性的处世态度,一是“我” 的矜持,“我”不是那么轻浮的人,不是那样把心爱之物不当一回事;其次是由于店主的老婆表现出中国传统妇女的忍辱负重和宽容。“店主听说他老婆下跪是为了给他要坛子时,受感动了……好看的东西都是惹祸精,咱不要那个玩意儿了,你快抱着走吧。他嘴上这么说,可他看坛子的眼神还是留恋的。”因此,店主再看着坛子,都能感受到清澈见底的温情,想得到它却不会有邪念,这正是“我”带着青草味儿的清香,净化了一个男人心灵。因此,店主之恋,是一种无奈的想像和自我解脱,自我感到精神满足。即使有忧伤的成分,那也是一种轻柔的美丽,至少在他心灵之中闪过一道霓虹,从而使他对生活有更多好的念想。
“温暖”在迟子健的小说世界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也是运用最为广泛的命题。这种创作立场有点像铁凝所说的那种:“值得我怀念的不仅仅是那种原始相互的记忆,那些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却成为了我生活和文学永恒不变的底色,那里有一种对人生深沉的体贴,有一种凛然的情义。”④“‘温暖’对迟子健而言是放大了的世界观、审美观,它既是审视世界的眼睛,又是理解世界的观念;它既是善的取暖器,又是对恶的不满和排斥,是批判的武器又是武器的批判。在这个世界上,‘温暖’不仅仅是人对自身的信念,人与人的关系图,而且也是维系人对自然、对天地、对动物乃至对物件的信念。”⑤在《一坛猪油》中,所有的叙述,都有一种天然的人性温情表达,例如:“这只坛子呢,天生就带着股勾魂儿的劲儿,不仅颜色和光泽漂亮,身形也是美的。它有一尺来高,两拃来宽,肚子微微凸着,像是女人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它的勒口是明黄色的,就像戴着个金项圈,喜气洋洋的。”沾了青草和蚂蚁的”猪油,滋润着爱情,复苏丈夫老潘激昂旺盛的生命力,演绎生命的激情,“老潘说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正是这些以“我”的自觉的人性体察,才得以把持住女性特有的满足心理和幸福感。作家叙述人物间的关系,没有仇恨,只有理解、尊重、温情、和心灵的慰藉。 “蚂蚁”敢于越过国界去寻找爱情去了,“到了冬天封江时,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想着蚂蚁一定是平安过去了,跟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即使小说中对崔大林的贪婪,也是最终给予宽容的态度,因为在叙述崔大林的命运过程中,崔大林经历内心的苦苦挣扎,在物欲面前,修补了人格,完成了个人道德的自我救赎,“崔大林抓着我的手,哭得像个泪人,说,潘大嫂,这戒指命该是你的,我说什么也不能要。它要是再回到我家,我非死了不可!我说,这东西这么金贵,不是我的,我不能要。”“在老潘的葬礼上,崔大林把折磨了他半生的秘密告诉了我。”一个大悬念让“我”一枚戒指是一颗真诚的心,也是一种道德的符号。霍大眼对“我” 一生的暗恋,正是附在一枚戒指上的温情话语,世间还可以和生命的过程相伴、值得珍藏一生的爱恋。由此,小说在最后才达到极致的高潮,“我”和读者我们,在无奈、震撼之余,更多的是在是心灵深处升腾起来的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似乎找到了作家的精神原乡。
注释:
①⑤程德培.魂系彼岸的此岸的叙事——论迟子健的小说.《上海文学》,2009年第8期。
②张懿红.回归自然:迟子建的终极乡土.《当代文坛》 2007年第6期。
③吴义勤.迟子健论.《钟山》2007年第4期。
④铁凝.文学是灯.《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迟子健.《一坛猪油》[M].《2008年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09,1,131-145。
[2]林建法.《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9年文学批评》[M].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1,222,337-354。
[3]孟繁华.当代文学:农村与乡土的两次历史演变[N] 《文艺报》2009-08-060 s5 C; U- 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