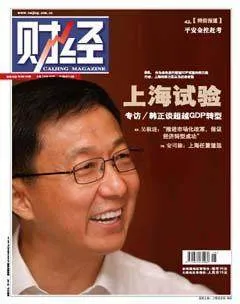大变革前的理论苍白
其实。“包产到户”不是什么新东西。1953年农村开始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始终在中共领导人眼前晃动。这是农民的本能但要找到承认农民创新之正当性的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并不容易
政治禁忌
王贵宸,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今农村发展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从1 949年参加工作开始就在农口工作,此后中国农村经历的所有波澜,他基本都经历过。只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他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60年代,他心中有了怀疑和苦闷,70年代,他在“又革”中经历被批判斗争,到80年代初,他开始明确立场:站在中国农民一边,支持包产到户。
根据他的总结,从1956年到1957年,刚刚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中国农村,就出现第一波包产到户,当时在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广西、广东、山西、河南各省都有。特别是浙江的永嘉和广西的环江,如果说上述地区的包产到户还都是农民的自发行为,这两个地方则是在县一级领导机关的直接领导和总结经验下进行的。但1957年,中共中央给出了判定:此为方向性错误。
第二波包产到户发生在1959年。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南、江苏、湖南、甘肃等省出现混乱,1959年春“整社”后这些省份出现包产到户。这一次,农民们得到了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支持,但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遭到压制。
接下来,是1961年到1962年的第三次包产到户潮。这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其中较典型的是安徽的“责任田”。
1960年,安徽农村经济几近崩溃,当年人口比上年净减384万。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曾希圣,他大胆主持了“责任田”的试点和推广,其要点实际是“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年底,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1%。试验效果非常惊人,当年全省粮食产量增长将近30%。此举本来得到最高层批准,当年任曾希圣秘书的陆德生回忆道:“毛主席原来说,安徽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了。结果翻了几番。”然而,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定义为“有方向错误”,曾希圣被撤了职,责任田随之全面夭折。
这一波包产到户引发中共高层斗争。4月初,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派人到安徽调查,得出结论:一些地方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就应该让农民搞。这些成为他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遭受批判的缘由。邓被撤职,而当时,杜润生就是邓子恢的部下,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中共党内的这种政治气氛,王贵宸深谙其情。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记忆犹新:有一次传达中央又件,讲陶铸等人去广西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分析了几种情况,提出包产到户搞不好很可能会滑到单干。“我当时站起来发言谈看法,觉得包产到户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说得通的。当然,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也讲了很多前提条件。当时并没有人对我的发言发表意见。”
但是后来运动一来,有人就将王贵宸以前关于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说法都整理出来,贴成大字报。“又革”中,王贵宸被“揪出来”批斗,罪名是两个:一是反对人民公社,二是主张包产到户。
因此,在经历了多年政治风波冲刷之后,即便到了1978年前后,在中共党内,是否“包产到户”仍是个禁忌的话题,因为它跟“走社会主义道路”联为一体。
激辩之年
农民也知道这个政治禁忌,但是,他们要生存。尤其是安徽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责任田有深刻记忆,它在民间的另一个叫法,是“救命田”。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秋种根本播不下去,眼看农民将无粮可吃,官员们都发了慌。当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子。
农民和基层干部由此马上就联想到“包产到户”。被人称为“汤大胆”的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振林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全体党员会上传达省委精神时就决定“得寸进尺”,干脆把全部土地拿来实行“责任田”制度。为躲避政治风险,他们编造了一个又绉绉的名称:“四奖一定”,其实就是包产到户。
“四奖一定”很快从黄花大队传播到整个山南区,来年2月又席卷整个肥西县,随后向安徽其他地区蔓廷。大名鼎鼎的凤阳小岗村农民则在此基础上再迈出一步。在1978年3月,凤阳已经出现了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到冬天,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比“联产计酬”和“四奖一定”来得更为彻底干脆。
安徽农民的做法引来全国的记者纷纷到此采访,当年的地委书记王郁昭回忆说,新华社曾经一下子来了国内部、国际部、社教部、摄影部等1 2个部的主任,其中11位表示赞成包产到户,只有一位持保留态度。
但是在中共高层,态度可没有这么一边倒。1979年成为中共党内对农村政策争论最激烈的一年。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包括安徽在内的七省农委负责人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时任安徽省委政研室主任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周日礼代表安徽出席。听到周日礼发言谈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他打起来,会上争论激烈,反对者言:这是“分田单干”!而且反对者自了大多数。
因为双方意见争执不下,很罕见的,这次会议的纪要搞了两份,国家农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单独又起草了一份。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来听汇报,听到安徽这边还有个纪要,而且赞成包产到户,不禁有些惊讶,急忙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与安徽省委联系,问这是怎么回事。
周日礼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只见王任重出去了。后来知道他出去是打电话找万里,打了很长时间。他问,你们安徽摘包产到户到底搞到了多少,你们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吹特吹包产到户,这些你们知道不知道?万里说,知道,周日礼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见省委已讨论过了。”
那天的汇报从下午3点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半。最后,这个会议的纪要,把周日礼讲的主要内容都用了进去,但打了折扣:包产到户在偏远地方、独家独户的地方或贫穷的山区可以搞。然而,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又件中为包产到户
1980年1月10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王贵宸也在会场上。周日礼上台发言,原定每人准备15分钟的讲话稿,他一上去就讲了两个半小时。这时他看看手表,对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说,我的时间到了。杜也看看表,说,还有半小时,你把它包干了吧!
这三个小时的发言,让会场炸了锅。在华东组,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各省的到会代表都不赞成安徽的做法。“我记得江苏、浙江两个省都不同意包产到户,理由是省情不一样,你要是搞的话将会影响到我们,这就像瘟疫病一样,我们不得不管。”王贵宸回忆道。
“最后是总结会议,杜润生主持会议,传达华国锋的讲话。基本调子是不同意包产到户。他又传达农委的意见:‘因为搞集体化后,我们农民吃了很多苦头,要求包产到户,我们是很谅解的,但是不得不提醒另外一些同志,你们不要逼我们再来一次反对单干风’。”传达完后,杜润生一句话没说,只说两字:散会。但很显然,杜润生对包产到户是另有看法的。
空谷足音
这个时候,关于农村的思想、政策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一方面,农民和部分基层干部为了解决农民生存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大胆地突破了原有的土地公有、集体经营的政治禁忌,一些地方高级干部表示支持。省一级领导公开站出来支持包产到户的,除了安徽的万里,还有贵州的池必卿。在高层,有人已经准备支持这种变革,但另一方面,从中央各级政府内部,也有一支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反对变革。
而在理论界,尤其是在官方的智囊中,后者占据优势。1980年,高层不同部门分别派出六七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包产到户。据王贵宸记忆,“只有我们一家支持包产到户。”体制内的智囊们经历过长期而残酷的政治斗争,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虽然知道,现有的体制千疮百孔,但在最高领导发话之前,他们不愿说半句出格的话。
王贵宸说的“我们一家”是由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所派出,一共去了三个人:人民公社室主任王贵宸、研究人员魏道南、陈一谘,在1980年的春夏之际成行。在此之前,安徽政协委员郭崇毅到北京找过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与陈一谘会过面。
陈一谘在见过郭崇毅的当天晚上,他把郭带来的材料转给邓力群一份、胡耀邦一份。据陈一谘事后的回忆,两位领导人都做了批示并转发。然后,就有了调查。
王贵宸回忆起那次调查的情况:“那时,万里已经从安徽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了。安徽省换了第一把手,气氛已经不太一样。省里的大概情况是,万里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就接着搞下去,但没有搞的地方,就最好不要再搞新的。”而农民则坚决要求继续实行包产到户政策。
他们在安徽做了三个月的调查。在安徽调查和回来写报告的过程中,陈一谘都是包产到户最坚定的支持者。回来以后,王贵宸接到了杜润生的电话。杜说:我们要组织人下去调查包产到户,你们农经所也出一个组。王贵宸说,我们刚从安徽回来,正在写报告。杜说:你们写吧,就算是我们先派出的组。“8月份我们写出了这个报告。不久他(指杜润生)安排的另一个组也下去调查了。”王贵宸说。
这个报告,就是王、魏、陈三人署名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它后来在为包产到户正名、推进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
而王贵宸提到的“杜润生安排的另一个组”,就是由陈一谘身边的那群青年朋友们组成的。王贵宸形容,“多数都是干部子弟,在农村插过队的。派他们去,是上边有这个意思,他们叫发展组。”他们的作用马上就被高层注意到了。(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