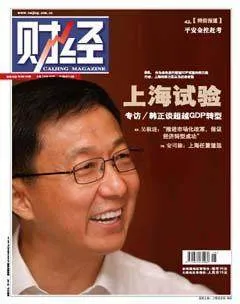20世纪中国之“我”与“他”
中国近代史反复转折经过一个半世纪,中国才进入国际社会,中国文化也将融入世界文化。这一过程,迂回曲折,若从“我者”与“他者”的相对性而言,竟是“我者”与“他者”的调换,将中国原有的文化,化“他”为“我”,弃“我”为“他”。这在中国历史上,毋宁是仅见的深远变化。
20世纪前30年,中国努力进入世界,但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历史太长久;中国选择了转舵向西,但不过是城市与精英的中国在转向,另一个中国,乡村与基层的中国却还是转不过来。
这一自我撕裂的过程,如果没有其他的干扰因素,中国仍有可能终于慢慢全部调转方向。然而日本侵略中国,东南及沿海城市沦陷。国民政府努力以赴的“现代化”,经过八年抗战,原来建构在都市与精英之上的结构,脱离了植根的土壤。不但八年苦战,民穷财尽,那一个辛苦转向的中国也失血太多,在抗战惨胜时,已是奄奄一息。
另一方面,广大的敌后内地乡村,留在乡间的现代文化资源并不丰厚,也切断了与内迁上层结构的联系。在经济方面,退缩到基本农业与小区域的交换;在社会方面,也回到乡党邻里的集合体,现代文化已无托根之地。中国本来已是一分为二,但还没有分离。八年抗战,中国真的分裂了。那一个先天并不壮硕的城市中国,或是在敌人占领之下,或是离根内迁,难以发展。
在那裂碎为一片一片的乡村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口号,将广大中国人民的保乡观念,转化为民族主义,取得重组中国那一半的机缘,并在地方集合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集合体,终于将中国改造为统御全民的庞大集合体。这一重新塑造的乡村中国,在国共内战中,压倒了已经为大战摧残的城市中国。这一转变,在共产党统一中国后,中国人的“我者”,已由国族认同界定;“他者”则是长期欺压中国的西方。即使同样是社会主义政权统治的苏俄,也只是短暂的友人,终究还是归入“他者”之内。
两三个世代了,抗日的记忆犹新,中国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官方与民司共有的情绪,使无数中国人为了“中国”,矢志靡它。巨大的“我者”,也将许多归入异类的个人清除改造,不让“五四”取诸西方的“主义”有孕育的机会,以防范那些“他者”余烬有再燃的机会。
而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毋宁是抹去了前面30年的中断。市场经济的开展,使那一个几乎绝灭的城市中国又复活,而且以无比的动能,扩大及于大片的内陆,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历史正在消长之际,1949年至1978年司的乡村中国,正在让位于今天的城市中国。一旦两者易位,则“我他”之司,也将有相应的转换。
在台湾,“我他”的对立,在于不少本土居民要求确认自己的主体性,而与坚守中国认同的另一部分人口有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与日本占台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与迁台的政权难以切开。于是认同问题与争夺政权,纠缠为台湾内部的对立。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台湾本土论的立论根据十分薄弱,其居民的文化根源,依旧是中国文化;族群血统,也绝大多数是闽粤移民的子孙;南岛原居民,只占少数而已。这一类的“我他”与主客争议,在全球化浪潮下,是另一股逆向的潮流。在世界别处,也多有类似争议,整体而言,其应是全球化走向“合”的趋势中难免的枝节。
今天的中国文化,已有深刻的变化。以日常生活方式言,除了饮食之外,也已华洋相杂。在思想方面,儒道佛三家综合的中国式思维方式,早已稀释于强大的西潮,相对言之,这一原为中国文化主流的思想系统,千百年来淀积于民司的枝节,却仍留在各处华人的行为、仪节,以至思维之中,例如互补的二元论(阴阳、公私、荣枯)。只是大多数人往往行之若素,未经反省而已。
在价值取向方面,传统的整体主义(宗、族、乡、国)与今天普及全球的个人主义(人权、自由……)之间,在我们的行为中处处有碰壁,却也人人可以找到自己以为适当的调和。在西方价值观俨然已是主流的世界中,中国人如此地寻求调适,是值得密切注意的现象。
各处中国人社会中的精英,应当因应这一现象,认真思考,或能有意识地导引,发动大家,合作进行深度的反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成分,挹注于有待我们合力缔造的全球人类共同文化。
如能做到这一巨大而持久的任务,则中国与今天的主流文化之间,将不必有“我-他”与“主-客”的分别,而是从矛盾中,辩证式地跻登更高阶的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