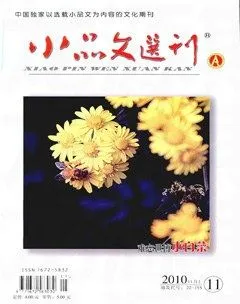印在泥土上
我从没见过我的奶奶,连照片也没有,当年妈妈过门时,奶奶已经去世六年了。
偶尔地,我会想像奶奶的模样,这个给予了我生命的人,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定像我在电视里千百次看见过的农村妇女一样,粗布衣裳、糙黄脸庞、关节粗大的双手,她们瘦弱单薄,仿佛一阵从庄稼地边上刮来的风就能扬跑她们,像扬走一粒麦粒,然后,在别的地方,继续生根发芽。
然而,爸爸和爷爷却告诉我,奶奶长得像舅公,像到了骨子里。
那不是一张美丽的脸,甚至也远远算不上清秀,倒有些像我在科普片中看到的原始人头像,颚骨高突,牙齿发达地顶起薄干的嘴唇,撑得整张脸如同我故乡连绵起伏的山岭。
半个多世纪前,我的奶奶带着这张脸进了爷爷家的门,媒妁之约,她一定还有些害羞,新婚夜里,头就快要低到尘土里去。我的爷爷,也一定紧张又迷茫,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将给他带来什么。
可是第二天,我的奶奶就脱下大红的新娘装下了地,扛着锄头背着萝筐,一个上午下来,一块庄稼地在她手里被锄得舒展漂亮,中午,地头的爷爷还吃到了滚烫的汤饭,他长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一切还未开始就已结束,一切还未结束就已开始,并将永远继续。
村里人后来跟我回忆,你的奶奶平生就做了两件事,做农活,怀孕,连对面镇上的集市都没去赶过。
油灯如豆、长夜如兽,昏暗简陋的屋里,草渣和黄泥敷就的墙壁上,夜夜印着两个人的影子。队里的活计刚放下,奶奶又拿起了自家的活计,她在缝一件小衣裳,针脚紧密而细腻,油灯的光有些晃,她下意识地凑近了,觉得清晰了些,眼睛里闪的光补充了一部分油灯的不足,她必须尽快了,肚里的孩子欢腾地踢蹬着她,奶奶嗔怪地拍了拍肚皮,又望了墙角处收拾大葱的爷爷一眼,手中的花花绿绿大大小小拼凑起来的布块,安静而服贴,变戏法般成了一朵欲开的花。
乡村的夜总是宁静的,静得让人安分守己。
我不知道奶奶挺着肚子的模样。没有人向我描述,似乎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村里的女人后来对我说,你奶奶想吃糖,身怀六甲,有一天早上,刚打完猪草回来,她突然念着想吃糖,说嘴巴苦,那个时候哪有糖啊,你爷爷狠命,有钱也不给她买。她念了两句也就不吭声了,转身进了灶房剁猪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