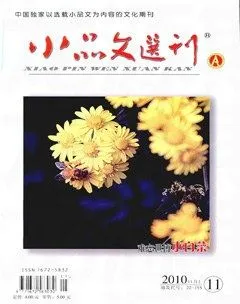生命的一抹
清晨,伴着“沙沙”的雨声醒来。
我蜷缩在床上,眼睛却眺望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深褐色的秃树干。尽管屋里依然是冬天那一种暖暖的干燥的热气,但我可以预感,房间外边已是早春的湿湿润润的气息了。
迅速起床,推开阳台上的窗户。果然,一股湿淋淋的由土地呼出来的雨水的味道沁入干燥的肺腑,我感到所有沉睡一冬的小虫子肯定都会在这个雨雾蒙蒙的清晨睁开眼睛。
阳台上的龟背竹又长出了嫩绿的新芽。回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浑然一体的宁静的气息了,甚至,已经几年没有看见早春时节街道两旁满眼的树木是如何发芽抽叶的了。一直以来,城市的噪音、人群的纷争以及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的压力,使我对身边这些安宁的事物几乎视而不见。不知是这第一场春雨,还是什么莫名的奇怪的引力,这会儿我终于重新看见了它们,一时间,竟恍若隔世,惊叹自己何以多时以来浑然不知?
其实,此时天地万物的和谐之感,首先是缘自我近日内心的安静。
这几天,我感到一股奇妙的安静的力量在内心里生长,它们先是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进而渐渐成形,然后它们成为一股清晰而强有力的存在——那是一团沉默的声音,它们一点一点地侵蚀、覆盖了我身体里的那些嘈杂,然后一直涌到我的唇边、涌到我的指尖上来。我清晰地听到了它们。这样,我的唇边和指尖都挂满丰沛的语言。我无须说话,无须表达。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同我此刻一样恬静,你就会听到它们。
由于它们的存在,当我独自一人对着墙壁依桌静坐的时候,我的眼前不再是一堵封闭的墙,相反,我的视野相当辽阔,仿佛面对的是一片丰富多彩的广袤景观,让人目不暇接,脑子里的线路与外部世界的信号繁忙地应接不断。而当我置身于众多的人群中,却又如同独处一室,仿佛四周空空荡荡什么都不复存在,来自身体内部的声音密集地布满我的双眼。
这感觉的确相当奇妙,但外人却难以察觉。它似乎是一种回家了的感觉,也似乎是复苏了的感觉。以前很多时候,人在外面,在茫茫人群里,嘴和脚是动着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心脏和血液几乎是死的。而此刻,尽管肢体一动不动,但心脏和血液却都活了起来。
多么美好!
桌上的这一页白纸,几天前它就空洞地展开着,张着嘴等待我去填充,如同一个空虚的朋友,饥饿地等待着灌输。然而现在,我对它依然不置一词,可这张白纸却分明在我的眼睛里忽然涂满了字,充满了内容。
电话机安静地卧着,像一只睡着的小动物。但是,它的线路却时时刻刻在我和我的对话者之间无声地接通着,我无须拿起话筒,交谈依然存在。
泰伊的《弥撒曲》远远地徐徐地飘来,其实我并没有打开音响,那声音的按钮潜藏在我的脑中,只需一想,那乐声便从我的脚尖升起。我甚至不是用耳朵倾听,而是用全身的皮肤倾听。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我一个人倚坐在沙发里,看着室内橙黄色的灯光与窗外正在变得浓稠的暮色,看着它们小心翼翼地约会在玻璃窗上,挤在那儿交头接耳。再仔细倾听,窗外的晚风似乎也在絮絮低语,间断掉落的树叶如同一个个逗号,切割着那些凌空漫舞的句子。
……
你肯定有过这样的感觉。
这种时刻,所有的嘈杂纷争、抑郁怨忿,甚至心比天高的欲望,全都悄然退去了,宁静、富足,甚至幸福感便会从你的心里盈盈升起。
选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