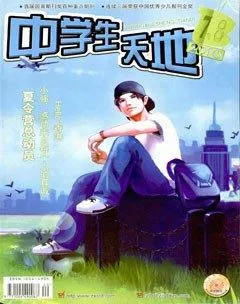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
在准备这个题目时,我一直在思索,我们生活全球化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们的洗发水、服饰、家具、汽车等商品已经全球统一,连城市的样子都日趋一致了。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香港、台北甚至纽约。马路边的路灯、公车站牌、广告和人行道设计等都大同小异。都市的景观与建筑通过国际竞标,由少数全球知名的建筑师与开发商运作,造就了面貌相似的大城市。
衣食住行如此,艺术就不一样吗?你去美术馆看一个新的当代艺术展,它很可能是一个多媒体的影音展:用录像机、照相机摄下现代感十足的光怪陆离的人生影像,你觉得很有意思。但如果这种展看多了——譬如你看过意大利威尼斯展、巴西圣保罗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展、德国卡赛尔展、韩国光州展等等,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尽管艺术家不同、地理位置和国家文化不同,怎么对“现代”的解释却大同小异、似曾相识?
看完展览之后。你也许还有时间逛逛书店。进门大概就能看到《哈利·波特》,在香港和台北是繁体中文版,在北京是简体中文版,在柏林会看到德文版。晚上,你也许想看个电影。要避开好莱坞可不容易,《阿凡达》在马来西亚的乡下都看得见,有如麦当劳的标准菜单完全“全球同步”,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梁启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谈的是“西学东渐”,西方的影响刚刚来到门口,人们要决定的是究竟该敞开门让它全部进来,还是只露一条缝让它慢慢进来。在100年后的今天,西学已经不是一个“渐”不“渐”的问题,它已经渗透到我们最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了。
然而什么是“全球化”呢?影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什么力量在“转化”,谁又被谁“化”掉?渗透到我们生活里的,难道是印度、埃及或阿拉伯的影响吗?不是的。仔细看你会发现,代表全球化的东西中99%是西方的。再细看西化的内容,其中又有非常高的比例来自美国,对我们而言,所谓“全球化”很大程度是一种“美国化”的过程。
全球化其实挟带了大量的美国化,许多欧洲人对全球化也是戒慎恐惧的,激进者甚至于诉诸暴力对他们认为象征全球化的符号一星巴克、元首高峰会议、麦当劳等进行抗争。人们所忧虑的,一方面是资源的垄断——韩国甚至有农民以自杀来凸显全球化所带来的本土产业问题;一方面是价值的垄断—美国价值观被包装成为商品,随着跨国企业的操作,威胁到了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对全球化第一次发生戒心是在刚到美国时。在台湾读大学时,教英语的美国教师要求我们取一个英文名字,因为她可记不得几十个中文名字,于是一整班的学生都变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
到了美国,我开始教美国学生英文写作。面对二三十个美国学生,很难记得谁是谁,我花了一整个下午把人名和脸对应起来,认得了。于是我回想,为什么教我的老师没把我们的中文名字记住。反而让50个人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吗?有了这个认识之后,Shidey从此消失,被“Lung Ying-tai”取代,而且不是“Yingtai Lung”。23岁的我认定,美国人也可以学着发中国名字的音,学着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脸,学着尊重中国人是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
那时我还没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但是对于所谓文化“交流”事实上是“流”而不“交”的现象,已经有所警惕。我这一代几乎是看洋书长大的一代。当我去开国际笔会的时候发现,我可以和各国作家谈莎士比亚、歌德、海明威,但是不能谈庄子、曹雪芹或张爱玲,因为文化商品大半是单向输出的。
在法兰克福,我想买本德文版的《道德经》给孩子,走进当地最大的书店,从哲学部到文学部再到政治学部,都找不到。最后在哪里找到呢?神秘学部!老庄孔子的书和风水、生肖、气功、太极拳放在一起,作为同类商品。我们的书店会把柏拉图与占星术归为一类吗?不会。但我们有可能把非洲最严肃的小说和“食人族奇谭”放在一起。不是吗?
我曾遇见一名印度作家,谈起年轻时知识的启蒙过程,发现我们都是美国新闻处的“受惠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里,美国政府透过组织和金钱,有计划地将美国价值观全球输出。你说它不好吗,对于我们民主开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贡献的;说它好吗。它又包藏着其他目的,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不是一直呼吁要国际化吗,为什么对全球化又不能一心的拥抱?
国际化与全球化之间有着非常关键的差别。全球化,在我的理解。是商品——包括物质和精神商品——的无远弗届,身处亚洲的我们往往是那输入的一端,当然要无比谨慎。国际化,是对于国际有深入的了解,从而发展出一种与国际沟通和接轨的能力。
当你进入香港的网页,你发现它用老练的英语、生动的画面、完整的资讯,很有效地让外人马上认识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它的特点,哪里好玩好吃,哪里可以带孩子去。进入香港机场,视线所及之处是精美的巨幅广告,活泼的英语告示,现代感十足的商店,完善的路线指标……营造出一种兴高采烈的气氛,告诉你“香港是亚洲的世界之都,我们欢迎你”。
其实就文化内涵而言,香港是最薄弱的。相较之下,北京的历史文物最丰富,台北的当代文化最活跃,但观光客与人口的比例,香港却是最高的。我们说香港最国际化,因为它比较懂得用国际的语言和手段呈现自己。
国际化是一种呈现的能力。但不要误会,把它当作表面的包装和营销。比如学习英语,一个把文法学得烂熟、语汇背得超多的人,不见得会使用英语,因为语言的背后藏着习俗和价值;不懂得这些习俗和价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门语言的。同样,当我们懂得国际的呈现方法。一定意味着懂得国际的内涵——文化的问题、政治的发展、市场的运作、竞争生态的改变、新思潮的涌现等。只有这样才可能知道如何呈现,可以达到目的。
一个让人看得懂的网页、一个让人觉得亲切的机场,一个城市让人看得见它的美好、认得出它的特别,都是“轨”接得好不好的问题。接轨的真正含义,是把自己的轨道和别人的接上,以便于将自己的货物输出。轨道与国际一致,火车里的货物却独此一家,否则谁要你的输出呢?
道理何其简单:谁要你模仿的、次等的、没有特色的东西呢?巴黎要跟纽约竞争,会把自己的老房子拆了去建和纽约一样的高楼大厦吗?人们不辞千里来看北京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来看北京的超现代高楼,或者法国人设计的模仿巴黎香榭丽舍的王府井吗?
我们的建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词汇。我们把土地和城市提供出来,让别人实验他的词汇,驰骋他的想象。我们的文学,有一点国际输出,可是其中有相当的比例不是汉语的精华,而是满足他人猎奇心理的投其所好。我们的视觉艺术要界定自己的“当代”还有困难。我们要对自己非常苛刻地追问。培育“当代中国”艺术花朵的土壤在哪里?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林怀民接受的是美国现代舞的训练,开始回到台湾创建舞团时,他就清楚了自己的位置:“我如果只是跟着美国这样走下去的话,到最后就只不过是一个现代舞团罢了。”于是他开始深入中国的古典和台湾的生活:京剧、楚辞、太极拳、书法、台湾本土诞生的历史、乡土信仰里的“怪力乱神”……最优雅古典的和最生猛原始的,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经过现代舞的诠释上了舞台。
云门舞集成为蜚声国际的亚洲舞团,与柏林、纽约、伦敦等各色舞团进行激烈的国际竞争,头角峥嵘。云门一年12个月国际邀约不断,两年后的档期都已排满,它在国际的轨道上奔驰,但火车里载的,可不是美国现代舞的模仿,也不是卖弄的东方情调。它所输出的内容有楚辞、太极拳、行草书法、红楼梦,有闽南人的悲欢离合、信仰与失落,也有欧美的现代元素,综合吐纳出一个属于林怀民自己的“当代”。
传统永远是活的,只是看当代的人有没有自己的眼睛,活泼大胆的想象力,去重新发现它,认识它。在全球化排山倒海而来时,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我们找不找得到铁轨与铁轨衔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旧的与新的那个微妙的衔接点,找到了那个点,大概就可以在全球化的大浪里,找到真正安身立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