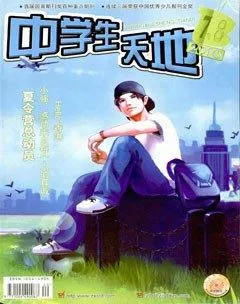月河
我回来了。
十年之后,我又一次站在这座桥的最高处,注视整个世界。
如从前般倚着桥栏那头被岁月磨灭了面容的石狮,我静静地感受脚下潺潺的流水。阳光落在水面上化作点点波光,被河水无情地碾成碎片,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让我想起小时候把金黄色的糖纸捏成一团的画面。
是我长高了,或是房子都被夷为平地了,我看到一幅比从前更开阔的图景。注视着左边的一片寂静,右耳是人声喧闹,我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儿。不远处,父亲和几位老人指点着几座空房子,寻觅着十年前生活残留的气息,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出遥远的人和事,又似乎就在嘴边一样亲切。
我似乎发现了介于过往和当下之间最恰当的角度。
房子没有拆,作了些修缮,然后作为江南古街向公众开放。旧弄堂里铺了新的石板路,不是像从前那样,走过就会发出声响。阁楼里装了新的雕花木窗,紧紧地锁住了通入阳光的隧道。新刷的油漆味道代替了记忆中的松香味,让我的鼻子很不好受。高高翘着的檐角,滴着冰水在阳光下闪着泪花,像是看到多年不见的老友后激动得无法克制的古稀老人。我想象着后面是否躲了一只古怪睥气的黑猫,有目光一样明亮的双眸,踏着春日乱长的青苔。徘徊。
走到正门口,发现这是一家酒楼,灯笼和春联增添了年味儿。食客挺多的,热闹地吃着,围坐在八仙桌旁。布景远比我的记忆更久远了,铜水壶、青瓷碗、披着毛巾带瓜皮帽的店小二,还有墙面上的泼墨山水画。我的记忆中没有这些,没有风雅悠闲,只是人间烟火而已。
“奶奶,我回来了!”我总是第一个冲出学校,背着书包一路穿过几个小弄堂,直奔明亮处的天井。奶奶剥着豆瓣,和几个老婆婆聊天,淘米的阿姨把水笼头腾出来,示意我去洗脸。我顺手抓起篮子里一根刚洗完的黄瓜。“小鬼头。”奶奶笑着夺回它,“先去洗脸,快点,别浪费水呀。”“晓得了呀。”我偷咬了一口,飞快地冲过去。夏天的水很凉快,我喜欢把水溅得满身都是,好降降体温。一屁股坐在泼过水的洗衣台上,凉意嗖地一下蹿入身体,我晃着够不着地的脚丫,大口大口地吃起黄瓜来。不久,别院的小孩都回来了。一样的飞奔、洗脸、玩水、吃东西,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清脆的铃声穿梭在各条过道上,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当厨房里第一勺油沸起来时,整个月河就热闹起来了。
店小二见我在酒楼四处乱转,就把我请出去了。继续行走,街的两边开了很多小店,卖些土特产和工艺品。游人很多。店主是些年轻面孔,卖酥糖啦、小饼啦、蓝印花布啦,好像只有这些物什才算江南特色。想去找从前育子弄古玩店的老爷爷,好久没光顾他的小店了。最终在一家中年夫妇开的店里,找到了老人的收藏。店里气氛阴冷,店主抱着双臂面无表情地倚在门前,老板娘傲慢地倚在柜边。我斗胆问了问她,原来老人付不起房租,就只好把店转给别人了。慢慢想起从前我躲在他的小小店铺里,听他讲每个宝贝的历史和出处。我发现,陈列的古董都被贴上了标价,俨然成了冷冰冰的商品。记得老人说过,古玩就在于“玩”字,是用来分享它的来龙去脉,而不仅仅是外形或年代。而这些丑陋的标价把可爱的小物什矮化成了只具有货币价值的商品,令我厌恶。店主是不明白这些的。我瞥了一眼柜台。离开。
离开喧嚣的人群,像从前一样找个角落躲起来。我告诉自己,我是来寻觅故里的,不是只顾赏玩的路人。我走进还未完工的蒲鞋弄,漫步在长廊下,慢慢地走,仿佛走回了过去的时光。
小时候的夏天傍晚,长廊总是最好的纳凉处。吃完晚饭,我总是搬出自己的小藤椅,紧挨在爷爷奶奶的大摇椅旁,再搬出小木凳来做作业。各家的老人们并排坐着,摇着大蒲扇打发闷热的时光。趁着夕阳还未收回最后一缕余光,再看会报纸,打几针毛线,剥几粒豆瓣。手脚利索的就沿着河岸溜达几圈,走到哪户人家门口就探头进去打个招呼。转弯口的阔地上有张石桌,老头们爱在那儿围着下象棋。梁柱上悬着一盏油灯,好像随时会被风吹落砸在谁的头顶。吞云吐雾中他们杀了一盘又一盘,不知消磨了多少个无聊的夏夜。
太阳归山之后,大概每户人家都出来了吧。这时候鸟瞰月河,没有万家通明,而是或零星或密麻的摇椅阵。收音机的声音此起彼伏,除了爷爷每日必听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我听得最多的是单田芳的《天下枭雄》,还有《游园惊梦》之类的。大多数老奶奶都在闲聊,东家长西家短,从月河到光明街到人民路,半个嘉兴城的人口都能涉及,哪个角落的动静都一清二楚。我趴在板凳上边做作业边听老人的讲话,有趣极了,细想来,她们平凡的一生里有多少时间花在了说话上,买菜讲,做饭讲,乘凉讲,晒被子隔了弄堂还能讲,她们所谈到的人名和故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罗列穷尽的。
我曾仔细观察过夏夜里的月河,用整个童年的时光。河边总是很凉快,临水的风总会带着那么一丝清凉沁入皮肤,像撒了花露水,或像喝一碗冰镇的绿豆汤那样,舒服极了。十里五里的灯笼和路灯低着头望穿河水。我喜欢在一片明媚的光影之中寻找落入凡间的月亮。水中的月亮不完整,白得很纯净,带一丝清冷,其实很容易把它与灯影区分开来,正如在一群吴国女子中找出小乔一样容易,因为尤物发出的必是与众不同的光芒。月亮的倒影柔美灵动,但冷若冰霜,和路灯的炽热亮光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在温柔的水中。东西走向的月河,月亮刚好能用一整晚的时间走完水上旅程,它在河上不断移动的样子,让我想起广告里那颗在丝绸上滑动的巧克力。当然,这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所以它才叫月河吧,这条河,是天生用来盛放月亮的,这个名字注定了它的宿命,就像这片土地,注定成了我的心灵归宿。
不知不觉走到了乌渠弄,这是我们几个小孩共同拥有的地方。伸出双手,仍能触到两边的墙壁,只是被刷成了雪白的颜色。我抬头看那一道狭小的天空,闭上双眼,回忆起童年的如歌岁月。我看到他们在看着我,小岩依旧挂着两道鼻涕虫,方方脸上的疤也还看得出,他说这是爷爷找他的记号,他们喊我,点点快来呀!我看到墙上稚气地画着男孩女孩大树小狗,不整齐的“王点点到此一游”的方块字,墙角被遗弃的几粒粉笔头……我睁大了眼睛,却找寻不到他们。我也不再是从前那个背着书包疯跑的王点点,月河依旧静静地流淌,冲刷岁月的痕迹,无人知晓。
记得在月河的最后一个夏天。大家要搬走了,看过政府安置的新房,正各自收拾家当。收拾老房子,就像把过去整理成册,翻出几十年前泛黄了的《新民晚报》,账簿里模糊的字迹和压平了的粮票与收据。折好每一件旧衣服,虽然年岁久远却总也不舍得扔掉,破了的就当抹布或用来扎拖把。该带的都随着卡车搬向新家了,那儿是单元楼的小区,没有弄堂,没有阁楼,没有开满花的自留地。
舍不得墙角搭建了许多年的花园,那些绚烂盛开的夏花。生了根的花草是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的,它们宁可被推土机连根刨起,也要开完这一个被河水滋润的夏天。我们的心何尝不是扎根于此呢?只是人没有花草那么坚定,那么刚烈。大人告诉我,离开是必须的,只有离开我才能长大。和邻居一一道别,约好以后一起回月河。再看一眼檐角的鸟巢,树枝上火红的小果子,粘满油腻的烟囱。看一眼被野猫路过的屋顶,摸摸我们曾经躺过的青石板。我们说好,以后长大有钱了要再造月河,把大人们请回来一起住。三个孩子在巷的尽头痛哭,声音响彻狭窄的一线天空。
再见了,方方,小岩,我的好伙伴。再见了,每一条我奔跑过无数次的小巷。再见了,流淌千年的月河。再见了,我的小时候。我告诉自己,离开这里,你就该长大了。
记得临走时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一个装了食物的豆腐盒放在老地方,那只喂养了好多天的小猫一定会在夕阳西下时过来吃晚饭的,它一定会慵懒地躲在这块最安详的土地上,等待月河的下一个天亮。
直到多年后,我在光明街的砖堆里发现一只很像它的流浪猫,蹲下抚摸时已泪流满面。
站在这座熟悉的桥上,看着右边的喧闹和左边的安宁,我想我知道了,我站在左边。这里,河水流淌过的地方,是家,是我的小时候,是一辈子都无法割舍的归宿。
很多老人都已经离开了。像我奶奶一样,搬家后不久就离开我了。曾经住在月河的人们,即使已经老得认不得面孔,听不清声音,却依旧能记住这是曾经的哪条弄,住过哪户人家。
这是一群住在回忆里的人,共同拥抱着一个叫月河的天堂。
那是我的小时候,亦是我心灵的一
- 中学生天地(B版)的其它文章
-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
- 纳米粒子回收有新法等
- 梦想有多牛
- 我的模联我的梦
- Hell
- 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