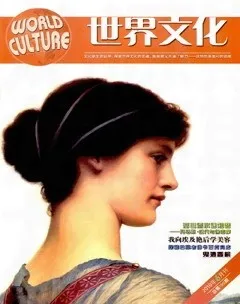《茶花女》:经验的移情
小仲马(1824-1895)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与父亲大仲马成就了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父子双璧”的奇观。小说《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作,也是小仲马根据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创作的作品。小说面世后,受到热烈欢迎,紧接着被改编成剧本。大仲马读完剧本后,激动得泪流满面,对他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嘉许小仲马,意谓《茶花女》必为不朽的伟大作品。
果不其然,自从1909年以来,《茶花女》已经被搬上银幕多达20多次,迷倒无数观众;在我国19世纪90年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以文言文翻译《茶花女》并向国人推介,结果洛阳为之纸贵,产生了“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的巨大反响。百余年间,无数世事变迁,《茶花女》不但没有枯萎凋零,反而像一株不老的常青树,愈发焕发生机,为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部小说,能在百余年间一直获得中外读者的青睐,这其中注定有着超越时空、超越国别种族的特质与内涵。在《茶花女》中,作家以细腻的笔触、高超的叙事手法、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塑造了美丽、善良、真诚、富有牺牲精神的玛格丽特,表达了对纯洁的爱情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些都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然而,还有一个原因:这部作品是小仲马自身经验的移情,浸透了小仲马自身的情感经历、幸福体验和人生苦痛。小仲马用诗化之笔,蘸着自己的血和泪将它一~摹写。
小说主人公玛格丽特在一定程度上是小仲马母亲的投影,小仲马的生身母亲有着与玛格丽特同样的命运,都是被欺骗、被遗弃的女性。小仲马的母亲卡特琳娜,拉贝是一名缝衣女工,她在大仲马尚未成名、仅仅是一个寒酸的抄写员时和他相爱同居,生下小仲马。她对大仲马一往情深,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后来随着戏剧创作的成功,大仲马开始和上流社会的演员、贵妇厮混,卡特琳娜母子渐渐被抛到了脑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母亲靠着缝衣服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然而在小仲马七岁时,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个儿子的父亲,又伙同情妇贝尔·克莱伯萨默尔与母亲争夺小仲马。为了保住儿子,善良的母亲带着他东躲西藏,但最后还是无济于事。离开母亲,使小仲马异常痛苦、愤怒,于是他很少回父亲的家,对父亲的情人始终持敌视的态度。1904年2月,大仲马与情人伊达·费里埃结婚,更使小仲马义愤填膺,立即奋笔疾书,写了一封信向父亲表示抗议。生活于母亲、父亲、父亲的情人们之间的小仲马,无论何时,总是坚定地站在母亲的这边,对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的遭遇抱着深切的同情。这种人生经历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使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对于被欺骗、被遗弃的女性满怀同情,在他的《奥布雷夫人的观点》《阿尔丰斯先生》《德尼莎》等剧本之中均反映了这种思想。同样,这种思想批判了大仲马造成玛格丽特悲剧命运的社会道德。小说中,阿尔芒的父亲不能接受玛格丽特,只因为她是一个妓女,在他眼中,妓女是道德败坏的象征,辱没家声,而且毫无人性,“是没有心肝、没有理性的生物,她们是一架诈钱的机器,就像钢铁铸成的机器一样,随时随地都会把递东西给它的手压断,毫不留情、不分好歹地粉碎保养它和驱使它的人。”正是这种伪道德,熄灭了爱情之火,也熄灭了生命之火。小伸马批判造成玛格丽特悲剧命运的伪道德,其实也是为母亲的悲剧命运鸣不平,因而是自身情感经验的移情。
同时,玛格丽特与作家本人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玛格丽特是妓女,小仲马则是私生子。直到7岁时,大仲马才公开承认他的合法地位。私生子的身世使小伸马痛苦不堪,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世人的讥诮。在学校里,当老师在历史课上提到私生子时,同学们都毫无顾忌地把视线投注在他的身上,给他的心灵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到了晚年,功成名就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受尽了冷嘲热讽,受侮辱是家常便饭,连一天太平日子也没有,而在打斗中输的总是我,身上伤痕累累,真使我痛不欲生。”作为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他强烈地体会到被逐出群体的孤独感,尝尽被侮辱、被蔑视的滋味,因而把自己的这种体验投注到玛格丽特的身上。作为妓女,玛格丽特尝尽世间的炎凉,世人对她报之以鄙视和不属,玛格丽特说:“别人像见到猛兽一样惧怕我们,像对待贱民一样蔑视我们”,这种感受真切地言说了作为私生子的小仲马的切身体验。
最后,作品的写作本身即是作家生活经验的移情。1844年9月的一天,观看戏剧演出的小仲马时结识了巴黎名妓、美艳绝伦的玛丽·杜普莱西,对她一见钟情,二人落入爱河。小仲马很同情、爱恋这个不幸的姑娘,劝她注意休息、保养身体,陪她到乡间去疗养,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但同时,小仲马对她又怀有强烈的占有欲,不能容忍她再与别的男友来往。可叹的是,从奢入俭难,玛丽·杜普莱西尽管珍重这份感情,但她已然习惯了奢华挥霍的生活,且无法自拔,而小仲马难以满足她的物质欲望。于是,裂痕慢慢出现,分歧渐渐加大,终于有一天,小仲马发现了玛丽·杜普莱西仍然与阔佬保持来往,一气之下就写了绝交信出国旅行。1847年2月小仲马回国,意外获知只有23岁的玛丽已经逝世,她的遗产拍卖后除了抵偿债务,余下的由一个贫穷外甥女继承,但是有一个条件:继承人永远不能来巴黎。这个遗嘱,包含着无限的幽怨和深意,深深触动小仲马。小仲马真诚地爱着这个女子,分手之后仍然惦记着她,把自己的坟墓也定在蒙马特公墓。他无法忘却这个美艳的女子,于是4个月后,小仲马来到他与玛丽曾经度过一段美好岁月的乡间。在那里,小仲马以自己这段爱情自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茶花女》。
小说《茶花女》讲述的是男主人公阿尔芒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妓女玛格丽特气质高雅,美貌非凡,拥有大批崇拜者。但她更渴望有真诚的爱情,把自己从泥浊中拯救出来,摆脱没有尊严的生活。当她得知阿尔芒真诚地爱上自己的时候,决心离开巴黎社交生活,与阿尔芒隐居乡间。为了实现梦想,她毫不吝惜地卖掉自己的马车、首饰、披巾、公寓、家具……幻想着与阿尔芒相亲相爱,共度余生。但是,美丽的梦很快遭到了来自家庭的阻力:阿尔芒的父亲、C城的总税务长绝对不容许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妓女。为了阻挠这对恋人,他首先对儿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是无奈儿子毫不理会;于是,阿尔芒的父亲改变了策略,把儿子支走,单独与玛格丽特交谈,告诉她:“你们两人套上了一条锁链,你们怎样也砸不碎……我儿子的前程被葬了,一个女孩子的前途掌握在你手里,可她丝毫没有伤害过您。”很“合理”的指出玛格丽特的爱不仅会害掉自己的儿子,而且还会危及无辜,使得玛格丽特无法坚持己见,决定斩断隋思。失去爱情的玛格丽特犹如行尸走肉,她很快回归社交界,但不是为寻欢作乐,而是只求麻醉自己、蹂躏自己,以使生命尽快完结。
只不过相对于生活经验而言,小说对玛格丽特进行了美化。之所以会这样处理,一则因为作家对玛丽,杜普莱西的死怀有深深的遗憾,甚至可能对此有一定的自责:另外则是进行创作的需要,玛格丽特越是美好,越能够彰显出社会道德的虚伪,达到道德批判的目的,小仲马曾说:“任何文学,若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
英国美学家V.李在1897年发表的《美与丑》一文中指出,人们对自己活动的体验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移情现象是自身对经验的反省,移情作用是长期的观念、情绪和意识积累而形成的心理过程。《茶花女》从题材到情感的抒放,都体现了作家自身经验的移情,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更是作家心底的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