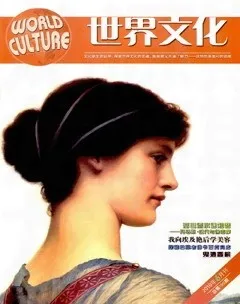歌声依旧的《喀秋莎》
又是春意浓时,海棠未谢,榴花又开,公园里处处花团锦簇。更有一阵阵歌声从松林深处传来,让人分外神清气爽。那是游客自发聚集的“合唱团”,已经延续十几二十年了,唱的歌大都是六七十年代耳熟能详的老歌:《二月里来》《南泥湾》……也有前苏联与俄罗斯的《喀秋莎》《三套车》……唱歌的大多是“白发族”,但也有“80后”、“90后”的年轻人。
随着手风琴欢快的前奏,《喀秋莎》的歌声又骤然响起。我们不禁想起今年1月,一则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说,《喀秋莎》的词作者、前苏联著名诗人米·伊萨柯夫斯基诞辰110周年之际,俄罗斯报刊、电视台刊登缅怀文章及播放专题节目外,各地还纷纷举行集会,《喀秋莎》《小路》《红莓花儿开》等伊萨柯夫斯基的歌又在俄罗斯大地唱响,令我们感到无限欣慰。
1 900年1月伊萨柯夫斯基诞生在俄罗斯北部斯摩棱斯克市郊的一个村庄,父亲是农民,也兼作村邮员。由于家境困难,他中学未毕业就参加了工作。他的文学与写作知识,不少是从父亲派送的报纸的副刊上获得的。他很小就开始写诗,深得老师赞赏。1 914年处女作《士兵的请求》发表在《新土地》报上,诗中表述的反战思想引起文学界的注意。1921年出版了诗集《沿着时代的阶梯》和《四万万》。虽然多是配合宣传十月革命后的农村政策,但由于他从小生活在农村,惯于采用民歌的风味,用清新又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与农村的变化,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受到读者喜爱。同年,他调往斯摩棱斯克《工人之路》杂志社,开始编辑生涯。1927年出版诗集《稻草中的电线》受到高尔基的称赞,使他倍受鼓舞。后因眼疾去职,成为专业诗人。
大约是1934年,有一次他在影院发现银幕上演唱的歌词,竞选自自己的一首小诗,感到十分新奇。也由此开始了他与作曲家察哈罗夫、波克拉斯、勃朗特尔等人的合作,成为一名诗人兼词作家。他说:起初,他也曾尝试给现成的乐谱填词,但效果不好,难以尽情表达心中的诗意。由此,他认为:“好的歌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而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因而,他无论是作诗或写歌词,在表现手法上都强调质朴、细腻、明快,富有节奏感,以收到谱曲能唱、离曲能诵的效果。
《喀秋莎》的词曲,实际上作于1938年。当时作家芮宁将伊萨柯夫斯基和他的“老搭档”、作曲家勃朗特尔邀到编辑部,请他们写一首歌,准备刊登在他正筹办的刊物的创刊号上。离开编辑部,伊萨柯夫斯基将几页手稿交给勃朗特尔,勃朗特尔仔细翻看着,当读到《喀秋莎》一诗时,立刻被它所表现的纯真感情和优美意境所吸引,尽管当时这首诗还没写完,他却兴奋地大声说:“就是它了!”在他的催促下,伊萨柯夫斯基将结尾部分很快写出: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
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上的人儿
她还珍藏着他的书信
啊,这歌声,始娘的歌声
跟随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
告诉驻守边境的战士
喀秋莎的歌声永远伴随着他
驻守边疆的年轻战士
心中怀念远方的姑娘
勇敢战斗保卫国家
喀秋莎的爱情永属于他。
伊萨柯夫斯基说:“青年们所以热衷诗歌,是因为他们热情奔放,希望用优美的语言去表达内心朴素又崇高的理想。”这首用俄罗斯姑娘昵称作标题的歌,恰恰是用明快朴素的语言和热情奔放的曲调,表达了俄罗斯青年心中的崇高理想,字字句句洋溢着令人振奋、鼓舞的爱国主义情怀,因而迅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然而这首歌,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竟能脱颖而出,产生难以估量的精神力量,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却是伊萨柯夫斯基和勃朗特尔都未曾料到的……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用“闪电战”横扫欧洲大陆之后,分三路大举越过苏联边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其中央集团军近百万人便直逼莫斯科城下。7月中旬,苏联红军新编第3近卫师开赴前线,莫斯科某工业学校的女学生高唱《喀秋莎》为战士们送行,当列车在歌声中徐徐开动,近卫军战士庄严地行军礼向女学生答谢,那悲壮的一幕曾令千千万万人动容……在后来的第聂伯河阻击战中,这个师的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但他们却重创了德国最精锐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队,为保卫莫斯科赢得了宝贵时间。从那时起,《喀秋莎》便伴随着战火硝烟,带着苏联人民战胜德国强盗的必胜信念,传遍前方、后方……
1942年冬季,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大反攻时,首次使用了一种由8根导轨自行发射的M-13型车载火箭炮,它便捷、火力强、覆盖面大,特别适于打击敌集团目标,压制敌火力配系和摧毁其防御工事,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战士们见火箭炮发射架上镌刻着字母“K”,那本是兵工厂的标记。但又恰是“喀秋莎”的第一个字母,便将它同他们喜爱的歌曲联系起来,把这种令德国鬼子闻风丧胆的火箭炮,也亲昵地称作“喀秋莎”……
我知道喀秋莎火箭炮要先于与它同名的歌曲。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住在重庆远郊沙坪坝,平时家中只有彭龄和母亲,父亲在城里,姐姐在学校住读,只在周末才回家。那时家中照明用的是一种灯心草作“稔儿”的油灯,浸透灯油的“稔儿”斜竖在油碗边上,燃一小朵微弱的火苗。为了节省,平日只点一根“稔儿”,周末夜晚一家人围坐小桌旁,彭龄姐弟呛书或做作业;父亲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母亲或帮父亲誊抄文稿,或为一家人缝衣服、纳鞋底。这时,常点三四根、四五根“稔儿”,斜斜的一长排竖在油碗边上,父亲说那就像喀秋莎火箭炮。有一次我们去南开中学看电影,从加映的苏联卫国战争纪录片中,看到干百发喀秋莎火箭炮发射的火箭弹,风驰电掣般呼啸着飞向德国鬼子阵地,那场面真是大快人心。于是,周末更成了彭龄母子期盼的日子,期盼着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喀秋莎油灯”下工作与学习。那清苦却充满温馨与希望的岁月,让我们铭记一生……
1945年4月当梨花盛开的季节,最后围歼德国强盗的柏林战役也即将打响,一支又一支红军部队高唱着《喀秋莎》向前线集结。伴着这歌声,两千余门刚出厂的喀秋莎火箭炮,也源源不断地向前开进……那振奋人心的壮丽场面,也永远“定格”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史页中……
我们知道依萨柯夫斯基和他写的《喀秋莎》《送别》《小路》《有谁知道他》……似及《红莓花儿开》《从前这样,如今还是这样》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与歌词,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诗与“老歌”,伴我们度过了青春岁月……我们曾听翻译家高莽说过,他有一次在莫斯科的一个集会上,遇到伊萨柯夫斯基和他的“老搭档”勃朗特尔,他告诉他们中国人对他们创作的歌曲并不陌生,特别是《喀秋莎》更是流传甚广时,伊萨柯夫斯基激动地说:“如果能听听中国人的演唱,该多好啊!”可惜由于后来中苏交恶,影响到两国正常的文化交往。正如父亲的老朋友《第四十一》的作者鲍,拉甫列尼约夫为生前未能喝一口中国江河的水而深感遗憾一样,伊萨柯夫斯基的这个心愿也同样未能实现,便于1973年7月20日病故……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各种思潮激烈碰撞,许多人将盲目追随西方引为时尚,恣意贬低与否定前人成果。高莽老师有一次在伊萨柯夫斯基墓前拍照,突然听到一个俄罗斯人用不屑的口吻说:“拍他干什么?他早被我们忘记了……”高莽十分惊讶,他说他曾想告诉那个俄国人:如果他的子女将来在祖国听不到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时,不妨到中国转转,他在中国会听到。1994年我们有机会路过莫斯科,特意去新圣母公墓瞻仰心仪已久的前苏联作家、艺术家的陵墓,其中不少人曾是父亲的老朋友。记得在《青年近卫军》的作者法捷耶夫的墓旁,一位年纪与我们相仿的俄罗斯人指着近旁的一座陵墓说:“那里长眠着一位诗人,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他……”墓旁有一尊坐像:一位穿西装戴眼镜的男士,腿上放着一本书,像在构思新作。我们忙去读雕像底座上镌刻的姓名,竟是伊萨柯夫斯基!“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愿沿着这条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那熟悉的旋律旋即在耳旁响起。我们轻轻起个头,同去的使馆的同事及留学生也随之唱起来。我们想,伊萨柯夫斯基如果知道这是几个中国人,在他墓前怀着发自内心的尊崇与缅怀,用并不专业的声调唱着他的歌时,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问那位俄罗斯人:“现在俄罗斯的青年还唱那些歌吗?”他十分严肃地说:“尽管现在不少人对老一代作家的作品说三道四,但请相信,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会记住他们,怀念他们的……”当时,我们听着这回答,心中同样有着说不出的无奈与酸楚……
如今又多少年过去,正如当年那位俄罗斯人所说,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不可能割断的,对于像伊萨柯夫斯基这样为国家、民族勤恳工作一生并卓有成就的诗人、词作者是不会被忘却的。如今,人们不仅唱他的歌、读他的诗,举行各种活动缅怀他、纪念他。他的故乡斯摩棱斯克不仅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而且还在乌格拉河畔建起一座《喀秋莎》纪念舘,陈列着与他相关的各种资料:文稿、书籍、照片,世界各国专业、非专业的合唱团用各种语言演唱的《喀秋莎》及其它歌曲的唱片、光盘,等等。为一首歌专门兴建一座独立纪念舘,恐怕还是不多见的。我们终于欣慰地看到,俄罗斯大地上喀秋莎的歌声依旧像明媚的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