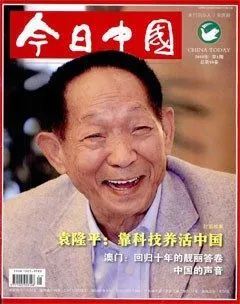甲型流感下的中医往事
今年以来,流感肆虐,但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流感、SARS等,按其临证表现,均属于中医之温病范畴,临床上以“辨证施治”为原则,往往会取得良好之疗效。
祖父孔伯华也曾经历过一次瘟疫。1918年,当西班牙流感在全世界范围肆虐之时,晋绥两地瘟疫爆发。
关于民国初期的这场疫情,史书中曾有过描述:“当时疫情猖撅,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本地有‘今夕聚着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真令人不寒而栗。”以上这些记载,多少真实地记述了民国初期的疫情情况。
民国政府当局为控制疫情派杨浩如、孔伯华、张菊人等率队深入农村开展防疫工作,成绩卓著。后来,祖父孔伯华与同仁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十卷引世。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较早的传染病防治医学专著,说明中医药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和经验,更说明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由来已久并不断有所发现和创新。
祖父感慨于疫情的严重,感慨于国计民生,也感慨于中医的担当的责任之重。1929年,汪精卫政府曾意欲消灭中医,这一政策立即激起中医界的极大公愤。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并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祖父被推举为临时主席率团到南京请愿谈判,在全国舆论支持下,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经过这次斗争,祖父认识到,必须壮大中医队伍,提高中医疗效,办诊务以图实效,真正赢得大众信任,兴教育以继传承。于是在1930年,他与萧龙发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因办学经费拮据,他常以门诊收入挪补开支。1937年“七七”事变后,伪政权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肖老年老请辞,祖父独力支撑多年,学院几易其址,最后宁为玉碎,于1943年毅然停办国医学院。该学院先后毕业了七百多人,分布在祖国各地,其再传弟子更是遍满天下。这些学生后来成为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
在30年代中期,祖父孔伯华获得了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称誉。“四大名医”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最早是杨浩如先生的。现在比较统一的说法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社会公推了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试题的命题与阅卷,从此就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说法,时称“萧孔汪施”,流传至今。
与其他名医不同的是,祖父治病的特点是强调患者体质特点,中医在临床上不仅是单纯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应该从整体上对患病的人进行治疗。萧龙友先生为乾清贡拔,曾因为孙中山先生诊疾而名誉京华,汪逢春先生用药精当治疗热病堪当一绝,施今墨先生衷中参西,开中西医结台之先河。
祖父对我的影响,除了高超的医术外,还在于告诉自己如何做人,“要学医术先学做人”。我牢记着祖父留下的临终遗嘱是:“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
在我看来,中医看病是辨证论治,有自己一套独立的体系,而不是先问是否是禽流感还是什么病毒,我们注重症状表现如何,或驱风、或清热、或化湿等诸法,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
1955年石家庄流行乙脑,中医界采用近代名医张锡纯弟子郭可民的经验以清热、解暑、养阴法用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防治取得良效。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医院按照石家庄的经验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均不奏效。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石家庄久晴无雨,乙脑患者偏热,属暑温,名医蒲辅周先生用白虎汤清热润燥,十分奏效;而北京2009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自热自退。
根据家父孔少华先生所制预防温病之方,我给当下的这场流感开出以下两方。今逢时疫流行,据孔门经验以行加减,亲朋好友索者甚众,重复告知,甚为繁琐,故而公布于众以利民生。
一、桑叶15g,菊花10g,金银花20g,连翘1呛,鲜茅根15g,鲜藿香20g,鲜佩兰20g,大青叶10g,杏仁泥10g。
二、桑叶15g,菊花10g,金银花20g,连翘10g,鲜茅根15g,鲜芦根15g,鲜藿香20g,鲜佩兰20g,鲜石斛15g,鲜生地10g。
值得说明的是,此二方非为治病而设,前方偏于热重,肺气不宣;后者偏于阴虚热重明显。立此二方意在使素有热者,肺气得宣,热邪得祛,清虚热养肝肾之阴,以达“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目的。价格则是参看,无论哪家医药商店,应不离其左右。煎煮时间不宜过长,以15分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