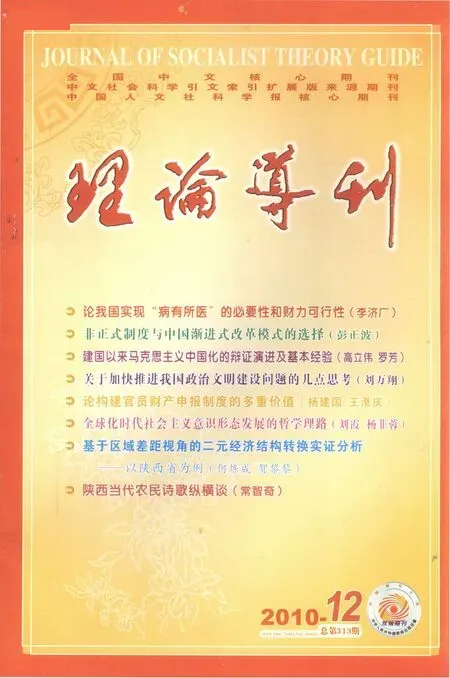从礼学视域看农耕时代狩猎风俗之嬗变
——兼谈田猎之礼的生态伦理意义
杨雅丽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从礼学视域看农耕时代狩猎风俗之嬗变
——兼谈田猎之礼的生态伦理意义
杨雅丽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在礼学形成之时华夏族已全面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在周代礼制下,田土分封与班爵禄相结合,农业收入是国家预算的基础,“积贮”始终是农耕民族的核心话语。田猎只是农业经济的补充成分,在礼制文化规约下,狩猎风俗已失去原始的荒蛮、强悍与血腥杀戮带给猎者的审美愉悦。农业立国的华夏族有土地般温厚宽阔的胸怀,田猎之礼承载了农业文化的精神气质与农耕民族的自然观与生态伦理意识。
《礼记》;农耕文化;狩猎;田猎之礼
古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是农耕文明史,中国文献的话语主题与遣词造句的声息间皆弥漫着农业文化的气息。《礼记》是战国至西汉初儒家礼学文献的汇集,编纂者是西汉经学家戴圣。其篇章“或是发扬孟子之学,或者阐发荀子之学,根源都出自孔子”[1]98。冯友兰先生认为,“《礼记》各篇大多数是荀子门人写的”[2]177,方孝博先生指出,“汉代的大、小戴《礼记》中大多数是荀卿和他的后学的著作”[3]4。在礼学形成之时,华夏族已全面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先秦诸子与“三代之英”构建了一个农耕民族绚丽多彩的精神家园。
狩猎自远古至夏商曾是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及至周代,农业社会狩猎的生产功能迅速减退,在礼制文化的规约下,狩猎已失去原始的荒蛮、强悍与血腥杀戮带给猎者的审美愉悦,田猎之礼蕴涵了农业文化的精神气质,承载了农耕民族的自然观与生态意识。
一、从礼学视域看周代农业社会的特点
1.周人农业立国的文化传统。周人早期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农牧交错地带,兴盛于渭水流域的黄土台塬和冲积平原。《汉书·地理志》曰:“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4]1642后稷是周族农业文明的创世纪英雄,《诗经·大雅·生民》记述了他教民稼穑的丰功伟绩。《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5]112《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公刘率族人由邰迁豳,循后稷稼穑之道,为周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故《史记·周本纪》云:“周道之兴自此始。”历史上曾因“环境恶化和水土资源退化”以及“游牧民族南侵占领”[6]404等原因,导致周人数次迁徙,如公刘迁豳、古公迁岐、文王迁丰、平王东迁,但周人始终坚守农业立国的传统。
2.田土分封——周王朝政治制度之基础。《礼记·王制》是以周代制度为基础构想王朝政治格局的文献。孔颖达疏:“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7]1321《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7]1321天子分封诸侯,与授禄爵相结合的是田土分封。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授予诸侯田土之多寡与其爵位相称,爵位越高,分封的土地就越多:“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7]1322天子与诸侯各自拥有的田土之多少形成等差。这种田土分封的格局及其象征意义可比作树:天子是树之主干与根系,公、侯、伯、子、男是粗细不等的枝;粗壮有力的主干和旺盛发达的根系足以承负粗细不等的枝,这棵树才能枝叶繁茂。
田土分封是王朝制度的基础,其他制度皆建立于田土分封之上并受其制约。《礼记·王制》论王朝官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7]1322天子设三公、卿、大夫之职,其官爵与俸禄皆与田土分封相结合。天子拥有天下,天下有九州,每州土地方千里。天子直接管辖之地方千里,曰“畿”,曰“县”。《礼记·王制》曰:“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此记天子畿内封国之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7]1323此记天子畿外八州的封国之数。
3.“积贮”——农耕民族的核心话语。古代生产规模简单狭小、种植水平低下,农田收获有限,“积贮”始终是农耕民族的核心话语。《说文·禾部》:“積,聚也。”[8]344《说文·贝部》:“貯,积也。”[8]298在农耕文化语境下,“积贮”即专指积蓄粮食。西汉贾谊《论积贮疏》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脆弱的农业经济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粮食储备不足的国家如同建在沙漠上摇摇欲坠的屋舍,因此,“积贮”是农业国家之“大命”,是天子施政之基础。
《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7]1334国家生存与社会发展必须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所以“积贮”始终是农耕民族的核心话语,也是礼学的关键词之一。
4.农业收入是国家财政预算的基础。农业国家的财政预算必然以农业收入为依据。《礼记·王制》曰:“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孙希旦注:“杪,末也。岁末五谷皆入,然后多寡有数,而国用可制也。”[9]337岁末是农事结束之时,故国家预算在年终。“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国家预算依据耕地面积大小、年成丰歉,还要以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数为基准,衡量收入来预算支出。土地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风调雨顺,如孙希旦云:“然地之大小有定,岁之丰凶无常,故必以二者相参而制之。”[9]337祭祀费用要在财政预算中体现:“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祭祀费用占全年开支的十分之一,国有大丧,三年不庙祭,只祭天地与社稷。“丧用三年之仂”,即丧礼预算占三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可见,农业收入是预算的基础,也是计划重大礼仪开支的依据。
二、从殷商到西周,狩猎风俗在农业社会的文化转型
1.狩猎作为生产方式在殷周之际由盛转衰。远古人民以狩猎为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形延及殷商。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优越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殷墟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野生动物名称和已发掘的野生动物骨骼,大多是今天在中原灭迹而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生存的物种。从殷墟出土的野生动物实体和器物造型推知,殷商时生存于中原的动物除今天常见的牛、羊、马、狗、猪、鸡等家畜家禽外,还有虎、象、犀牛、豹、熊、鹿、狐、獐、貘、獾、鲸、龟、雕、鹰、丹顶鹤、冠鱼狗等今天在中原已绝迹或很难见到的动物[10]2。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对商王狩猎的记载,从武丁到纣各王大都爱好田猎。有学者认为,田猎逐渐消退而农业逐渐占据社会生产主要地位的情形“直到商代末期都还没有出现”[11]63。我们至少可推断商朝拥有高度发达的狩猎文明,田猎在殷商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商周之际,黄河流域生态逐渐恶化,气候变得寒冷干燥;农田开垦使植被锐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破坏;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狩猎致使野生动物资源锐减。尽管狩猎在周代依然重要,但周人并未遇到殷商时期优越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那些在殷商考古遗址中经常发现的象、犀牛等动物的骨骼,在西周考古遗址中已很难见到[10]8。由此,我们认为坚守农业立国传统的周人在推翻殷商之同时,将农业文明全面推进中原,殷商时兴盛于中原的狩猎文明迅速消退,狩猎生产方式在周代农业社会退居次要地位。
2.狩猎在周代社会功能的多样化。关于“田”在先民语境中的含义,蒋礼鸿先生认为:“有树谷之田,有猎禽之田,字形同而非一字也。”“田即网也,田所以取鸟兽,因之凡取鸟兽皆曰田矣。”[12]1172狩猎之义的“田”后作“畋”。田猎在周代社会功能呈多样化:是获得肉食与祭品的生产方式;捕杀野生动物可以减少其对农田的损害;是军事训练和礼仪操练。周人不仅将田猎作为获取禽兽的生产活动,而且作为“逼真”的实战演习与“实践性”极强的礼仪演练赋予它重要的政治与礼俗意义。《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周人将猎获的禽兽献给祖先,在表达敬意之同时还表明子孙绝不敢耽于享乐而忘记武备。农耕民族在充满冒险刺激的狩猎中可以培育强悍、勇猛、自信的品质;大规模的田猎需要严密的组织和机警勇敢的战斗意志,参与者能真切感受到军事训练与礼仪操练之意义,所以“田猎与军事有联系,是国家实施礼治教化的重要活动”[13]43。
田猎是周代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中直接涉及狩猎的诗有《周南·兔罝》、《召南·野有死麇》、《召南·驺虞》、《郑风·叔于田》、《郑风·大叔于田》、《郑风·女曰鸡鸣》、《齐风·还》、《齐风·卢令》、《齐风·猗嗟》、《魏风·伐檀》、《秦风·驷驖》、《豳风·七月》、《小雅·车攻》、《小雅·吉日》等,是狩猎在周代农业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之明证。
3.周文化对周边异族狩猎风俗的包容与尊重。远古族群的图腾和崇拜物多为禽兽,这印证了狩猎在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当华夏族全面进入农业社会时,狩猎在周边异族的经济生活中仍发挥着主导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云:“文化是一张地图。”每张地图都遵循着一个原则:“以我为中心。”[14]145《礼记·王制》构建了华夏族农业立天下的王朝格局,王朝的中心在黄河流域的北方平原,这里的农耕民族有温厚稳健的性格和土地般开阔的胸襟。他们处在“文化”地图的中心区域,以“我者”姿态审视作为“他者”的四方异族;“我者/他者”与“中心/边缘”概念根植在农耕民族的脑海里并成为他们观察宇宙的起点与行动的指南。大一统观念自尧舜时已初步确立,与之相随的“夷夏之辨”贯穿民族历史。中原农业民族一方面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通过朝聘、盟会、通婚等方式化解夷夏矛盾,主张“用夏变夷”,使之成为王朝的远方臣民。
《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以上论述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表达了“我者/中心”对“他者/边缘”的体察、包容与尊重;主张对异族“脩其教”但“不易其俗”,“齐其政”但“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展示了胸襟博大、气质温厚的农业文化精神:处于“我者/中心”地位的中原农耕民族对处于“他者/边缘”、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异族持包容、尊重态度。
三、田猎之礼的生态伦理意义
《礼记·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是礼之大纲,如国家法度;“曲礼”指礼之细节。无论“经礼”还是“曲礼”,都是“礼意”的载体,都承载着行礼者“赋予礼的系统的精神含义和人文意义”[13]42。礼包涵“礼仪”、“礼物”、“礼意”三要素[15]107-109,“礼意”是礼最重要的“构成要素”。田猎之礼的“礼意”既指向政治与礼俗范畴,也承载了先民对天人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哲学思考。
1.礼制文化视域的田猎之礼。在礼制文化视域,狩猎并非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田猎制度是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农业文化的精神气质。
《周礼》将四季的狩猎称为“时田”、“四时之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周礼·地官司徒》记迹人之职:“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禁麛卵与其毒矢射者”,禁止捕杀幼兽、拾取鸟卵、用涂有毒药的箭射杀禽兽[16]748。《礼记·月令》记各月天子政令,在记述农事政令之同时多言及田猎之礼: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大田猎”[7]1357-1365。春夏是禽兽繁育生长之时,故严禁捕杀幼兽,不准掏取鸟卵,捕捉鸟兽之器具、杀害禽兽之毒药禁止带出城门。这些对野生动物采取的保护性措施,皆作为天子之禁令而发布。在礼制文化的制约下,田猎之礼成功地消解了狩猎习俗特有的血腥与残忍,蕴藉了华夏族作为人类“我者”体察万物“他者”之理性与温情。《礼记·郊特牲》云,“大罗氏”是天子掌鸟兽之官,蜡祭时负责收取诸侯贡献的鸟兽,并将鹿与女子赠与诸侯使者。他向使者宣读天子诏书:“好田、好女者,亡其国。”[7]1454在此叙述中放纵的田猎甚至丧失应有的生产功能与礼俗意义,与荒淫好色一同被看作祸国殃民的灾难之源。《老子》第十二章亦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正代表了农耕民族对狩猎习俗独特的文化解读。
中国古典哲学将宇宙视为“一个和谐的、秩序井然的、生生不穷的历程”,是一个变化的大流[17]202。田猎之礼的哲学意义指向“天人之际”:人属于自然,人类必须也必然地追随着宇宙运行的步履,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生生不穷”、“秩序井然”的宇宙“大流”;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的索取必须有节制。
2.田猎之礼的生态伦理意义。狩猎建立在对野生动物的血腥杀戮之上,漠视鲜活生命体的价值意义;而农业劳动者不避风雨霜露寒暑,辛勤耕耘,在对“他者”生命的呵护与培育中付出最真挚的情谊。所以农夫心中总是洋溢着对土地与田禾的温情,最能深切感知“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真理。农耕民族以特有的道德情怀观照狩猎习俗,田猎之礼必然凝聚了丰富的道德情感。
《礼记·王制》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孔颖达疏:“若田猎不以其礼,杀伤过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7]1333礼制文化在确认狩猎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之同时强调对禽兽的猎取必须有节制:“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禁止对禽兽赶尽杀绝。《礼记·王制》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以火田”指用火焚烧草木驱赶捕杀猎物。在昆虫未蛰伏时实施“火田”会焚灭各种生物,故禁之。先民视禽兽为“天物”,认为天地生成之,人可以猎取之,但要取之有度,不可狂捕滥杀,即使对猎获对象以外的各类“天物”亦不得任意伤害。
儒家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仁,仁既是一切德目的总概括,又是各种德目的生命之源与萌芽发端。仁的核心是“爱人”,就是要用仁心关怀和滋润他人。仁的出发点是孝与悌的亲亲之情,并通过忠、恕推及社会,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不仅要爱亲人、爱人类,还要将仁心推及万物,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礼记·祭义》曰:“夫子曰:‘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儒家将“爱物”与“孝亲”相联系,主张以仁爱之心待物。
“仁民爱物”的思想自先秦以降一直为中华民族所传承,宋代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从“仁民爱物”到“民胞物与”,代表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就是要人类不仅顺应自然,而且要主动关怀和爱护自然。田猎之礼能约束人的欲望,限制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与破坏,还能通过道德层面的潜移默化使人以仁心珍惜、保护自然。
《礼记》展示了农耕民族的广阔胸怀与崇高理性。在礼制文化的规约下,狩猎风俗那基于对野生动物无情杀戮而特有的粗犷与荒蛮被消解殆尽,田猎之礼凝聚了农耕民族温厚、凝重、严谨的文化气质,蕴涵了华夏族基于特定的农耕生活情境而形成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生态伦理智慧。
诚然,这种生态意识产生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较弱的上古农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质上具有被动地适应自然规律的性质,其实践方面的道德规范也是对生存经验的归纳和概括”[18]148。但这种基于“天人合一”哲学思考的生态伦理观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珍贵的贡献,对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赵光贤.儒学的源流[A].孔子研究论文集[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方孝博.荀子选·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黄春长.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J].第四纪研究,2003,(4).
[7]礼记正义[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说文解字注[Z].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9]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朱彦民.关于商代中原地区野生动物诸问题的考察[J].殷都学刊,2005,(3).
[11]舒怀.从龟甲兽骨看田猎在商代的经济地位[J].湖北大学学报,2000,(6).
[12]汉语大字典[K].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13]王文东.《礼记》中的生产礼仪及其意义解读[J].孔子研究,2008,(1).
[14]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5]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6]周礼注疏[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8]樊宝敏,李智勇.夏商周时期的森林生态思想简析[J].林业科学,2005,(5).
B222.105
A
1002-7408(2010)12-0109-03
201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经典阐释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杨雅丽(1956-),女,陕西武功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训诂学与儒学。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