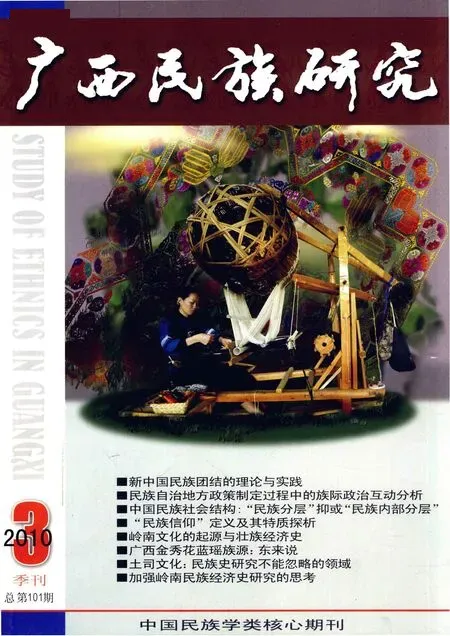“民族信仰”定义及其特质探析*
——基于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特质及当前“民间信仰热”的反思
和晓蓉
“民族信仰”定义及其特质探析*
——基于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特质及当前“民间信仰热”的反思
和晓蓉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呈现的“民间信仰热”,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目前对于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定义和理论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拟就“民间信仰”的概念、定义、特质及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和阐释。
“民间信仰”;特质;心灵传承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间信仰及其活动的复兴和近年来学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形成一股“民间信仰热”。这是新时期党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体现。然而,关于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学理、功能、价值等问题还明显滞后,这是长期以来“禁区”破解之初的一种必然。对少数民族信仰的研究,需要在理论、观念上的突破和广度与深度的拓展。本文通过对“民间信仰”概念及相关理论的阐释,对宗教——信仰——民俗生活及其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民间信仰研究现状
关于我国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从被诬名 (迷信、糟粕)到被虚化 (文化化、原始崇拜化、非宗教化),被正名与再界定,最后被“非遗化”的起伏跌宕历程。在理论上,从禁忌变显学;在实践上,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举行仪式;在地位上,从打击对象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其中所蕴含的意义是极其深刻的,是我国民族振兴、团结和谐、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需求的表现。这种“复兴”的动因大致有三个方面: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式、民众生活内需式、申遗推动式。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诸多研究者多是围绕民间信仰的来源、文化内涵、质态、历史作用等方面。有学者指出:“民间不应被视为同质的社会范畴,因为其中又可能包含了不同的阶层、组织和族群,应该把它当做一个舞台来把握,这是不同宗教传统相互较量、相互渗透的舞台”。①
从介入学科看,民间信仰日益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研究取向也呈多样化:民俗学的民俗生活整体研究取向、历史学“自下而上”的新史学 (社会史学)取向、人类学与西方汉学联盟的民间宗教和中国宗教取向、宗教学的宗教和谐与宗教世俗化取向等等,都在从各自学科的角度进行重构与言说,有学者指出中国民间信仰是中国三教以外的第四传统②。民间信仰研究因而呈现一派兴盛景象。事实上,民间信仰的后现代“复活”,无论从学术研究需求上,还是普遍的人们精神向度的探求上,都开通了一个极其深邃的面向。
但从本文视角出发,问题也是显见的:其一,宗教化约式研究依然是学界宗教信仰研究的主流方式,言说者保持局外身份,缺乏亲证意识或者宗教同情;其二,没有明确指出民间信仰与所谓制度性宗教在形成和传承等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亦即宗教——信仰——民俗的本质关联问题;其三,言说对象的去少数民族性亦即纯汉学背景性。换言之,现行的民间信仰概念不适用于少数民族信仰的认知和研究。而这三个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以下分别述之。
其一,宗教化约式研究问题。基于科技和理性的现代学术都对宗教信仰进行了完全或部分的功能论和心理论的解释,并且坚信通过其解释可以消解宗教。但化约式研究对于宗教信仰这一特殊的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把握程度、错位情况等,伊利亚德、普里查德等人早有洞见,他们始终坚持:“‘宗教现象’唯一可被认识的方式就是从其本身的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把它当作宗教性的事物来研究。竭力通过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艺术学或任何其他的研究方式来理解宗教的本质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触及不到宗教中一个独特的、不可化约的要素——它的神圣性”③。但化约式研究取向及其消极影响在我国现阶段并未受到重视;对民间信仰的多学科解读也大多在这种取向下进行。当然并非绝对不能采用化约式研究,诸多学科的本位研究,是自然且必要的,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对其有一个非化约式的研究,从本质上对宗教信仰有一个相对正确完整的认识。否则热闹上演的只是盲人摸象的现代版本。以下一段目前尚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定义性文字即是例证:
“民间信仰,主要是指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那些存在于民间而又不同于传统宗教信仰的信仰现象。具体到我国的民间信仰,是一种无经典、无明确或系统教义、也没有固定仪式的有神论信仰,表现出相当大的无序性。它属于非官方的文化,很少通过文字进行传承,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潜意识中,对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产生着深刻的影响。”④
这样的认识,不要说与少数民族信仰状况毫无应对性,就是放到汉民族社会背景下,也显见其谬误。近一个世纪的“宗教禁忌”,使我们对宗教信仰及其文化表象已经是非常的疏离和无知;并且很显然地,这种局限性被带进了相关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理论和田野成果都建立在了“去宗教化”和“去神圣化”的基础之上,亦即宗教化约论基础之上。信仰的整体性被肢解,整体意义被消解、误读或屏蔽。
其次是缺乏信仰研究的亲证意识或宗教同情问题。化约式取向消解了信仰研究的实证——毋宁说亲证要求。人们得以在对宗教信仰毫无实际感受或者毫不认可的情况下,超然于宗教之外地研究宗教和信仰问题。“客观实证”这个原本是现代学术研究最为讲求的态度方法在宗教和宗教文化研究中仅仅成为了一个双向的障碍,人们既不客观也不去实证⑤,隔岸观火,以保持自我的唯物和理性面孔。换言之,以无神论观念理论解读灵性的传统信仰导致了理论与实相之间的巨大张力,造成南辕北辙的荒唐局面⑥。世界跨宗教研究的领军人物潘尼卡对此有着充满智慧的洞见: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社会和宗教难题启示了人类需要一场转化,从而导致人类视域的大改变。如果不改变人们以往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维度,和谐难以从根本上实现。他不仅证明多宗教经验是可能的和真实的,而且证明它将深刻地转变卷入的人和传统。他指出唯有触及自己传统的根——也就是宗教核心、灵魂——一个人才可能真正基于他者的角度,理解他者文化,也才称得上真正的跨文化研究。他从而倡导一种灵性的认知科学。⑦承其倡导,我认为灵性认知科学的基础应当是在摆脱唯物与唯心二元张力之后,在亲证意识和亲证方法指导下的认知和研究方法。我们没有足够关注潘尼卡为代表的后现代宗教学理论反思,则是因为我们自己对宗教信仰的认知还很不够。
其二,宗教——信仰——民俗的本质关联性问题。民间信仰的宗教属性 (是宗教的抑或非宗教的)和体系属性 (体系化的抑或分散无序的)的探讨是当下“民间信仰热”的热点之一。其中将民间信仰归属宗教系统,承认其宗教属性,为时下较为周全的观点。金泽教授即以“上聚下散”来归纳正统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民俗学研究就是一个沿着宗教信仰怎样由制度化、正统性宗教到民间宗教再到民间信仰到民俗事象一路散下去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关注怎么聚起来的过程,即怎么样又在民间信仰的土壤中生发出民间宗教、新兴教团等”⑧。但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宗教的根本属性是什么?如果仍以化约式观点定义宗教,那民间信仰的根本属性又如何得以确定?相应地,实践民间信仰的民俗生活又该如何看待?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迄今还没有得到正面的阐释。但这是一个关节点,我们必须厘清认识,才能理顺宗教、信仰、民俗三者关系,其他言说才可能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一种倾向是割裂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迎合当下政策倾向捧民间信仰而抑宗教,没有将视域扩展到整个信仰世界及其基本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以宏观的信仰为大背景来考察民间信仰。再深刻一些的话,可以说这当中存在一个悖论: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似乎是两个信仰系统,亦即同一个体或同一群体应当有两颗心、两个精神世界,一个面向宗教信仰,一个应对民间信仰和民俗生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也反映在有关的论述当中而难以自圆其说。当然造成这个悖论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即汉民俗乃至汉民族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就是“太俗”了,信仰的神圣性和超越性,在历史上曾被宋明儒学长期地儒化亦即世俗化,功利化⑨,加之汉民族对宗教兼收并蓄但信而不笃的特点的影响,以及西方现代性的荡涤,中国汉文化社会已成为世界上最世俗化的社会,传统文化衰退了,早已没有了少数民族民俗那种缘于信仰基质的灵性和全民生活性。因此可以说,西方理论的科技实证要求、加之我国汉民族社会的俗化情状、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共谋偏向,影响和限制了人们对民间信仰的认识乃至整个信仰研究视域的设置,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此外,“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精英与百姓”、“文化与权力”、地域象征与权力空间等二元对立化的西方理论观念在时下民间信仰研究中仍然是主流意识。谈中国宗教信仰问题,“实际上是讨论别人文化义理架构中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是讨论的材料,而别人文化 (西方文化)中的概念、术语、名词则是讨论的‘义法’(最基本的义理架构)”。⑩
上述情况表明,如果从非化约论的和少数民族信仰特点出发,我们对宗教和信仰需要一个新的认识,但这里限于篇幅和学力,我仅能做一个极其浅要的概括:
宗教当起源于神圣与世俗的最原初的分离,因而宗教也就是重新实现人们与神圣超越者的关联的途径与方法。⑪宗教的内核即是信仰,信仰即是对超越者或神圣者的信念与追求,这种亘古的追求通过内在的心灵传承和外在的仪式传承而实现。民间信仰即是宗教信仰的散化和衍生形态,有着更多的世俗功利取向,民俗是民间信仰的生活化形态或生活实践,围绕民间信仰推展的民众生活即为民俗生活。
换个角度,民间信仰首先起源于人类满足生存需求的活动,它最早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获取饱暖的文化模式;但这个模式里更为本质的,则是民族神话中所显示的人类敬神祀神以求自我生存与发展的方法规则。因此,在其源起上,其实并无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之分,二者是合一的。而人类物质能力的强化过程也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自我心灵分离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不再统一,最终导致知识和信仰的分道扬镳这一蜕变的现代状况;但另一方面,永恒的精神需求以及人们对于物质攫取与自然限制之间关系的认识,又迫使人们在从心灵空间中异化出来之后又不断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以重新回归心灵空间,寻求与宇宙、心灵的和谐。这些手段、方法就是上面所说的原生宗教以及后来的民族宗教。原生-民族宗教的信仰方法、义理、观念等散落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以较之于宗教信仰松散、零星、更为生活化的方式出现时,即为民间信仰;以民间信仰所引导规范的民众生活,即为民俗生活;民间信仰缺失的民众生活就不能称作民俗生活。因此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有着本质的联系。而处于不同信仰层次上的民俗,与其源头有亲疏远近的关系,若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分析,则存在一个由核心的原始意象逐步向外层泛化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迷信就是那些处于泛化边缘的甚至已经与核心原型发生异化的信仰,笔者称之为“类信仰”或“次信仰”。
因此,信仰是贯穿整个宗教、民间信仰、民俗生活的主线,三者有着共同的内核——如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只不过它们距离这个原型核心的远近不同。我国少数民族信仰的这种“三位一体”特点最为突出⑫;“民间信仰”显然与之名实不符。本文“民族信仰”概念的提出亦缘于对这个特点的关注和把握。
其三,“民间信仰”概念的去少数民族性。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其概念建构和言说对象的单纯汉文化语境性以及当下自我界定的复杂多样性;二是该概念与民族传统信仰实相的非应和性。
作为一条副线,少数民族传统信仰同样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蒙诬和平反、复兴的过程。但在以中国民间信仰为题展开的研究中,少数民族传统信仰被完全屏蔽:在学术上主要有两种称谓:民族民间信仰、少数民族宗教,而西方学术的替代词即是原始宗教、萨满教等;就“民族民间信仰”而言,不过是在通用的“民间信仰”前面加了一个定语“少数民族”,但对其历来没有一个严肃的界定;这个概念与少数民族宗教是何等关系,与以汉民族社会为背景的民间信仰实相有无区别,是否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的内涵、特点、历史与现状等相符合,似乎没有人追问过。最明显的,“民间”二字即与少数民族生活实相不符:与民间相对存在的“官方”、“国家”、“上层”、“文人精英”等概念在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中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不是显性的分类标准。在“中国民间信仰”之名下展开的信仰研究屏蔽了少数民族信仰这一大实体,且自身界定尚不明确;少数民族信仰研究者又往往将这个根本没有兼顾少数民族信仰特点的表述生搬硬套到少数民族信仰头上,名实相背。这恐怕是学术的一大疏漏。这个状况对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的研究以及当下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笔者认为民间信仰概念不适用于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的认知和研究。
二、“民族信仰”概念的提出及其特质
(一)概念的提出
上部分的探讨,已为“民族信仰”概念的建构做了几个铺垫:“民间信仰”概念自身的若干问题;宗教、信仰、民俗、民俗生活定义的重新归纳——内在一致性的强调;对神圣性与超越性的非化约式取向的强调亦即复魅取向的主张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特点的归纳,提出“民族信仰”概念,初步阐释其自足性和现实必要性。
其一,少数民族信仰的特点。
如上所述,对民族传统信仰的称谓,历来有原始宗教、巫教、萨满教、多神信仰、小传统及新近启用的原生性宗教等多种,各有所指;但我认为它们并没有比较完整地表现我国少数民族信仰的特质。
在少数民族社会中,更为真实的情景是,民族传统信仰对各个民族或族群个体而言,就是其制度宗教;信仰的民族性和民族的信仰性二者互为前提;且大多具有全民性、集体性的特点,内在地以多神、多巫术实用性或实践性为特点;相应地,其民俗信仰和宗教信仰往往是相融合而共生的,难以言说何为宗教信仰,何为民俗信仰或民间信仰,民族宗教与其民间信仰有着根本的内在连续性,并表现为在民族生活中二者相融共存的实际状态。
对以上特点,原有概念显然缺乏概括力和表现力,以及一种内在整合力。“民族信仰”概念更能代表民族宗教与其民俗信仰相融共生又各具情态的真实境况,更能代表人类普遍的原型心理和精神超越追求;更为重要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性。
其二,“民族信仰”概念的自足性与现实必要性。
关于“民族信仰”这个概念的自足性与现实必要性,可以从其本体与形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实践的,和当下国家和民间共同倾力的非物遗保护与传承的,这样三个方面来认识。
就其本体与形态而言,首先本概念所用的“民族”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与主流汉民族相比较而言的55个少数民族的族群单位,亦即传统的按族系、族别、支系认定的少数民族族群单位。“民族信仰”包括了原来分属民族宗教、民族民间信仰、民俗信仰的所有具有信仰内质的信仰内容和形式。在此界定下,则“民族信仰”具有整体的形态,与整个民族的信仰生活相对应边界重合;以及在整体形态下丰富的层次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同时可回避当下围绕民间信仰的性质 (包括其对国家安全的掂量)、学科归属等的讨论和争执。
就其生活实践而言,“民族信仰”之说与各民族社会生活实践具有完整的对应性,包括外在形态与形式的对应性和内在心理的一致性。
至于“民族信仰”概念的现实必要性,一是指上述其满足相关实践要求的特性,二是指适应现实中我国民族文化研究领域理论建构的需求。这种建构有两个取向:整合性和复归神圣性。以西方神学的和基于反抗神学而彻底世俗化的理论观念来诠释我们有神的文化体系,显然是悖逆的,有失分裂的,而不是整合的、圆融的;依其概念方法我们无法准确把握我们自己民族信仰的特质,更何况西方自身已经日益危机重重。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标准、语言、概念、理论体系,否则所有的努力不是在建构,而是在解构、肢解和消解神圣性。而神圣性是我们所有传统——包括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灵魂。如当代儒学家蒋庆先生所言:“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使命就是进入世俗化的世界而不放弃神圣性的理想,最后在世俗化中用神圣性去转化现代性,去对治世俗化,最终实现儒家“圣俗不二”的“中和理想”;“因为人必须在具有神圣性的生活中才能够安身立命,才能够过一种圣俗合一的健全的生活”。⑬
(二)“民族信仰”的特质及功能
作为一个初设的概念,要在一篇论文中全面、准确、完整的界定显然是困难的。择其要点,我尝试从“民族信仰”的和谐性、整体性、心灵传承性三个方面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民族信仰的基本功能。
其一,“民族信仰”的和谐性。
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当有本体的和功能的两方面的认识。就本体而言,如同人类所有宗教信仰传统一样,民族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中最为普遍和最为基本的原型意象,包涵着人类普遍性的生命超越追求和道德价值准则;是特定文化生态环境中寻求社会、自然与心灵和谐的智慧体系。和谐是信仰的核心。民族信仰从形式到内在义理的深刻的一致性,即是民族信仰和谐性的表达。从功能的角度看,由于其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的三位一体特性,相融共生性,其覆盖了整个民族生活的边界,具备了对于民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统合能力、解释能力、化解能力——更为根本的,心灵整合能力。因而它是自足的;自足的自然是和谐的。
这种本体与功能的和谐性的根源,外在的可以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分层不明显、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生态环境的相同或相似性等方面加以考察,但内在的、最为基本的根源,应当回到民族信仰的集中表现形态——宗教信仰的原型心理那里,因为在多数的民族社会中,心灵的原型性在各自的传统生态环境中得到了较好的保持;⑭这样一种心灵所具有的包容性、整合性是巨大的。⑮原型心理的一致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民族社会中诸多层面的信仰融汇而并行不悖的内在原因。也是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人类信仰传统都具备内在和谐性以及由此而禀赋的宗教间、族群间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相互融通与借鉴的可能性。⑯我还相信,对这种和谐性的认识是探求人类心灵文化的深层机制的必由之路。西方伟大的智者们如爱因斯坦、汤因比、荣格、潘尼卡等,都极其睿智地洞察到了这个实质,并作了各自的表述;而实际上,他们的表述与东方古典圣哲们的智慧体系、与我们各民族传统信仰特质有着深刻的应对关系。
其二,“民族信仰”的整体性。
在当今学术中,“整体性”是一个不断被强调和建构的概念。但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想到,这个整体因何而整合?何以能够被视为整体?我们用什么框架去装载这个整体?用什么主线去穿缀这个整体?我认为,除了信仰别无二者。这是整体的整体。如果我们仅仅将整体理解为地域的整体性、族群的整体性——有时仅只是村落的整体性 (例如对村落民族志的过分强调和依赖),那么我们的整体观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而我所尝试把握的“民族信仰”概念,在注重事项的整体性的基础上,更为关注的是一种内在有机联系;它既是一种形态化的整体,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整合于人类心灵的一致性 (这种心灵一致性表现在同一个体的世俗信仰与超越信仰之间、同一群体或族群乃至所有人类之间;也表现在不同信仰体系、信仰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一种基本的和谐性),一种如维柯所说的“人类心灵的永恒结构”。这种以内在的心灵传承和外在的仪式传承共同构成的整体性才是其他有相的整体得以形成和辨认的基础。因此毋庸讳言,在所有的整体性中,信仰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整体性。⑰民族信仰更是如此,其整体性和生活性互为前提。以此观之,则时下世俗化潮流中呈现的所谓在后现代条件下的神圣生活将成为完全个体化的终极关怀的理论是有偏差的;个体化只可能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信仰本身。⑱民族信仰的历史与复兴的现状、民族信仰本身的特质提示我们,后现代并非世俗化本身,回归神圣和信仰将是其最终走向。
其三,心灵传承性。
民族信仰是民族文化的母体和基质,其传承在沿循语言传承、行为传承等具体的传承方式的前提下,更为本质的,是一种我称之为“心灵传承”的传承方式。我认为这是所有传承方式中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但也是人们通常没有观照到的一种传承方式。⑲我尝试将其描述为:心灵传承是民族文化诸多传承方式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它是在特定传承场中对人类精神智慧的直接“传达”和“体认”,这种传达和体认是超出了认识、观察、经验乃至直觉等理性认知范畴,或者说排除理性认知甚至语言概念的。通过这条途径,人类精神文化中最基层最隐秘的部分自远古以来一直传续不绝。
心灵传承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作为本体的和作为具相的传承方式的。
心灵传承的本体即核心内容就是人类心灵的智慧,具体而言就是各民族不同形式的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神秘主义传统以及与宗教文化互为表里的民族艺术。
作为具体的传承方式,可以表述为:人类各种信仰传统,虽由于自然和文化生态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旨向相同,从传承的角度看,即是特定生境中个体或群体通过仪式 (无论具象的还是心理的)以心灵交通自然与神圣,获取特殊知识或启发自我心灵以实现人类或族群神圣性及有关超越的知识智慧的传递的方式和过程;人们在从心灵空间中异化出来之后又不断采取的各种回归心灵空间,寻求与宇宙、神、和平共处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心灵传承。
从以上初步界定可看出,民族信仰与心灵传承是互为本体、互为方式和手段的。民族传统信仰的习得、认知、领悟、展示、传续等 (表现为心理精神的、知识体系的和仪式的三个层面的),都必须以心灵传承为核心方式;以心灵传承进行的,必定是属于信仰范畴的内容;二者是完全对应的关系。这种完全相关性就是保障我们民族文化有序传承的内在机制。
心灵传承特性是从传承角度对民族信仰神圣性和超越性的归纳。形而上的人类心灵智慧,实际上都有其形而下的外化形式,从特定信仰的心理、精神、行为、仪式到整个特定信仰传统的生存发展演化,即是通过文化方式把人的心灵模式“复原”和“再现”,或使集体无意识“显影”。当然,这些“复原”和“再现”在心灵智慧层次上,在实际操作方式上又各有差别,因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信仰文化样态;因此无论民族信仰抑或心灵传承,都是实相的或可证的,不存在虚无缥缈和无法实证的问题,关键在于视角的转换,亲证意识的养成。
其四,“民族信仰”的基本功能。
特质与功能有表里和因果的关系。以上有关民族信仰特质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提示出其基本的或核心的功能,可归纳为:族群文化的聚合创生功能、族群与社会和谐功能、族群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保障功能。
族群文化的聚生功能:信仰是文化,但它是文化的文化,民族生活整体得以为整体的制度。民族信仰的族群文化聚合创生功能即源自其本身的整体性以及由此具备的文化孕育、整合、维持和再生能力。综观任何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其信仰的基础上、框架上进行架构的,而其整个的社会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架构中有序进行的;以特定信仰为内核,可以蕴生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以信仰为内核的文化表象,无论其如何的五花八门,面貌各异,但却一定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杂而不乱,井然有序;当其文化发生变迁或涵化,只要信仰不断,则变迁与涵化都是一种有序的变化,反之,要复兴一个民族的文化,则除信仰复兴别无他途。
族群、社会的和谐功能:民族信仰的族群、社会和谐功能来自其内在的和谐本质 (如上所述)。但对于这种和谐性及其和谐功能的把握,首先需要我们改换一个视角:亲证的和整体的;在此新视角下,心灵传承性决定了民族信仰在排除其历史消极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前提下,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其内质的和谐是其外向的社自然、社会、族群乃至国家和谐功能的保障;和谐的形态和原则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换言之,一种信仰是否具备上述和谐功能,只要看其本质是否追求内在的仁爱与和谐。
族群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保障功能:维系和保障族群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民族信仰核心功能的题中之意;没有信仰就没有文化,更没有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当我们真正认同了民族信仰从形式到内在义理的深刻的一致性,就会很自然地反省当下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头下开展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它们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将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和特定文化传人的保护普遍地当作了保护的重点和目标,而忽视了根本保障传承可持续进行的民族信仰和民俗生活的有效保护,致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个要求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有强大应用性特征的领域,至今还是一个实践超前而理论认知、理论建构严重滞后或不足的领域;该状况往往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性保护或保护性破坏。若将非物遗内涵边界扩展至“民族信仰”概念边界,改变一直以来以传承人为重点的思路,注重民族信仰生活在后现代情景中的复活,则可以从更本上实现民族非物遗的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赖于民族信仰和民俗生活在后现代条件下的重新植活。
结 语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次大的沦落:从神人时代到拜神时代,从拜神的信仰时代到去神的哲学时代⑳,从形而上的哲学时代到形而下的科技时代,终至神圣不复,人文沦丧,人类处于精神道德的底谷。中国民间信仰的复兴表现出对这个状况的反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各民族生活中,其传统信仰的生态性不仅是各民族自身信仰复兴的条件,也是人类信仰复兴的资源借鉴。在当今传统文化已趋崩溃的困境中,对尚保有生态性的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信仰的认识和强调已是刻不容缓;“民族信仰”概念本身因此而具有复兴的意义。
注释:
①见刘永华.“民间”何在?——从弗里德曼谈到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J〕.“民间”何在,谁之“信仰”.北京:中华书局,2009.25.
②见朱海滨.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民间信仰〔J〕.“民间”何在,谁之“信仰”.北京:中华书局,2009.47.
③[美]包尔丹著,陶飞亚等译.宗教的七种理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7、306.
④见宗鑫曼.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特殊性的初探〔J〕.青年文学家,2009,(17).
⑤即便有尝试实证者,其使用的也是物质科技的方法理念,结果自然是证伪,从而又否定了自我。
⑥和晓蓉.宗教和谐视角中的西藏佛苯关系浅析〔J〕.思想战线,2010,(3).
⑦参阅雷蒙·潘尼卡著,王志成、思竹译.宇宙-神-人共融的经验——正在涌现的宗教意识〔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王志成.走向第二轴心时代〔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⑧金泽.民间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⑨儒教作为一种信仰的出世面向,也是客观存在的,与其他信仰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超越性与神圣性,只不过在宋明以降历史上和五四以来的现实中都没有得到强调,而是被不断去神圣化。
⑩蒋庆.追求人类社会最高理想——中和之魅: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宗教性〔J〕.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zqlrshdzglxzhzmjqtzj.htm。作为西方传统来说作为西方传统来说,对宗教研究还存在着一种难以克服的神学偏见和文化偏见,这种偏见不仅影响了西方自身基督教神学及其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东方传统的宗教及文化研究,其一系列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还影响了中国学界对自身及东方传统宗教文化、神秘文化乃至民俗文化的研究态度和结果。
⑪几乎所有的创始神话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类曾经历了一个神人共处的阶段,诸多原因导致其与神的隔离,以及自身神性的蜕化。我们所有的相关研究如神话学的、心理学的实际已经逼近这个真相,但却又退缩,转而言其他,继续缘木求鱼的徒劳。如果我们不能跨越这个临界点,则我们的研究和认识永远都无法超越当下的悖论,处于自我心灵以及知识的分离状态。只要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很多根本性问题如人类起源、艺术起源、宗教起源等等长久困扰人们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⑫而与同样来自西方神学背景的“宗教”一词及其观念标准也不相应。限于篇幅,有关“宗教”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语境中的不相应性无法展开,留待以后讨论。
⑬蒋庆.追求人类社会最高理想——中和之魅: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宗教性〔J〕.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zqlrshdzglxzhzmjqtzj.htm。
⑭参见黄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西南民族文化与民俗——民族文化学的新视野〔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2-14.
⑮对这种特性的研究,应当成为民族宗教学和民族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尚无力展开。
⑯和晓蓉.宗教和谐视角中的西藏佛苯关系浅析〔J〕.思想战线,2010,(3).
⑰我并以此观点回应人类学非完整的整体观以及潘尼卡有关“多元论困境”观点。
⑱此类观点在唐·库比特那里达到极致,参其《后现代神秘主义》,北京: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⑲“心灵传承”是我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中,针对民族信仰文化本质及其传承特性而逐步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旨在创设一个新的视角,将各传统民族信仰及其文化表象统括起来并放到一个新的视界中加以观照、认识和阐述。相关阐述详见.民族心灵传承文化浅论〔J〕.思想战线,2008,(1).及.民族文化传承场的维护与再造〔J〕.思想战线,2009,(1).
⑳俄罗斯现代哲学是一个例外: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神人哲学是对西方去神哲学的超越。
“Ethnic Faith”a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cept——Based on the Re-understanding of Ethnic Religions and Current Situations of“Folk Faith”Studies
He Xiaorong
The upsurge“Chinese folk faith studies”has its profound social-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Yet from the point of this paper,the definition of“folk faith”itself and rela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are questionable in some certain senses,especially when facing the reality of ethnic society.“Ethnic faith”is thus proposed since it is more corresponding to the reality of ethnic society and valid in the practices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concerned.
Folk Faith;Characteristics;inheritance and regeneration
【作 者】和晓蓉,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昆明市:650091
C95
A
1004-454X(2010)03-0055-008
*本文为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项目学科建设项目“中国西南民族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关系”子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21131011-09011)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覃彩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