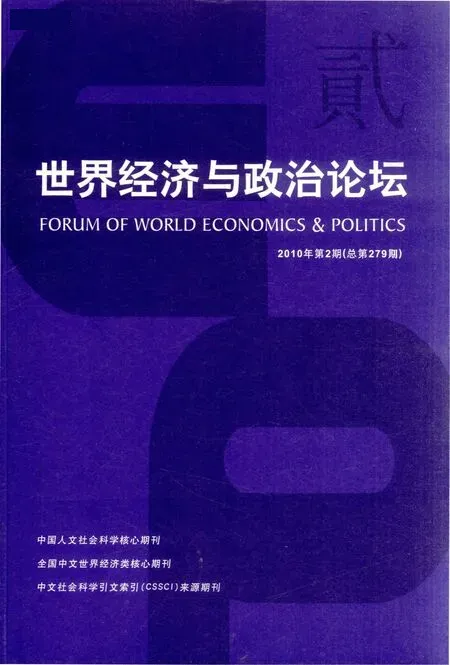伊朗因素对以色列-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影响
钮 松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便走上了一条以挑战国际秩序尤其是美国霸权、争当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区域霸主的道路。纵观战后历史,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东地区的战争主要集中在黎凡特(Levant)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埃及的西奈半岛,而80年代开始主要集中在海湾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今日的伊拉克。与巴以开启和平进程截然相反的是,海湾区域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接踵而至,海湾三强伊拉克、伊朗和沙特为首的君主国之间不断实现力量和结构的重组。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分别消除了伊朗东西两翼的宿敌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伊朗在海湾的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海湾形成了新的三强格局,即美国、伊朗和海合会国家。2009年初,美国奥巴马总统推出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该战略以撤兵伊拉克、增兵阿富汗为显著特征。一旦美国撤出虚弱的伊拉克,海湾相对稳定的三极格局就会迅速被打破。鉴于伊拉克新政府已由什叶派占据了主导而与伊朗实现了关系的完全正常化,甚至有着天然的同盟关系,因此,海合会国家面临着伊朗的极大威胁,这种威胁既包括安全威胁,也包括宗教教派的威胁。以色列在与埃及、约旦媾和,并与巴勒斯坦主流派实现了相互承认之后,其与阿拉伯国家保持了一种实际的和平共处状态。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走上了反以反美道路,这对以色列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以色列甚至先发制人摧毁伊朗的核反应堆。面对着伊朗力量的逐步坐大,尤其是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无论是海合会国家还是以色列都感受到了全所未有的压力和不安全感。面对伊朗这个共同的现实威胁,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开始了安全方面的接触和初步合作。但由于海合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盟主”沙特阿拉伯的特殊地位,如何在当前巴以和平仍未实现的前提下妥当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并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双赢对于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都是巨大的考验。
伊朗崛起对中东安全的影响
伊朗的崛起并非历史的偶然,自巴列维王朝开始便走上了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大肆宣扬日耳曼人的祖先“雅利安”人。德国“渲染种族主题,即伊朗人也是‘雅利安人’,且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通过将其指称为拥有殖民内涵及‘种族自卑’色彩的‘波斯’来贬低该国”①Sīrūs Ghan ī.Cyrus Ghani,Iran and West:A Critical Bibliography,Routledge,1987:166。为了消除伊朗历史上长期受英俄帝国的侵略和分治而造成的民族自信心空前低迷的状态,礼萨国王于1935年将国名从西方人所称的“波斯”正式正名为“伊朗”,伊朗的发音便来自于波斯人的祖先“雅利安”。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否定了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但是伊朗的神权领袖却继承了伊朗这个国名并进一步显示出争做地区大国的心态和举动。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实行全世界唯一的神权共和体制,不仅如此,伊朗的革命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伊斯兰世界首次开始成为主导的思潮。因此,这种体制的特点一是神权政治,即神权领袖和教法学家引导国家;其二是共和制,即反对君主制,既包括君主专权,也包括君主立宪制;三是激进性,这种激进容易导致在国际和国内的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这三个特点对于中东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伊朗什叶派对于君主制的反对招致了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的极大忧虑。霍梅尼就认为:“君主制等同于伪神、偶像崇拜和在地球上传播腐败”①Abrahamian E.Khomeinism: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24。巴列维王朝时代,伊朗与沙特等国同为君主制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相对平稳。伊斯兰革命后,沙特等海湾君主国遭遇到了巨大的压力。正是在伊朗明显且直接的压力下,沙特等海湾君主国联合自强,于1981年5月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形成合力共同防御伊朗。其次,伊朗什叶派政权对于国外什叶派的煽动极大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社会安定,伊拉克和巴林便是显著代表。伊拉克和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比例多于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但掌权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对于伊拉克,虽然萨达姆政权并非君主制,但萨达姆早年对于霍梅尼的不友善以及伊拉克是海湾唯一能与伊朗抗衡的国家等因素导致伊朗极力煽动伊拉克什叶派推翻萨达姆政权。巴林虽然是小国,除了君主制原因遭致伊朗的威胁之外,其什叶派占据主导也是主要原因,不仅如此,伊朗对其还有领土要求,声称其为伊朗的一部分。除了伊拉克与巴林这两个什叶派占据主导的国家之外,沙特虽然什叶派人数较少,但伊朗将他们作为颠覆沙特王室的突破口,“最为感受到威胁的国家是拥有什叶派少数群体的沙特阿拉伯”②Marschall C.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from Khomeini to Khatami.Routledge,2003:26。最后,伊朗的激进革命输出以及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支持极大威胁了以色列的安全,这种激进主义又与萨达姆的世俗主义的激进军事政策相碰撞。真主党和哈马斯分别在1982年黎以战争以及巴勒斯坦第一次“因提法达”中得到伊朗的有力支持而建立,是其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重要成果,这两个组织思想激进,成为所在国家内部拒不妥协、拒不承认以色列的武装力量,虽然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巴以和平进程而言其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萨达姆具有称霸海湾地区的雄心和激进的军事政策与其前任巴列维国王以及贝克总统的稳健政策有着很大不同。正是伊朗的反君主制、煽动什叶派对抗以及其激进的革命输出等三个方面导致了伊朗与海合会国家、伊拉克、以色列的剧烈碰撞和摩擦,并酿成八年的两伊战争以及持续至今的真主党、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
两伊战争期间,无论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是海湾君主国都积极支持伊拉克,这对于伊朗是极大的牵制。伊朗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其革命输出的激进主义有所收敛。萨达姆突然入侵科威特使得局势逆转,美国与伊拉克反目成仇,海湾君主国也对于伊拉克抱有极大戒心。伊朗所承受的国际压力和威胁开始主要转移到伊拉克,伊拉克开始得到美国的重点打压直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为止。伊朗利用海湾战争后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积极推进其核计划的开展。对于美以而言,霍梅尼的伊朗拥有核武器对于自己而言是致命的威胁。对海湾君主国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尽管伊朗核计划有抗衡以色列的作用,但这对于除叙利亚之外的阿拉伯人也是巨大的威胁。与西方与伊拉克和利比亚关系的持续僵持和恶化相对应的是伊朗采取了一定的务实政策,在欧盟与美国之间不断寻找突破口,其核计划一直未间断。随着“9·11”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来的是伊朗宿敌塔利班政权的败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以及伊拉克和利比亚核计划的彻底偃旗息鼓,伊朗事实上已成为海湾地区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地区强国,这也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伊朗的崛起对于海湾君主国以及以色列都是最为直接的安全威胁,对于以色列而言,伊朗内贾德政府具有激进的反以色彩,而对于海湾君主国而言,伊拉克和利比亚和计划的失败意味着阿拉伯人核计划的失败,伊拉克新政府倒向伊朗这对于它们的安全感而言尤为重要。美国在中东问题尤其是伊拉克问题的解决上不得不需要伊朗的合作。尽管2006年开始伊朗核问题成为美伊关系的核心问题,但美国再也难以考虑单边军事行动解决该问题,伊朗核问题始终在多边合作的集体安全框架内来寻求解决。虽然自2009年因总统大选争议而来的政治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但伊朗现行体制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
总而言之,伊朗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建设和免费搭乘外力扫清宿敌的便车使得其成为海湾地区综合实力的霸主,伊朗对于中东地区的海湾君主国和以色列构成了最大的安全威胁,而且这种威胁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以色列-海合会关系的发展与障碍
由于阿以之间围绕以色列建国业已存在的长期矛盾与战争,以色列与海湾君主国之间长期以来并没有外交关系或实质关系,海湾君主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沙特阿拉伯甚至派兵参加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但此后的数十年内,海湾君主国主要通过道义而非武力的方式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20世纪80年代,伊朗因素开始成为影响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的新因素。在此种情形下,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实质上仍处于对立状态。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94年巴以“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巴以关系的突破和缓和以及随之而来伊朗威胁度的凸显促使海合会成员国卡塔尔和阿曼与以色列建立官方联系和经贸关系。
沙特阿拉伯属于不与以色列发展任何公开的官方或商业往来的海合会国家,尤其在“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其对以态度仍无缓和。但实际上,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定位非常具有针对性,囿于其“伊斯兰盟主”的身份,沙特难以与以色列建立公开的官方关系或者发展经贸关系,但沙特作为海合会的领头羊以及海湾大国,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对以关系主要出于防范伊朗的考虑,沙以之间的安全合作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整体关系进展迟缓,其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双方关系与巴以和平进程紧密联系甚至交织在一起。海合会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涉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两大方面。奥斯陆协议以前,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当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其背负“叛徒”的骂名而遭到空前孤立;奥斯陆协议之后,巴以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阿拉伯国家从拒绝对以色列的承认转到期望巴以和平的尽早实现以及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尽早建立。由于巴以之间关系进展曲折、反复,暴力冲突不断,其前景黯淡,这为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最终改善投上阴影,迄今仍只有埃及、约旦、突尼斯三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①毛里塔尼亚曾于1999年与以色列建交,2009年3月断交。,海合会国家位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区域,尽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号召力日渐衰微,但伊斯兰教的号召力却没有丝毫减退,因而其正式承认以色列并与以建交亟待中东和平的实现才有可能实现。其次是海合会国家内部的不团结导致难以有整体的对以色列和对伊朗政策的出台。对以政策方面,卡塔尔和阿曼发展半官方联系以及经贸关系,沙特发展安全和军事方面的合作,科威特与阿联酋没有明确表态,而巴林则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甚至决定对与以色列接触的公民判刑;对伊政策方面,各国均对于伊朗有着戒心,尤以巴林的态度最为坚决,但除沙特之外的海合会国家皆为小国,它们也有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左右逢源的外交设想。尽管海合会国家与以色列关系进展存在着根本的障碍(巴以和平)和制度的障碍(海合会外交机制建设的滞后),但伊朗在海湾的崛起以及核计划的不断进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伊朗称霸海湾的动机和行动越来越明显,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巴以和平进程,在此情形下,海合会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因伊朗因素的进一步推进就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与可能性。
以色列-海合会未来关系可能的走向
尽管以色列与部分海合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开始了官方接触、经贸合作、互设代表处以及秘密的安全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但在面对伊朗的崛起以及其核威胁这个共同目标时,海合会国家的利益相对一致,沙特的选择是:要么伊朗对海合会国家进行分化组合而使沙特力量削弱;要么整合海合会,建立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使得以色列与海合会国家的一对六的关系简化为以色列与海合会之间的一对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伊拉克加入海合会对于其过分亲伊朗也会有一定缓解作用。以色列-海合会关系未来可能的走向如下:
首先,海合会与以色列可能建立一定的政治联系。海合会的成立的动机最主要来自于海湾君主国对于对于伊朗的防范,这个重心迄今仍无改变,但从机构建设上,海合会最初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身份出现,近年逐渐向经济—政治组织转变,即具备国际组织与贸易集团的双重属性。尽管海合会成立动机在于防范伊朗,但其经济一体化进程乃至机构的制度化建设处于阿拉伯国家各种区域组织的前列,是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善的组织。海合会迄今没有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但这不影响海合会的对外交往,尤其是经贸交往上,海湾君主国以海合会的集体名义参与国际关系,目前已与欧盟、中国等许多组织和国家启动了自由贸易谈判,其在国际交往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权国家职能。海合会设立负责对外事务的专门机构从长远看非常有必要,可以深化政治一体化的步伐并在国际社会中发展成为如具有集体力量的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在伊朗地缘政治地位愈发凸现、伊核问题日益危急的时刻,作为主权国家的海湾君主国在目前巴以局势下难以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前提下,以海合会作为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平台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这样既可以统一在对伊问题上的政策,可以在非主权国家的层面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①欧盟在这方面便是例证,欧盟的邦交国不一定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邦交国,但这不妨碍彼此之间的合作。总而言之,海合会的集体行动能够起到免责的作用。
其次,海合会可以深化军事一体化进程,并与美国、以色列建立军事联盟或准联盟关系。目前海合会作为一个以“民事力量”为主的“贸易国家”国际行为体,其组织对外交往主要以经贸合作等非军事的方式进行,其目的并非获得军事霸权或以军事作为对外交往的方式。但民事力量的贸易国家并不代表着不拥有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工具而非主要方式。欧盟实际上早在1984年海合会便成立了联合军事指挥部,并于次年成立了5000人的“半岛盾牌”部队,但这支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十分欠缺。海合会在总秘书处下设军事事务部和安全事务部来处理相关事宜。海合会国家主要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但这种军事依附无论是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还是伊朗的崛起上都是具有重大缺陷的。2009年12月15日,海合会国家通过了“海湾共同防御协议”,并打算组建联合部队以增强集体防御能力,这个“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直接原因是因为也门判乱者在也门与沙特边界制造的冲突。海合会的军事合作有着深入的考虑,也门并非其安全威胁的重心。2009年12月16日,巴林外交大臣认为海合会国家缺席IEAE、美国和伊朗关于伊朗核问题谈判是“这场谈判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①Stracke N.What Could the GCC Have Done on Iran?.Khaleei Times,December 16,2009。这些说明军事力量建设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海合会国家的重点考虑。就目前双边军事合作来看,尽管海合会多国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在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建有军事基地,积极出售先进武器并提供军事援助,如帮助阿联酋建立反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为了帮助海合会国家抵御以色列与伊朗交战之后而遭受来自伊朗的袭击。但海合会国家在面对伊朗军事威胁的时候实际上处于一种整体状态,各国分别与美国的军事协议、军事设施的建立缺乏协调,因此除了海合会自身向军事力量的某种变形之外,建立海合会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合作或者海合会与以色列的准军事联盟关系将有助于军事资源的协调从而避免重复建设,在遇到伊朗威胁时也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及时对海合会提供某种军事支持从而避免与海合会各国分别协商与沟通。
最后,海合会可积极参与伊拉克重建,并最终吸收伊拉克为海合会成员国,这对于改善海湾君主国与伊拉克关系以及以色列与伊拉克关系从而削弱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会有着一定推进作用。海合会的成立兼具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其最终结果在于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收益。萨达姆与霍梅尼于1979年分别在伊拉克和伊朗的掌权,海湾局势陡然紧张。尽管两国均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海湾君主国对于伊朗的恐惧远甚伊拉克,在两伊战争间成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全名自然将伊朗排除在外,借助伊拉克抗击伊朗也只是权宜之计,因而伊拉克也被排斥在海合会之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遭致了海合会国家的不信任,海合会国家参与了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军事威胁。但随着2003年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以及伊拉克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伊拉克从黩武极权的军事国家向和平民主的贸易国家过渡,这就为海合会国家与伊拉克实现经济合作乃至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伊拉克战后重建以及经济发展除了加强与西方国家合作之外,立足本区域参与海合会经济一体化是不错的选项。伊拉克参与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助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整合国内的分歧与分裂,尤其是生产石油的库尔德区与其他省份的融合。海合会吸收伊拉克,除了经济收益之外,这也是其解决地区冲突、减少极端主义势力的手段之一。海合会吸收伊拉克将有助于伊拉克重建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伊拉克与伊朗的什叶派同盟关系。由于海合会君主国和以色列目前最为担忧的是伊朗威胁,因此若能吸收伊拉克入会将促使伊拉克在海合会的框架内协调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对伊朗和对以色列政策,这将改善伊拉克与以色列的关系,提升海合会与以色列可能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合作层次。伊拉克经过数十年的世俗化熏陶以及美国的民主改造,并不具有伊朗般的神权政治思想,这也为伊拉克与海合会、以色列的未来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结 语
伊朗的崛起以及核计划带有明显的非和平特质,在此情形下,它带给原本敌对但关系相对缓和的国家之间如以色列与海合会之间基于安全考虑而走向某种可能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但这种合作仍旧是非常规的合作,其基础也是脆弱的。中东和平的实现虽不能一蹴而就,但要从点点滴滴开始,就以色列与海合会而言,要真正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就必须认真解决巴以问题,既要维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益,也要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就伊朗而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并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尊严,在全球核扩散危险日益加剧的情形下谋求发展核武器并不能真正达到安全化。只有参与国际体系,在参与中谋求游戏规则的改变,认真从事经济建设从而实现国强民富并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产品才是和平崛起的地区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