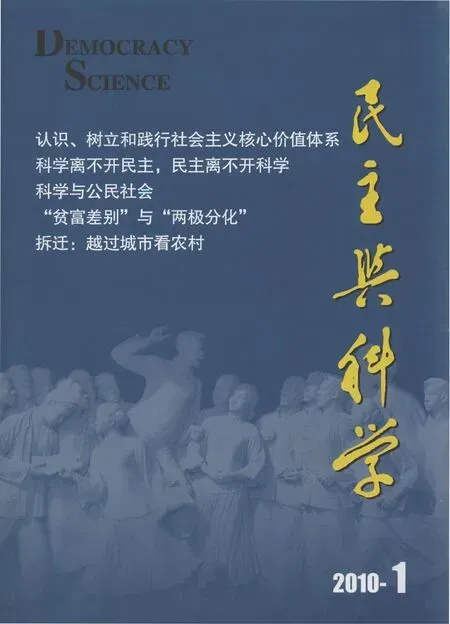拆迁条例究竟要改什么
■张千帆
拆迁条例究竟要改什么
■张千帆
成都被拆迁户唐福珍自焚事件再次使拆迁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焦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也自然成为社会拷问的对象。虽然此次自焚悲剧其实是农村“拆违”引起,并不适用城市拆迁条例,但是就从条例授权的强制拆迁已经造成不计其数的社会冲突和悲剧来看,拆迁条例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已经表示,将以《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取代拆迁条例。不过拆迁的作用只是强制执行预先制订的城市规划,并非造成拆迁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和收容遣送是实施户籍制度的手段、城管是实施有关市容、卫生等城市治理的手段一样,拆迁只是政府完成市镇规划的手段;这个地方按既定规划要拆迁改造,而“钉子户”限期不搬、劝说无果,那么政府只有强制执行——就这么简单。事实上,哪个国家都得执法,哪个政府都得有执法权,甚至可以说哪个国家都有拆迁——只要是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能没拆迁吗?至于网上流传的国外“最牛钉子户”逍遥多年、“违章建筑”巍然不倒,不过是开发商或政府出于恻隐之心而没有出手的个别例外,要采取行动是完全可以的;如果美国“钉子户”限期不搬,那么政府照样会强制“拆迁”,或许出手还比中国更快更猛,暴力抗法的“钉子户”肯定被送进监狱。那为什么人家拆迁就没有发生我们这里的冲突和悲剧呢?或更准确地问,为什么人家就没有我们那么多“钉子户”呢?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简单修改乃至废除一个拆迁条例就能解决得了的,或者说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条例的修改必须触动更深层次的制度。固然,各地拆迁悲剧大都是由拆迁暴力引起的,但是拆迁条例本身显然没有授权这种暴力。在法律上,拆迁条例的主要问题是让拆迁“吃掉”了征收和其它所有程序。令人吃惊的是,这么多年来竟找不到一部直接规范拆迁的上位法。宪法规定了征收必须“给予补偿”,但是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补偿”,而拆迁条例第四条也要求“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物权法》第42条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但这一条是针对“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而不适用城市拆迁。要说拆迁条例违法或违宪,主要是因为条例意义上的“拆迁”实质上是财产征收而非单纯的执法过程,而条例没有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就授权剥夺公民私产。然而,即便拆迁条例变成了《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拆迁必须以征收作为前置程序,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经过征收程序的农村征地发生了那么多事,足以告诉我们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此。拆迁之所以造成了那么多罪恶,过错不只是在于一部条例,而在于这部条例所要实现的城市发展规划及其所折射的发展模式。
当今中国城乡之所以有那么多拆迁,而拆迁又造成那么多暴力,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实行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近三十年来,中国GDP高增长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后果与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市场活力,二是政府主动推进城市化、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主导模式固然可以为市场经济发展打下一定物质基础,但在根本上是违背市场经济逻辑的;用政治力量发展经济不仅带有市场之外的成本,挤压市场力量的发展空间,而且也为政府寻租创造巨大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总是民营经济占主动和优先地位,政府的作用则是消极和第二位的,主要限于纠正市场自身的某些缺陷,譬如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基本福利、保护资源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等。如果政府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却去主动介入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今天的发展代价:不仅食品安全没人监管、生态环境没人保护、贫困家庭没人照顾、社会保障体制落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且权钱交易盛行、公权滥用严重,而整个社会也被带入非理性发展的歧途。因此,修改拆迁条例不只是要改其中某些程序和规则,更重要的是改革违背市场规律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
在目前自上而下的政绩体制中,地方GDP一直是衡量官员表现的主要标准,而农村城市化和城市拆迁改造自然是提升地方GDP的捷径。仅此一项便足以解释中国的地方官员为什么总是对拆迁、征地、基础建设项目如此热衷,而对于执行那些项目又表现得如此急切。更何况在缺乏宪法约束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项目都有大量“油水”;征地和拆迁意味着政府可以收取土地转让金,或通过低价征收、高价转让和开发商分享征收利润,不仅为地方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而且也成为一些官员个人“灰色收入”的来源——今天有哪个贪官不和“开发”、“批地”、“修路”发生点关系?一旦征地拆迁和地方官员的仕途财路划上等号,那么我们的农村必然会以“大跃进”的速度城市化,而我们的城市则永远是一个不太平的大工地。在规划方案没有市民参与、拆迁补偿又得不到宪法保障的情况下,我们见证了公权力和私权力最糟糕的合作方式:开发商替政府赚钱,政府则授权开发商拆迁,让他们拿着公权力的“尚方宝剑”作为压低补偿的砝码;失去生计的被拆迁户不得不铤而走险、激烈抵抗,而急不可待的政府或开发商必然会动用合法或不合法的公权力强制拆迁……不打破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拆迁或征地悲剧就必然是土地财政和“政绩工程”的衍生物。
在我看来,中国是没有理由延续这种社会代价巨大的发展模式的。近一二十年经济确实增长很快,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却难说提高了多少。食品丰富了,但是也变得不安全了;商品充足了,但是资源耗竭了,环境恶化了;老百姓的钱更多了,但是被上涨更快的房价、物价、学费等等抵消了……让我们还是把属于政府的还给政府,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政府应该先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而不要直接插手应该由人民自己通过自愿交易完成的事情。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改造一定需要政府主导吗?没有政府主动征地,中国农村是不是就不能现代化?没有政府积极规划和拆迁,中国城市是不是就不能改变面貌?我认为不是这样。不要忘记,今天城市的许多房子之所以要拆,正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单位这个“小政府”造的房子太破旧,城市居民的住房质量还是在住房商品化之后才得到实质性改善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城市居民和开发商自愿协商开发小区呢?为什么不能让开发商和农民自愿协商自然而然地实现城市化呢?没有政府主动干预,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改造不仅会进行下去,而且会正常、理性与和平得多。政府可以审批(譬如为了控制耕地)、可以监管(譬如为了保障建筑质量)、可以裁判(为了解决私人争议),但是政府不能也没有必要直接成为城市化或城市改造的“推手”,否则被拆迁户自焚之类的场景就会不断重现在中国各地。要从根本上避免悲剧重演,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职能。
当然,在自上而下体制不变的环境下,各地政府是闲不住的;要消除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冲动,必须遏制“政绩工程”和土地财政。要遏制“政绩工程”,至少要让城乡规划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过程。毕竟,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农村也是农民的农村;中国城乡发展规划必须由城乡的主人说了算,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不能想拆哪里就拆哪里、想征哪块地就征哪块地。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国家所有”显然是指全民所有而非“政府所有”,政府只不过是土地的管理者而非所有人。即便土地的全民所有权太大太空,土地的使用权是具体的,人民对如何使用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有发言权;附着在土地上的房屋更是属于人民所有,人民显然对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有发言权。作为管理者的政府无权以土地所有者自居,什么时候想征就征、想拆就拆,并强迫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的主人搬走。财产征收(也就是拆迁)必须符合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而官员“政绩”显然不等于影响百姓生活的公共利益。政府官员在乎“政绩”和GDP,但是老百姓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只希望住在一个安全、无污染、有保障的地方,而不用担心失去自己的房子或土地。要保证征收和拆迁确实符合“公共利益”,而中国城乡得到符合基本理性和人性的发展,就必须由当地老百姓参与规划。
我注意到,拆迁条例修改草案尝试将“公共利益”区别于“商业开发”。这种界定固然必要,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颇难把握。这主要是因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很难通过一张清单罗列清楚,或者即便制订这样的清单执行起来还是会扯皮,因而即便美国、德国等法治国家的法院也基本上放弃了公益界定,而将其留给地方民主政治过程处理。“公共利益”是一个政治概念,征收是否符合公益未必存在客观标准,而主要取决于当地人民是否满意,因而自然离不开地方民主参与。因此,与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界定“公共利益”,不如完善保护“公共利益”的民主决策机制。政府规划过程应按照《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做到公开透明,征地、拆迁以及安置补偿方案必须及时公布,并广泛征求当地人民尤其是拟拆迁地区居民的意见。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政府关起门来规划、和开发商悄悄分红,等一切都内定了再通知被拆迁户限期搬迁、否则就诉诸各种强制手段,那么不仅无法避免大量幕后黑色交易,而且也无法防止层出不穷的拆迁或征地悲剧。广州番禹经验告诉我们,连垃圾处理方式都需要有效的公民参与才能得到理性解决,否则会出大问题,更何况和人的基本生存攸关的拆迁或征地呢?
断绝土地财政则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在保证地方民主监督的基础上,中央有必要下放部分财税立法权,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正常的征税过程满足正当的财政需求。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得到保障,但是某些地方财政却遭遇困难,从而在客观上加剧了土地财政趋势。如果不改变税收立法的中央集权体制,那么至少需要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源,使地方财政足以承担正当的地方公益事业,同时进一步精简地方机构,尽可能减少地方冗员和挥霍浪费。当然,在自下而上民主机制不能确立的情况下,第一点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只有落实“公正补偿”原则,才能防止拆迁或征地成为地方政府生财之道。如果政府必须按照公平市价给予补偿,如果被征收的土地或房屋在市场上值多少政府就必须补偿多少,征地或拆迁成本很高、在原则上不再是赚钱的行当,那么地方政府也就不会那么热心征收了。中国城乡得以在自愿自主基础上按照市场规律稳步发展,各地自然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拆迁或征地悲剧了。
在此基础上,可以比较拆迁条例的三种修改方案。一是在现有拆迁条例上小修小补,旨在完善拆迁必须经过的行政程序,但是这种方案显然不足以解决中国拆迁或征地出现的问题。二是索性像当年废止收容遣送办法那样废除整个拆迁制度,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执法模式取而代之。其实作为正常的执法手段,本来是没有必要专门规定拆迁或收容遣送的,而我们之所以需要专门的拆迁条例和收容遣送办法,正是为了执行国家的特殊使命——城乡发展和户籍制度,以至于拆迁和收容遣送成了地方政府的常规职能。如果目的已经失去了正当性,那么手段自然也应跟着废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之所以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最终是因为户籍制度本身不正当;现在政府主导的城乡发展模式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其正当性已经受到如此严重的质疑,是否还有必要保留拆迁作为特殊的执法制度呢?我认为,如果中国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削弱政府主导作用、走向真正的市场发展模式,那就没有理由不废除拆迁概念;但是如果一时达不到这个目标,如果政府主导的规划、征地、拆迁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引擎,那么简单废除拆迁不但不能改善现状,而且还会因为公权力进一步失序而加剧政府主导模式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规范征地和拆迁领域的公权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但是从根本上修改拆迁制度。这就是第三种方案。
不论是取代还是修改拆迁条例,新的法律方案必须建立在重新认识并建构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城市改造和城市化过程应该主要由市场力量带动,由私人各方通过自愿交易达成协议进行;开发商应该和居民而非政府直接打交道,如果居民不同意开发方案就只能作罢,根本谈不上“拆迁”。政府的角色应限于仲裁者而非当事人,征地和拆迁应成为中国社会凤毛麟角的稀罕事,而不是政府乐此不疲的家常便饭。在这个前提下,如果确实还需要动用公权力征收或拆迁,则必须满足如下基本条件。第一,程序重心必须从目前关注的拆迁前置到城乡规划和征收。拆迁只是整个程序的最后一步,而公民参与必须被提前到第一步;拆迁程序应被归并为征收程序的一部分,作为决策程序完成之后才能启动的执法步骤。程序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在于保障公民对整个规划决策过程的有效参与,公民参与的范围包括城乡区划、开发选址、改造方式、征收补偿标准等事项。第二,城乡规划方案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公民参与是保证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的第一道屏障,而公平市价的补偿标准也迫使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以资源利用最优的方式发展中国城乡。最后,公民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应通过民主和法治机制加以解决,尤其是安置补偿标准应经过独立和中立的评估机构审核,最终可经过司法裁判确认。
这样的程序看上去相当费事,但这也正是其目的所在:征收和拆迁以性命攸关的方式影响着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政府决策能草率吗?如果新法规定的程序如此麻烦,以至地方政府不胜其烦、最终放弃,而整个中国社会也可以按照市场规律和自身需要正常发展,而不是继续在政府主导下“被发展”,那么唐福珍事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甚至会超越当年的孙志刚事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