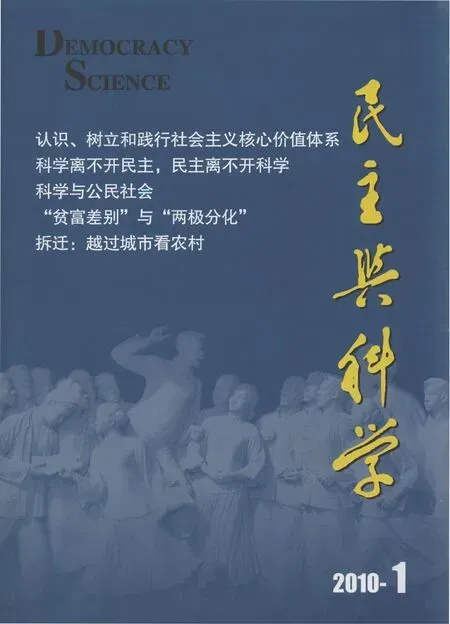科学与公民社会
■李大光
科学与公民社会
■李大光
科学研究学科分类的精细和研究手段的复杂,使得科学和技术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拨款控制导致整个研究过程呈现出科学仅仅是政府和科学家团体之间的事情。但是,科学研究成果最终体现在技术和工程项目的实现。公众作为科学研究项目的纳税人的身份在整个过程中被隐去,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是否能体现公众的利益成了难解之谜。时代似乎在呼唤公民社会的出现,但是,公民社会,谈何容易。
飞速的科学与瞠目的公众
近些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其迅速。科学的飞速发展再次引发公众态度的变化,同时也深度冲击了公众的传统认识和伦理意识。在科学事件中,最具有冲击力的是对宇宙起源的探索和生命科学的最新研究,这些重大进展引发了人们的讨论以及争论。
2008年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基础物理学研究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3月,苏黎世地下100米深处,欧洲科学家建立了强子对撞机实验室。这个强子对撞机加速器中心规模巨大,27公里长的隧道横穿法国和瑞士。它的能量使它能够模仿宇宙诞生一千亿分之一时候的物质状态。其内部共有9300个磁体,其制冷分配系统的八分之一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制冷机。在环形的对撞机轨道上,质子束以接近光速,以每秒6亿次速度撞击,产生粒子浓汤,科学家将从粒子浓汤中分离出反粒子,从而重现宇宙大爆炸的瞬间情景。这个对撞机的建立被认为是世界基础物理研究中心从美国转移到欧洲,从1999年以来,科学家基础物理研究进展缓慢的状况将会发生改变。物理学家希望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对宇宙中种种神秘现象,如暗物质、超对称粒子等展开新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一种到现在为止尚未发现的次原子微粒,名为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被霍金称为“上帝粒子”,它是人类现有理论预言中唯一还未发现的基本粒子。如果它根本不存在,那么倾向于多维时空的其它理论会变得更有说服力。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甚至拿出100美金打赌自己的黑洞理论将得到证实。但是,按照他的理论,黑洞将吞噬宇宙间所有的物质,甚至光都难以逃脱。消息传出,欧洲舆论哗然。很多人认为,科学家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应该为纳税人谋幸福和利益,这样的研究违背了公众的利益。许多社会组织用各种方式提出抗议。其中NGO组织和环境主义者,甚至一些科学家团体都走上街头,提出抗议。消息传到印度,中央邦的一个16岁女孩,竟然自杀。
但是,反对声音最大的还是来自科学家内部。2008年9月10日,大型强子对撞机将要开展对撞试验。对此,一些欧洲科学界人士声称,认为实验产生的黑洞可以吞噬地球。或者,强子对撞机将产生一类名为“奇异微子”的粒子,将地球变成一团沉寂、收缩的“奇异物质”。他们甚至到法院起诉资助该项目的20个欧洲国家,要求停止或推迟这个项目。据“新浪科技”报道,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联邦法官面对科学难题,一直在犹豫是否要考虑联邦政府的请求,驳回由前核安全专家沃尔特·瓦格纳和西班牙科学作家路易·桑奇联合提起的这起民事诉讼案。而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法院同意审议主要由德国和奥地利教授和学生提出的强子对撞机可能导致世界末日来临一案。不过,法庭拒绝了他们提出的立即中止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请求。
该报道还说,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的诉讼案中,原告都声称,关于这台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描述均未能准确表达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其中包括全球范围的小黑洞及物质变异或单磁极化等等,要求对该项目开展进一步的安全评估。而被告方——美国能源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物理中心却辩称,一系列安全测试报告的结果表明,上述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上述安全报告由业内领先的高能物理学家执笔,认为,与强子对撞机的对撞相比,宇宙光的碰撞能量和频率都要高许多倍。如果大型强子对撞机能引发全球大劫难的话,那么即便在最不可能的条件下,广阔宇宙中早已应经历了许多次灾难。据说官司现在仍然在进行,公众的示威和反对之声仍然强烈。2009年8月13日,美国《斯坦福日报》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工程学家斯蒂文·奎科(Steven Quake)发明了商用人类个人基因组解读器。任何想获得自己的基因图谱的人都可以仅仅花费48,000美金,在4个星期内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全部基因图谱。自从1975年美国科学家桑格发明了基因图谱解读技术以后,科学家已经在1990年实行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到2003年,个人基因图谱解读已经实现个人基因图谱解读费用为50万美金。美国科学怪人温特已经用100万美金解读了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华生个人基因图谱。斯蒂文·奎科的发明意味着今后任何人,只要购买回这个体积仅为冰箱大小的机器以后,都可以在家里就完成自己的基因图谱解读,了解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孩子获得某种遗传疾病的可能性。获得基因解读谱的人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以后,都可以根据自己患病的危险采取措施。比如通过干细胞移植技术修补自己缺损的基因。我们很难想象,采用这种技术以后,人类的寿命会有多长。但是,在这个惊人的科学成果出来以后,理论学家又开始担忧,假如按照科学家所说,人类的寿命会延长到300岁甚至更长,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教育体制都需要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人类犯罪率会上升,人口剧增导致资源的紧张,甚至国家领土问题,以至战争的频繁等等。
美国为了降低个人基因全图谱解读的成本,“X Prize”基金会准备拿出1000万美金资助100个个人基因图谱解读,争取在2012年将解读价格下降到每个人5000美金。生命科学为我们带来了科幻世界一般的未来梦想: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交纳几千美金,在带孩子出院的时候,就可以带走一个载有孩子基因图谱的光盘。在解读以后,就可以基本知道祖父母、父母和后代遗传疾病的可能性,甚至可以知道在某个年龄段将会患病,或者患遗传病,甚至可以知道自己的寿命。在得知了遗传疾病以后,就可以通过干细胞移植技术,在专门培养的迷你猪体内克隆自己的器官。通过一般的手术就可以进行器官移植。人的寿命将大幅度延长。但是,生命科学的飞速增长也会带来宗教与信仰的冲突等问题。比如,当人类在发现通过干细胞可以克隆与自己身体器官相同的替代器官以后,人类移植肺、肝和心脏等器官都是完全可能的。
在生物技术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时候,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需要得到医疗的时候,他该在自己的信仰和生命之间如何选择呢?
朦胧中的中国公民
科学家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无异。他们都生活在某一个特定时代的评价体系中。科学家的成就与获得课题经费,完成质量以及社会评价有关。技术开发人员与企业效益直接相关。科学家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经济社会中都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或者战争时期,科学就与当权者的利益相一致。二战期间,为纳粹工作的物理学家差一点赶在“曼哈顿计划”前生产出原子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731部队”中的医学科学家应该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同时,在纳粹集中营中用犹太人和战俘进行眼睛手术,以使他们更接近日耳曼民族的试验的也是最优秀的科学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不可能完全是纯粹的科学目的。既然这样,科学家活动的结果就有可能与普通公众的利益不一致。那么,在科学家道德和社会约束机制不存在或者缺失的情况下,公众的利益就很难保证。
近些年来,重大的与公众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不断出现,其中很多事件与科学、技术和工程相关。比如,萨斯、禽流感、圆明园防渗膜事件、“汉芯”事件、太湖巢湖蓝藻事件、西部水利大开发争论、怒江大开发的争论、厦门PX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中西医争论、伪科学的争论、珍奥核酸事件、转基因农作物、苏丹红、蒙牛OMP、安全饮用水、院士作假、华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垃圾焚烧等等。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公众对科学技术还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家团体的信任度在下降。其中一个不信任就是信息不透明。
法国科学传播教授比埃尔·法雅赫(Perrier Fayard)认为世界上科学传播信息基本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计划模式。这种模式是传播者将自己要传播的信息事先准备好,然后在一个信息传播处(比如科学技术馆或者科技节)将至少80%的自己要说的话展示出来。但是这种模式只会吸引来对你准备的话题感兴趣的人,而不了解这个领域知识的人就会吓跑。另一种模式就是自由模式。这种模式只事先准备很少的信息,而安排很多有关科学家在现场进行解释和回答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埃尔认为,第一种模式告诉公众的是信息,而不是科学。只有第二种模式才能完成真正的科学传播任务。因为他们告诉公众的是公众最需要的。第一种模式虽然效果不好,但是,轰轰烈烈,场面热闹,这是政府最喜欢的模式。第二种虽然不那么热闹,产生的效果更好。政府或者科学家团体在躲避自身责任或者追求效应方面一般会采取以政府目前的利益为主。避重就轻或者将自己的利益隐含在一种隐晦的说法中,是惯用的手法。在厦门PX事件中,在不得已而必须召开的公众听证会上,负责环境评估的化学家将“所有的”环评报告和各种数据都提供给了听证会的听众。你不能不说他的态度是公开的。但是,所有面对复杂的化学公式和数字的人,除了骂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没有选择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以外,得到了什么呢?出色的“科学普及”和坦诚的“科学结果公开化”,将自己的结果得到最有效的保密。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赵玉芬这样的科学家,如果没有公民自发的“散步”,如果没有两会期间104位良心科学家的联名动议报告,如果没有那位新华社记者的数码相机将报告直接送到温家宝总理的桌子上,厦门政府会有最后的“英明决策”吗?
为了保证科学符合公众的利益,1989年在丹麦诞生了“共识会议”制度,很快传遍全世界。每当一种新技术要使用或者新工程要上马,科学家共同体或者有关部门要召开公众听证会。这种模式被称为丹麦模式。美国科学基金会在研究项目确定以后,都要将研究内容在网上公布,所有的人都可以登录查看,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反对一个科学研究项目也可以上街游行。公众反对声音大的项目,很可能导致下一次评审时受到影响。在重大的资源开发项目过程中,比如,在旧金山要开发油田的时候,必须进行公民投票。一种只要发动,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车灯都会大亮的新车制造技术也需要得到公众的听证会同意。其实,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是大家的事情,这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财产,使用必须经过大家同意。如果你真心是在获得大家的同意,那么,你就一定会使用大家都懂的语言。牛顿早在将近300多年前就说:“虚假的事物可以随意想象,惟有真实的事物才能被理解。”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你一定会被人理解。如果你的假话被人揭露,你的人格也就失去。
中国社会在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在飞速发展。快速的发展使人欣喜,但是,短桶板效应就会凸显,那就是,公众不理解,在不理解的同时,任何打着科学旗号的东西他们都信以为真。中国的公众是世界上最憨厚朴实的公众。他们热爱和崇拜任何一个主流声音推崇的东西。但是,朴实憨厚的人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一旦发现自己被忽视或者被欺骗,他们又很难重新燃起往日的热情。中国的科学传播必须将真实的科学发展告诉公众,人民才会拥护你们,科学事业才会有美好的前途。
公民社会是怎样炼成的
科学发展导致利益集团运作的手段的多样化。地方政府利用科学追求经济利益;企业利用实用技术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科学家和学者利用科学研究成果获得学术成就,从而获得经济利益。惟有手无寸铁的公众,除了采取“散步”的唯一方法,谁来保证他们的利益呢?最近不断出现的垃圾焚烧事件,再一次将公众的利益引入社会议论中心。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大众阶级形成维持国家秩序的政权国家。大众赋予了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通过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这种通过“君权民授”的方式,使得整个社会得以运行。国家(state)的稳定取决于公民社会是否存在以及这个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这个公民社会的活跃与否取决于他们法律的认可与允许、国家管理信息的透明程度、公民对自身利益的敏感性、讨论自己利益的自由度、讨论结果信息的发布有效性、公民选举权与参与决议权。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法国、荷兰等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赫胥黎等人的大众科学运动的催生下,欧洲的公民社会迅速形成。首先是英国的科学咖啡馆(CafeScientifique)和法国的沙龙公众舆论聚集团体的形成。天文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起源以及宇宙的形成,甚至上帝的存在等问题的讨论。生产与销售科学仪器的公司开始出现,科学仪器进入到贵族家庭和公园。更有甚者,贵族们筹资购买山头,建起天文观测站。发展势头之猛,导致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科学咖啡馆至今仍然是欧洲最主要的谈论科学的场所。
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公民自己的理性思考和信息的有效表达。马丁·路德·金曾经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喧闹,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沉默的原因值得追究。首先是公民自身的觉醒意识。在科学技术事件中,公民作为纳税人,首先应该知道支持科学家的活动的经费来自公民的纳税。最近,美国“科学怪人”克瑞格·温特(Graig Venter)采用第二代基因解读技术成功进行的个人基因图谱解读和斯蒂文·奎科(Steven Quake)在自己家里将自己的基因图谱进行了解读并开发出个人基因图谱解读器,使查寻遗传疾病的方法进入到公民个人家中。他们的经费都是社会自行解决,也就是说,是公民社会自行解决的。前者的经费400万美金是世界第一富翁比尔·盖茨掏的,后者的经费完全是自己掏的。这是在高度发达的科学社会中才能出现的科学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在意识到社会的需求的时候,居然能够通过自己的财力解决科学问题。但是,大多数国家或者大多数科学技术项目中,公众还是作为纳税人对科学技术进行投资。但是,在公民社会未形成的国家中,作为公民只有纳税的义务,却并没有获得了解产品产出的权利。
中国的情况需要社会学家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在笔者过去20多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公众的几个重要特征。
1.我们在过去的将近3年时间内,对不同经济地区进行的公众科学意识调查中发现,虽然公众对科学家的行为已经不是绝对相信,但是对科学还是坚决支持。其支持的态度令人惊讶。他们中接近98%的人异口同声的声明,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用科学研究,他们都坚决支持。甚至声明:“即使再困难,我们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持!”
2.科学素养水平低。在2008年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学指标》(Science&Engineering Indicators)的国际科学素养比较中,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不仅低于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在多项问项中,正确回答比例低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
3.但是,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却居世界首位。尤其是对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的信息尤其感兴趣,尽管对医学新进展感兴趣程度不高。
4.尽管我们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不高,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程度很高,但是,科学信息渠道却十分有限。中国公众与其他国家的公众一样,电视是他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中国的电视台科教频道却仅仅只剩下10个,而且多数都在从事商业或者娱乐节目。
5.生活压力与信息需要的广度成反比。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但是,在中国体现的极其鲜明。尤其在中国边远的落后地区,信息基本隔绝的村落和社区不在少数。甚至在北京边远的山区,竟然还有没有电脑、没有数字网络的村落。农业种植收入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生活的压力使得他们的信息搜索范围形成“管视”,甚至“点视”效应。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生的重大科学事件,更不知道世界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发展对他们生活所具有的潜在的影响。他们不仅不知道高锟发明的“光缆”已经使得世界连为一体,甚至也不知道中国居然还发射过“神七”飞船。在科学技术发展如此快的今天,知识沟仍然不仅存在,而且发展趋势以及如何构成的因素,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过。
6.参与意识与自身利益成正比。大量的定性调查表明,我们的公民只有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存在潜在的威胁的时候才会参与决策。近些年来发生的污染事件和资源开发等工程事件与公众之间的冲突,多数发生在局部,甚至更小的范围,比如社区和村子。公民没有形成对作为整体社会公民的利益的思考,对自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同样也没有理性思维群体,即舆论领袖的产生和活动。所有的事件是否会产生冲突完全取决于一个偶然事件,或者良心科学家的偶然出现。
公民社会形成的外在因素目前在中国还远没有出现。最值得考量的就是影响公民社会形成的舆论要素。媒体虽然处于转型过程中,但是,这个转型与改革初期的企业转型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转型取决于经济运作模式和资本的再分配的模式转换。前者取决于掌握权力的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潜规则。两种本质不同的“转型”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对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我持怀疑态度。在免费赠阅的科技类报纸、杂志和自己掏钱买的大众类报刊和杂志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距离政府越近的媒体越远离科学与公众利益的讨论焦点。而目前技术和工程建设与利益的冲突却越演越烈。对此,所谓“主流媒体”三缄其口。
媒体体现出应付工作的状态。科学技术专业媒体远离科学中心,而社会大众类媒体却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事件核心。2009年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中国媒体中只有《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对华裔诺奖得主高锟现场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他所有科技媒体一片沉默。中国的科学技术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由科学技术专业媒体转向大众媒体。
最近,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似乎令人振奋。在2009年10月9日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上,胡锦涛谈话中谈到几个关键词: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愿,所有的号召都能得到实现。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