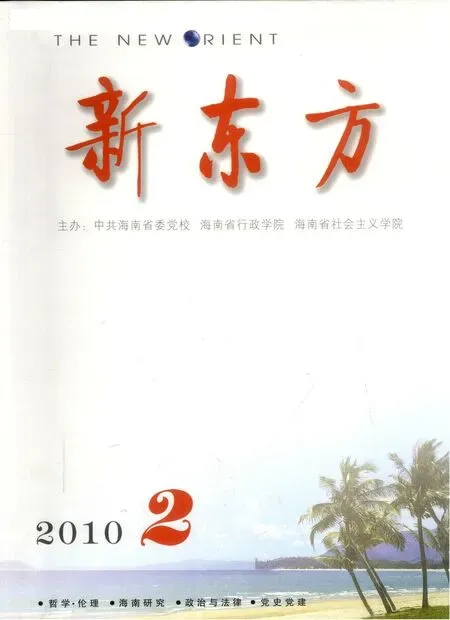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五大主题
干春松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五大主题
干春松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的思维特质也越来越受人关注。同样,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自信心的增强,也让我们开始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依然还很复杂,但是这样的复杂性本身就表明了,我们已经跟那些简单的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告别。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来谈论文化中国的问题。
文化问题,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同的文明形态,其实就是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凝结。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出西方、印度、中国、阿拉伯和其他许多不同的智慧类型。以前,我们在描述中国哲学特性的时候,因为西方的文化强势地位,所以一般比较喜欢谈论所谓中西文明比较的问题。其实,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同样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从多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文化。在这样的前提下,本文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描述。
一、天人合一
中国哲学以天人关系为主题,但是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对应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谓天,并非单纯指称客观的自然,而是凝结着人性的内容,体现了特定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其所谓人,也并非单纯指称人类社会,而是包含着对客观自然的效法,对宇宙和谐规律的体认。……由于中国哲学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探索,目的在于从中引申出一种可以运用于人事的内圣外王之道,所以理论与实践也是合而不分的。”[1]
具体来说,由于对于天、天道,人、人道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道家认为天道无为,人道有为,要达到“道法自然”的境界便应“不以人灭天”。
对于儒家而言,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天人相通,其实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天。以思孟学派的说法为例,《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意思是说天是人道的本原。但是如何去理解天呢,却是回到“人心”。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这看上去似乎是在做循环论证,但实质上儒家是以人为出发点来理解天地宇宙的。
天人相类是汉代的一种观点,典型的表述是“人副天数”,这种看法将天人关系的内在和谐理解成天和人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比如董仲舒说:“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天副人数》)这种说法对应于汉代的具体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所以并没有成为中国人思考天人关系的典型思路。
思孟学派的天人相通论被宋明时期的思想家所重视,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二程语录》十八)从这个思路转而讨论心性问题,便是“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同上)这样人类秩序便是一种天命之流行。后来的朱熹和陆王,理解天人关系并没有超出这个思路,其差别在于如何达成心性之间统一的方式不同。
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还有天人相分和天人交相胜等不同的说法。荀子等人试图说明自然秩序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差别,进而强调人在建立社会规范中的作用,但是他所忽略的是天人相通论所借助的天,更多的是象征的意义,因此,荀子的强调本身并没有击中天人相通的要害。
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均建立在天人和谐的基础之上。现代许多人在理解天人合一的时候,主要阐述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内容,以此来回应环境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但如果说“只有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则多少有些观念决定论的意味。
二、求真与致善
哲学之本义为“爱智”,中国人也十分重视智慧,但是中国人追求智慧的方法和目的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论语·子罕》中知、仁、勇三者并举,“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显然是将“知”看作是人品的重要内容,这种倾向在孟子那里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即以“是非之心”作为“智之端也”(《公孙丑》),这就是说人的智慧主要是要辨别是非。因此,“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2]
虽然荀子区分了“知”和“智”,“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正名》),后来张载又有“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区分。但是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知识论体系,对于作为认识方式的逻辑形式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并且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名家也消失无形了。
因此,中国思想的展开并不是建立在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之上,而是以能否完满地解释生活的经验和秩序的合理性为指向,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言说就只是道德教条而非理性之思索。中国思想并不追求清晰性,在讨论语言与对象的关系的时候,充分关注语言的局限性和对象的复杂性,因此“得意忘言”式的内心体悟成为高妙思想的标志。
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种“反智论”[3]的倾向,意思是说存在着对于具体知识和从事具体的知识创造的人的轻视。的确,在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传统社会中,那些对于自然的探索和器具的发明,会被看成是“奇技淫巧”,这几乎被认定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重要原因。
三、哲学与宗教
杨庆堃在《中国社会的宗教》一书中,用结构—功能的观点解析中国宗教,将之大致界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制度性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另外一种则是分散性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制度性宗教”自身有独特的神学或宇宙解释系统和形式化的(包括符号性的形象和精神表征,如上帝等)崇拜祭祀系统,并有一个独立的人事组织去促成神学观点的阐释和祭祀活动的进行。从结构角度而言,制度性宗教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自身可独立于世俗的社会体系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分离。“分散性宗教”也有其神学、祭祀与人事的运作系统,但是无论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的仪轨组织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成为结构的一部分,它自身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很显然,中国的本土宗教属于“分散性宗教”的范畴。
因此,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具有宰制意义的宗教,但是中国哲学中宗教的因素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哲学和宗教之间一直纠缠不清。比如说儒家,虽不说“怪力乱神”,但是特别强调“神道设教”。这种理性和信仰的混合特别体现在“礼”的繁盛上。一方面作为古代祭祀文化之遗存的“礼”在经过不断的理性化之后,转变为百姓日常生活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依然保留着许多神秘的和巫术化的色彩。道家也一样,其追求的清心寡欲与全身保形的养生方术不即不离,最后转化为道教的重要素材。
中国虽然没有出现系统化的宗教形态,但在道教出现之前,各种“类宗教”的形态比比皆是。那么中国人如何解决理性和信仰之间的问题,按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就是“以道德代宗教”。他说:“古代宗教往往临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礼俗法制在内,可以说整个社会靠它而组成,整个文化靠它作中心,岂是轻轻以人们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纵然欹重在道德上,道德之养成似亦要有个依傍,这个依傍,便是‘礼’。事实上,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二者合起来,遂无事乎宗教。此二者,在古时愿可摄之于一‘礼’字之内。在中国代替宗教者,实在是周孔之‘礼’。不过其归趣,则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别于宗教,因此我们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4]按着更为专业的逻辑线索,另一著名学者杨庆堃具体地分析了为什么儒家担负了很大部分的宗教功能。他说:“中国宗教缺少独立的中央组织的僧侣集团与有组织的会众,使它无法在社会组织的一般架构上占任何重要的地位。这样遂让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上扮演一个中心角色。同样地,宗教组织上的薄弱,使它在中国社会制度的运作上只能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配角。如果中国宗教会发展出强固的组织,则儒家恐惧宗教与之竞争将远甚于现在。这是在中国儒家与宗教长期以来合作的特性。”[5]此外,蔡元培还有“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显然没有梁氏的说法有说服力。
佛教传入之后,中国人开始接受佛教的许多观念,比如报应、轮回。但这种接受更多是道德意义上,而非宗教意义上。且由于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对于宗教往往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拜佛又给道教的元始天尊烧香。
中国人在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时候,其实并非特别明确地去区分是哲学还是宗教,进而言之,在许多时候与其说是将佛教看成是一种信仰,还不如说是一种哲学。现在人们也在讨论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这个问题或许有非哲学的背景。按照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强调儒家不是宗教,并不影响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肯定儒家是一种宗教,它也不能成为中国人的信仰。这是由中国人以哲学的态度看待宗教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了的。
四、斗争与和谐
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形态中,那种斗争性的决裂必然会让位于包容式的和谐。有两个观念可以作为这种思想的基础,“和而不同”和“中庸”。
“和而不同”,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史伯与郑桓公之间的谈话。谈话内容本身是关于周王室的命运,在批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的时候,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对“和”与“同”的含义作了解释:“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也就是将和看做是在差异之中寻求一种平衡的结合点,而如果反对差异,则没有出路。
春秋末年,晏婴发展了这一思想,并用音乐和烹调做例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矛盾的因素才能“相成相济”。后来孔子也使用“和”“同”的概念来说明为人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坚持在承认事物的差别的前提下,寻求和谐的方式。现在“和而不同”的思想被看做是处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一个原则,尽管中国原有的解释世界秩序的“天下”观念更具有价值观的意义。
“中庸”一直被看做是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达到的人生境界,其最紧要处在于“无过无不及”。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论语集注·雍也》)强调行为的适度性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调,在《易传》中表述为“正中”“中道”“中行”等。
这种对中道的追求,影响到中国人对于矛盾和对立双方斗争的结局的理解或者说期待。宋代的思想家张载说“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为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显然,统一性被肯定,矛盾的和解成为目标。虽然在客观世界中,矛盾的发展更多表现为有一方消灭另一方,但是如果立足于社会,那么对于和谐的肯定,对于斗争的化解是中国人对于秩序的一种理解。
五、生命与境界
中国思想文化的重点在于对人的生命与社会秩序的关切,尤其是儒家,如何修身做人,一直是其学说的核心。
儒家的主流是以性善论为基点,阐发出一套由人心上升至社会、国家乃至于天下的修养论体系,也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八条目”。儒家对于人的理解是有其特殊性的,也就是儒家将人在社会中的长幼尊卑看成是一种自然性的秩序,并依遵“缘情制礼”的原则,将道德规范的合理性诉诸于内心的情感的自发性。这一点《论语》中对于“三年之丧”和“子为父隐”的讨论中是很明显的。在孔子看来,父母去世之后,子女是否守三年之丧的答案在于“心安”,这种非逻辑性的证明在儒家看来是有力而不容置疑的。
整个中国文化都有一种很强的命定论色彩,在儒家那里命定论体现为抗命和宿命的矛盾统一。一方面对社会秩序的追求要求人们服从命运的安排,另一方面则要刚毅、奋斗。然而在道家的思想中,命定论发展出一套消极、闲适的生活态度,在命运面前的从容不迫。
人生观的终极表现是境界论。陈来说:“从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来说,中国文化与哲学不过是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强调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的境界,一种是以佛老为代表的注重内心宁静平和与超越自我的境界。”[6]如果更具体一点来看,在儒家的人生理想中,就包含有这两种态度,比如孔子既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方面最经典的表述要算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此,也有人说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儒道互补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思想家的观念模型中有许多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庄子笔下逍遥自在的“真人”“至人”和“神人”,魏晋的名士们更是以“放达”和“飘逸”形造出“魏晋风度”。到了宋明时期,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儒家人生理想的充分的表述,成为后来儒生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近代以来,有两种境界论颇受人欢迎,一是王国维的境界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个境界虽立意在文学创作,但何尝不是人生境界之侧影。
另一种境界说由冯友兰先生所提出。他在《论人生中底境界》中说:“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的“自然境界”是最低层次的精神境界,是指人对其行为只有生物直觉,是人对周围各方面的一种关系;“功利境界”是指其行为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道德境界”是指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是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冯先生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能是天地境界的最好体现吧。
总之,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和消极的平衡,以《周易》的话来说,便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蕴涵着宽容和博大。
由于受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影响,人们对中国的思想还有着很多的误解,依然是将之与封建、落后、愚昧相联系。现在,我们应该从盲目的唯西方主义中醒悟过来。我们依然相信西方思想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但我们要抛弃非此即彼。中国文明因为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世界其他文明一起,共同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情感和价值的依托。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各美其美,世界大同”的口号,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关系的一种角度,
我们现在提倡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国家是难以承载其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和义务的,所以了解中国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们承担民族发展使命的一部分。
[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7-288.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
[3]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M]//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学林出版社,1987:108-109.
[5]杨庆堃.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C]//杨联生,等.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339.
[6]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人民出版社,1991:5.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